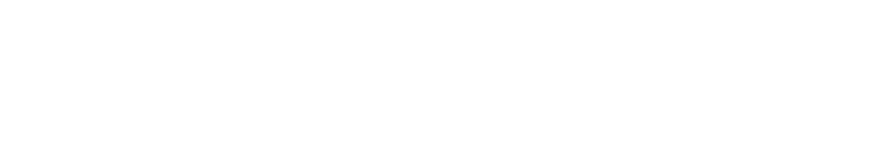历史重新审判:苏格拉底之死
| 发布时间: | 2009-09-04 | 点击次数: | 0 |
热案简述:
苏格拉底为什么审判雅典民主
来源:南方周末 2009-09-03 16:30:06 作者:冯八飞
■虎头传说
雅典的民主时期,个体非鬼即兽,“人民”的意志和利益高于一切,“人民”可以牺牲任何“人”。而现代的民主政治,享有政治主权的是“人”,而非“人民”,“人”从属于“人民”,但享有作为个体的“人”的自由、独立和尊严
不是民主保证自由,而是法律保证自由
公元前399年,70岁的苏格拉底,站在雅典的法庭上,审判雅典民主。
雅典是全世界第一个实行民主制的国家,也是全世界惟一一个实行民主制的古文明。其他的古文明最后都变成了封建社会。可是,雅典民主并非现代民主。公元前683年雅典废除了国王制,实行执政官制度,到梭伦改革,雅典宪法诞生,所有公民均获投票权,因此,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骄傲地宣布:“我们的制度之所以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手里,而非被少数人掌握!”不过,伯里克利的“全体公民”,其实并非“全体公民”,它仍然只是“少数人”。
只有纯正雅典血统的成年男子才是“雅典公民”,占雅典人口90%的奴隶、妇女和外国人均非公民。雅典公民生为雅典人,死为雅典鬼。亚里斯多德警告“公民不得私有其自身”。他建议惩处企图自杀的公民,因为自杀的结果是城邦丧失一个公民。雅典“公民”有权分享雅典的光荣与财富,其“公民权”类似“北京户口”,并非个人权利。西方的“个人权利”概念要到《罗马私法》时才形成。
苏格拉底生逢雅典“黄金时代”(前461-前429年),他25岁时雅典与斯巴达签订30年和约,伯里克利一统“提洛同盟”。文化上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好戏连台,菲狄亚斯的雕像和波吕格诺图的壁画精彩纷呈,雅典一跃而成“全希腊的学校”。
伯里克利的成功基础正是民主。他宣布:除军事财政之外所有的官职,均由公民抽签出任,海量激发了雅典民气。他完善的雅典国家机构成为“三权分立”的雏形。
雅典最高立法机关为公民大会,每月召开3至4次,决定内政和外交大事,通过的议案经批准即成国家法律。
雅典最高行政机关是500人议事会,专事公民大会的准备、召开和主持以及执行大会决议。500人又均分为10组,抽签轮流担任议事会执行委员会,负责处理国家日常事务。执委会再抽签一人出任议事会和公民大会主席,掌管金库钥匙和国玺,任期一天,不得连任。
雅典最高司法机关是陪审法庭。
苏格拉底审判雅典民主,地点就是陪审法庭。
苏格拉底犯了“不敬神”的重罪
公元前399年,检察官阿尼图斯、悲剧诗人美勒托和修辞学者吕孔控诉苏格拉底不敬城邦认可的神、另立新神和腐蚀青年。
不敬神是重罪。伯里克利老婆阿斯帕西亚曾被另一喜剧诗人指控“不敬神”,经伯里克利百般哀求才得免罪。但雅典议事会自此通过法律,规定凡不信雅典宗教神灵或教授宇宙理论者,均属“不敬神”。
被指控者,并非只有苏格拉底。
从伊奥尼亚到雅典讲学30年的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曾被控“不敬神”,因为他说太阳是一块红热的岩石,月亮是一块土。他是世界上第一个解释月光为太阳光反射,并据此正确解释月食的思想家。以当时的科学条件,这些发现基本上类似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值八个诺贝尔奖。他却因此被迫逃离雅典。
这是人类历史上科学触犯政府而遭政治迫害的第一个例子,恰恰发生在世界上第一个实行民主制的雅典。
另一位来雅典讲学的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在其著作《论神》中说:“我不能断定神是否存在,认识神障碍众多,第一是对象不明,第二是人生短暂”,结果其著作被公焚,这个以“人是万物的尺度”一句话影响西方哲学史二千年的伟大哲学家被控“不敬神”,只好逃离雅典。
伟大的悲剧家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10年也因“不敬神”被起诉,不得不自动离开雅典前往马其顿,最后客死异乡。
苏格拉底案件严格依照雅典民主审判程序进行。
雅典法庭民主到没有法官,只设主持人负责组织审判和维持秩序,判决权力完全属于陪审员。雅典法庭的民主,完全体现在陪审员。
每年初,年满30岁的雅典公民都可报名参选陪审员,雅典10个行政区从报名者中各抽签选出600人,共6000人成为陪审员,任期一年。遇有案件,则根据案件大小从6000人中抽签选出5到2000人组成陪审团,开庭之日再抽签将他们分配到不同的法庭。今天美国法庭的陪审团,源于雅典。
这个复杂的选拔程序完美体现了民主政治的最根本原则:公民直接和广泛参与政治生活。它有效预防贿赂,除非你能贿赂所有6000名陪审员而不被人知晓。
苏格拉底案陪审员500人。大案陪审员一般多达2000人,特别重大的案件往往由公民大会直接审判。因此,苏格拉底并非“由500名法官判处死刑”。
审判程序是原、被告先行辩论,然后举证,最后陪审团投票。被告获“无罪”票多,或“有罪”和“无罪”票数相等,均无罪。之后还要点算原告所得票数,如不足总票数的五分之一,原告就要遭到处罚,以惩罚诬告。
如被告被判有罪,则当场由原、被告分别提出具体判罚,再由陪审团投票选择其中之一作为最终判罚。
这一看似荒诞不经的程序,却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为让陪审团采纳自己提出的判罚,原、被告都会提出尽量合理的刑罚,不会随心所欲信马由缰。
除了苏格拉底。
雅典法庭民主完全彻底,即无论什么指控,无论有否证据,无论伤害大小,只要陪审团投票认定,罪名即告成立。当时又无现代刑侦手段提供证据,因此,通过辩论争取到陪审员同情,直接决定官司的胜负。
说到辩论,全雅典,苏格拉底认第二,就没人敢认第一。
苏格拉底口若悬河,陪审员两次全场哗然。第一次是因为他说自己是天底下最具智慧的人,因为他承认自己无知:“我承认我无知,而他们却不承认。我正是在这一点上比他们更智慧。因此,德尔菲神谕无误:惟有像苏格拉底那样知其智慧实际毫无价值的人,方最具智慧。”两千多年后,“我知我无知”,仍是绝大多数人可望而不可及的终极智慧。
雅典的民主程序,杀死了苏格拉底
然而,人民通常不会被智慧说服。
苏格拉底上法庭时,雅典早已不再是“黄金时代”。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再度当选雅典领袖,随即病死,接着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败于斯巴达,斯巴达扶植“30僭主(tyrant,指违宪夺权者)”执政,其统治的暴虐导致后世把Tyrant直接译为“暴君”。一年后30僭主被推翻,民主派卷土重来。重新上台的雅典民主派矫枉过正,片面强调反对任何人独裁,结果走向另一个极端———人民独裁。
古希腊文“民主”一词(Δημοκρτια,demokratia)由“demos”(人民)和“kratos”(统治)复合而成,因此,雅典的民主就是“人民统治”。不过这里的“人民”是集合名词,指整个“人民”,而非作为独立个人的“人”。亚里斯多德说,个体只有在属于雅典时,其存在才有意义。不属于雅典的个体非鬼即兽。“人民”的意志和利益高于一切,为此可以牺牲任何“人”。而现代民主政治中享有政治主权的是“人”,而非“人民”,“人”虽从属“人民”,但同时享有作为个体的“人”的自由和独立。
雅典民主最伟大的例子是“陶片放逐法”。该法律规定每年雅典可放逐一名政治家,由公民大会投票决定,因选票为碎陶片而得名(后选票改用贝壳,所以亦称“贝壳放逐法”)。投票者只需刻上政治家名字,无需任何罪行,也无需任何证据,只要该政治家得票超过6000,即遭放逐10年。
雅典名将阿里斯泰德是马拉松战役的指挥官,战功显赫,曾担任首席执政官,素以“公正者”著称,公元前483年经公民大会投票遭放逐!据说投票时有个文盲农民把陶片递给正好坐他旁边的阿里斯泰德代为刻字。阿里斯泰德大奇曰:“您都不认识他,为何赞成放逐?”农民答曰:“经常听人歌颂他为‘公正者’,很烦人,干脆放逐了算了。”据说,阿里斯泰德真的在那块陶片上刻下自己的名字。而且他真的就此服从判决,离开雅典,没想到过发动军事政变。因为他知道,发动军事政变也没用。军队不会跟他走,虽然他在军队中享有崇高威望。
强大的雅典军队,只服从公民大会。
因为,雅典军队的所有士兵,都是“雅典公民”。
这就是雅典的“人民统治”,近乎独裁的力量!
因此,在当时雅典的民主法庭上,并无现代民主制必不可少的言论自由。只有陪审员的言论自由。可是,苏格拉底却在法庭上大声疾呼:“必须给我讨论所有问题的充分自由。必须彻底废除官方干涉。”他知道自己定会为言论自由付出代价。
然而,他仍然自由言论!
他说:无论是否被判有罪,他都不会改变自己的行为,“哪怕要我死一百次!”苏格拉底的这番话,引起陪审团第二次全场哗然。
投票!苏格拉底以280票对220票被判有罪。
然后双方提出刑罚。原告提议判苏格拉底死刑。轮到苏格拉底,他宣布自己对雅典民主的贡献超过奥林匹克冠军,因此不仅无罪,而且法庭还应当发给他执委会免费就餐券作为判决书。他说自己给学生上课从不收费,所以没钱,因此建议法庭罚他一个明那(合银436克),后来在柏拉图等学生的呼喊下勉强改成30个明那。然而,他拒绝改变自己的行为:“只要我的良心和我那微弱的心声还在让我继续向前,我就要把通向真理的真正道路指给人们,绝不顾虑后果。”陪审团从没见过像买大白菜一样拿死刑讨价还价的被告,苏格拉底彻底激怒了陪审团。第二轮投票,他以360票对140被判处死刑!第一轮判他无罪的陪审员竟有80人转而判他死刑!
这就是没有法律约束的“人民统治”。这当然不是公正的审判。陪审员的愤怒消灭了苏格拉底的肉体。雅典公民胜利了,雅典法律失败了。于是,历史留给历史无尽的讽刺:30僭主恨苏格拉底入骨,但不敢杀他,雅典民主派却以绝对公平的陪审团,通过真正民主的程序,杀死了苏格拉底。
民主的要义不在于少数服从多数,而在于多数保护少数
雅典民主制的悲剧结果,不是民主制的问题。民主的第一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然而,这原则具有与生俱来的不治之症:多数欺压少数。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断言:“人民易行专横残暴”,而且“多数人永远并毫无例外地剥夺少数人的权利”。这位《独立宣言》的共同起草人认为,所有的政体中,民主政体最容易发生混乱。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之父卢梭在奠定“主权在民”民主思想基础的伟大著作《社会契约论》中说:“人民可以废除任何他们想废除的东西,没有也不可能有哪部法律可以约束全体人民……任何拒不服从公众意志的人,集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多数欺压少数”的例子比比皆是:1793年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被民选上台;1852年拿破仑第三获80%赞成票当上了皇帝;1932年4月希特勒在德国总统大选中以36.8%得票数仅次于兴登堡列第二,后被兴登堡总统委任为总理,民主程序十分完备的魏玛共和国,通过绝对民主的选举,把希特勒捧上台。希望大家记住,希特勒,是被德国人民选上台的。
这些例子的结果如何,大家都知道。
最触目惊心的例子是法国大革命。1793年1月21日,亲手参与发明断头台并亲自批准用它执行死刑的法王路易十六,在巴黎协和广场被送上断头台。巴黎人民万众沸腾的山呼海啸至今犹在耳边:“国王的血不是人血。死刑!死刑!”奠定人类民主基石的法国大革命不仅杀死了路易十六,并且杀死了所有的革命领袖:马拉、丹东、埃贝尔、布里索、罗兰夫人、罗伯斯庇尔。一场以推翻国王统治,创立民主共和为目标的伟大革命,穿越欧洲最惊心动魄的血雨腥风,赢得历史的惊人倒退:巴黎人推翻了国王,最后得到一个皇帝———拿破仑。
因此,民主不是万应良方。还要看如何民主。
列宁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事实正是如此,在政治、文化和科学领域中,能够提出崭新意见,能够迅速认同新知识,能够接受新真理,能够率先冲破旧传统束缚、慨然向新世纪放歌的,永远是“少数”,而且通常会被视为“破坏秩序者”,正如萧伯纳所说:“许多伟大的真理开始时都被视为亵渎。”如果绝对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人类社会,根本不会进步。
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民主的要义并不在于少数服从多数。
一般说来,少数只好服从多数。因为,权贵比较容易获得“多数”。
民主的要义,在于保护少数!保护少数,经常就是保护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没有法律的民主,将沦为人民的独裁
那么,用什么来保护少数呢?
法律!
不是民主保证自由,而是法律保证自由。洛克说:“人类天生自由、平等和独立,不能剥夺任何人的这些权利,非经本人同意,不能令其受制于他人政治权力”,而保障自由的不二法门,是法律:“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因为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暴力侵犯。”“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洛克仅仅重复苏格拉底的话,就当了哲学大师。雅典法律判处苏格拉底死刑,但他却为了维护雅典法律的尊严而拒绝逃生。他要证明的,就是这句话。苏格拉底为自由和法律而死,替人类世界立下万世不倒之民主华表:严格遵守法律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没有法律的民主,最后只能沦为人民的独裁。
历史教育我们,世界上并不存在“好的独裁”。
哪怕是人民的独裁。
真正的悲剧,是两个合法道德的正面呼啸相撞,双方都有充足的存在理由,但却必得你死而我方可活。民主,是雅典城邦的伟大实践;法律与正义,是苏格拉底的伟大理想,双方冲突不可调和。苏格拉底以身殉道,慷慨奉上生命,为维护那部判他死刑的法律那至高无上的尊严。
苏格拉底之死,是真正的哲学之生。
苏格拉底之死,是独立自由的“人”面对集体的“人民”之生!
人的自我意识随之觉醒,人,终于看到他诞生以来的第一个真理,也是最后一个真理:认识你自己!
德尔菲女祭司被称为先知。然而,她们都只是习俗培养的不自觉的演员。
古希腊第一个伟大先知,是苏格拉底。他说,“如果你们指望用死刑来制止大家公开谴责你们的错误生活方式,那你们就错了。这种逃避方式既不可能又不可信。尽善易行的办法不是堵住别人的嘴,而是尽力向善。这是我对投票判我有罪者的最后告诫。”苏格拉底,全世界第一个为言论自由和法律尊严自愿奉献生命的圣哲。
高山仰止!
从此,这个笨拙矮小的“菜市场演说家”纵剑历史,马踏时空,赢得后世哲学家万众一致的推崇,这些谁也不服的超级大腕,独向苏格拉底低下高贵的头。
在西方文化中,他是惟一与耶稣并肩的思想殉道者。巧合的是,他俩都未留下自己的著作。他们的思想,都只见诸弟子的纪录。
以民主和自由为标榜的雅典审判苏格拉底,判词是:死刑。
一生追求法律和真理的苏格拉底用自己的生命在历史面前审判雅典民主,判词是:非正义!
拥有耀眼夺目古文明的伟大雅典,把“杀死苏格拉底”的耻辱十字架一直背到今天。并且,还将继续背下去。
这是苏格拉底判给雅典的无期徒刑。永不减刑。
因为,苏格拉底,只能死一次。
有时候,杀死对手,就是自己走进地狱。
请记住苏格拉底:民主,是美好的,是每一个现代国家的必需。
不过,还必须由至高无上、不容亵渎的法律来保证。
来源:南方周末 2009-09-03 16:30:06 作者:冯八飞
■虎头传说
雅典的民主时期,个体非鬼即兽,“人民”的意志和利益高于一切,“人民”可以牺牲任何“人”。而现代的民主政治,享有政治主权的是“人”,而非“人民”,“人”从属于“人民”,但享有作为个体的“人”的自由、独立和尊严
不是民主保证自由,而是法律保证自由
公元前399年,70岁的苏格拉底,站在雅典的法庭上,审判雅典民主。
雅典是全世界第一个实行民主制的国家,也是全世界惟一一个实行民主制的古文明。其他的古文明最后都变成了封建社会。可是,雅典民主并非现代民主。公元前683年雅典废除了国王制,实行执政官制度,到梭伦改革,雅典宪法诞生,所有公民均获投票权,因此,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骄傲地宣布:“我们的制度之所以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手里,而非被少数人掌握!”不过,伯里克利的“全体公民”,其实并非“全体公民”,它仍然只是“少数人”。
只有纯正雅典血统的成年男子才是“雅典公民”,占雅典人口90%的奴隶、妇女和外国人均非公民。雅典公民生为雅典人,死为雅典鬼。亚里斯多德警告“公民不得私有其自身”。他建议惩处企图自杀的公民,因为自杀的结果是城邦丧失一个公民。雅典“公民”有权分享雅典的光荣与财富,其“公民权”类似“北京户口”,并非个人权利。西方的“个人权利”概念要到《罗马私法》时才形成。
苏格拉底生逢雅典“黄金时代”(前461-前429年),他25岁时雅典与斯巴达签订30年和约,伯里克利一统“提洛同盟”。文化上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好戏连台,菲狄亚斯的雕像和波吕格诺图的壁画精彩纷呈,雅典一跃而成“全希腊的学校”。
伯里克利的成功基础正是民主。他宣布:除军事财政之外所有的官职,均由公民抽签出任,海量激发了雅典民气。他完善的雅典国家机构成为“三权分立”的雏形。
雅典最高立法机关为公民大会,每月召开3至4次,决定内政和外交大事,通过的议案经批准即成国家法律。
雅典最高行政机关是500人议事会,专事公民大会的准备、召开和主持以及执行大会决议。500人又均分为10组,抽签轮流担任议事会执行委员会,负责处理国家日常事务。执委会再抽签一人出任议事会和公民大会主席,掌管金库钥匙和国玺,任期一天,不得连任。
雅典最高司法机关是陪审法庭。
苏格拉底审判雅典民主,地点就是陪审法庭。
苏格拉底犯了“不敬神”的重罪
公元前399年,检察官阿尼图斯、悲剧诗人美勒托和修辞学者吕孔控诉苏格拉底不敬城邦认可的神、另立新神和腐蚀青年。
不敬神是重罪。伯里克利老婆阿斯帕西亚曾被另一喜剧诗人指控“不敬神”,经伯里克利百般哀求才得免罪。但雅典议事会自此通过法律,规定凡不信雅典宗教神灵或教授宇宙理论者,均属“不敬神”。
被指控者,并非只有苏格拉底。
从伊奥尼亚到雅典讲学30年的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曾被控“不敬神”,因为他说太阳是一块红热的岩石,月亮是一块土。他是世界上第一个解释月光为太阳光反射,并据此正确解释月食的思想家。以当时的科学条件,这些发现基本上类似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值八个诺贝尔奖。他却因此被迫逃离雅典。
这是人类历史上科学触犯政府而遭政治迫害的第一个例子,恰恰发生在世界上第一个实行民主制的雅典。
另一位来雅典讲学的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在其著作《论神》中说:“我不能断定神是否存在,认识神障碍众多,第一是对象不明,第二是人生短暂”,结果其著作被公焚,这个以“人是万物的尺度”一句话影响西方哲学史二千年的伟大哲学家被控“不敬神”,只好逃离雅典。
伟大的悲剧家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10年也因“不敬神”被起诉,不得不自动离开雅典前往马其顿,最后客死异乡。
苏格拉底案件严格依照雅典民主审判程序进行。
雅典法庭民主到没有法官,只设主持人负责组织审判和维持秩序,判决权力完全属于陪审员。雅典法庭的民主,完全体现在陪审员。
每年初,年满30岁的雅典公民都可报名参选陪审员,雅典10个行政区从报名者中各抽签选出600人,共6000人成为陪审员,任期一年。遇有案件,则根据案件大小从6000人中抽签选出5到2000人组成陪审团,开庭之日再抽签将他们分配到不同的法庭。今天美国法庭的陪审团,源于雅典。
这个复杂的选拔程序完美体现了民主政治的最根本原则:公民直接和广泛参与政治生活。它有效预防贿赂,除非你能贿赂所有6000名陪审员而不被人知晓。
苏格拉底案陪审员500人。大案陪审员一般多达2000人,特别重大的案件往往由公民大会直接审判。因此,苏格拉底并非“由500名法官判处死刑”。
审判程序是原、被告先行辩论,然后举证,最后陪审团投票。被告获“无罪”票多,或“有罪”和“无罪”票数相等,均无罪。之后还要点算原告所得票数,如不足总票数的五分之一,原告就要遭到处罚,以惩罚诬告。
如被告被判有罪,则当场由原、被告分别提出具体判罚,再由陪审团投票选择其中之一作为最终判罚。
这一看似荒诞不经的程序,却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为让陪审团采纳自己提出的判罚,原、被告都会提出尽量合理的刑罚,不会随心所欲信马由缰。
除了苏格拉底。
雅典法庭民主完全彻底,即无论什么指控,无论有否证据,无论伤害大小,只要陪审团投票认定,罪名即告成立。当时又无现代刑侦手段提供证据,因此,通过辩论争取到陪审员同情,直接决定官司的胜负。
说到辩论,全雅典,苏格拉底认第二,就没人敢认第一。
苏格拉底口若悬河,陪审员两次全场哗然。第一次是因为他说自己是天底下最具智慧的人,因为他承认自己无知:“我承认我无知,而他们却不承认。我正是在这一点上比他们更智慧。因此,德尔菲神谕无误:惟有像苏格拉底那样知其智慧实际毫无价值的人,方最具智慧。”两千多年后,“我知我无知”,仍是绝大多数人可望而不可及的终极智慧。
雅典的民主程序,杀死了苏格拉底
然而,人民通常不会被智慧说服。
苏格拉底上法庭时,雅典早已不再是“黄金时代”。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再度当选雅典领袖,随即病死,接着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败于斯巴达,斯巴达扶植“30僭主(tyrant,指违宪夺权者)”执政,其统治的暴虐导致后世把Tyrant直接译为“暴君”。一年后30僭主被推翻,民主派卷土重来。重新上台的雅典民主派矫枉过正,片面强调反对任何人独裁,结果走向另一个极端———人民独裁。
古希腊文“民主”一词(Δημοκρτια,demokratia)由“demos”(人民)和“kratos”(统治)复合而成,因此,雅典的民主就是“人民统治”。不过这里的“人民”是集合名词,指整个“人民”,而非作为独立个人的“人”。亚里斯多德说,个体只有在属于雅典时,其存在才有意义。不属于雅典的个体非鬼即兽。“人民”的意志和利益高于一切,为此可以牺牲任何“人”。而现代民主政治中享有政治主权的是“人”,而非“人民”,“人”虽从属“人民”,但同时享有作为个体的“人”的自由和独立。
雅典民主最伟大的例子是“陶片放逐法”。该法律规定每年雅典可放逐一名政治家,由公民大会投票决定,因选票为碎陶片而得名(后选票改用贝壳,所以亦称“贝壳放逐法”)。投票者只需刻上政治家名字,无需任何罪行,也无需任何证据,只要该政治家得票超过6000,即遭放逐10年。
雅典名将阿里斯泰德是马拉松战役的指挥官,战功显赫,曾担任首席执政官,素以“公正者”著称,公元前483年经公民大会投票遭放逐!据说投票时有个文盲农民把陶片递给正好坐他旁边的阿里斯泰德代为刻字。阿里斯泰德大奇曰:“您都不认识他,为何赞成放逐?”农民答曰:“经常听人歌颂他为‘公正者’,很烦人,干脆放逐了算了。”据说,阿里斯泰德真的在那块陶片上刻下自己的名字。而且他真的就此服从判决,离开雅典,没想到过发动军事政变。因为他知道,发动军事政变也没用。军队不会跟他走,虽然他在军队中享有崇高威望。
强大的雅典军队,只服从公民大会。
因为,雅典军队的所有士兵,都是“雅典公民”。
这就是雅典的“人民统治”,近乎独裁的力量!
因此,在当时雅典的民主法庭上,并无现代民主制必不可少的言论自由。只有陪审员的言论自由。可是,苏格拉底却在法庭上大声疾呼:“必须给我讨论所有问题的充分自由。必须彻底废除官方干涉。”他知道自己定会为言论自由付出代价。
然而,他仍然自由言论!
他说:无论是否被判有罪,他都不会改变自己的行为,“哪怕要我死一百次!”苏格拉底的这番话,引起陪审团第二次全场哗然。
投票!苏格拉底以280票对220票被判有罪。
然后双方提出刑罚。原告提议判苏格拉底死刑。轮到苏格拉底,他宣布自己对雅典民主的贡献超过奥林匹克冠军,因此不仅无罪,而且法庭还应当发给他执委会免费就餐券作为判决书。他说自己给学生上课从不收费,所以没钱,因此建议法庭罚他一个明那(合银436克),后来在柏拉图等学生的呼喊下勉强改成30个明那。然而,他拒绝改变自己的行为:“只要我的良心和我那微弱的心声还在让我继续向前,我就要把通向真理的真正道路指给人们,绝不顾虑后果。”陪审团从没见过像买大白菜一样拿死刑讨价还价的被告,苏格拉底彻底激怒了陪审团。第二轮投票,他以360票对140被判处死刑!第一轮判他无罪的陪审员竟有80人转而判他死刑!
这就是没有法律约束的“人民统治”。这当然不是公正的审判。陪审员的愤怒消灭了苏格拉底的肉体。雅典公民胜利了,雅典法律失败了。于是,历史留给历史无尽的讽刺:30僭主恨苏格拉底入骨,但不敢杀他,雅典民主派却以绝对公平的陪审团,通过真正民主的程序,杀死了苏格拉底。
民主的要义不在于少数服从多数,而在于多数保护少数
雅典民主制的悲剧结果,不是民主制的问题。民主的第一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然而,这原则具有与生俱来的不治之症:多数欺压少数。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断言:“人民易行专横残暴”,而且“多数人永远并毫无例外地剥夺少数人的权利”。这位《独立宣言》的共同起草人认为,所有的政体中,民主政体最容易发生混乱。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之父卢梭在奠定“主权在民”民主思想基础的伟大著作《社会契约论》中说:“人民可以废除任何他们想废除的东西,没有也不可能有哪部法律可以约束全体人民……任何拒不服从公众意志的人,集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多数欺压少数”的例子比比皆是:1793年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被民选上台;1852年拿破仑第三获80%赞成票当上了皇帝;1932年4月希特勒在德国总统大选中以36.8%得票数仅次于兴登堡列第二,后被兴登堡总统委任为总理,民主程序十分完备的魏玛共和国,通过绝对民主的选举,把希特勒捧上台。希望大家记住,希特勒,是被德国人民选上台的。
这些例子的结果如何,大家都知道。
最触目惊心的例子是法国大革命。1793年1月21日,亲手参与发明断头台并亲自批准用它执行死刑的法王路易十六,在巴黎协和广场被送上断头台。巴黎人民万众沸腾的山呼海啸至今犹在耳边:“国王的血不是人血。死刑!死刑!”奠定人类民主基石的法国大革命不仅杀死了路易十六,并且杀死了所有的革命领袖:马拉、丹东、埃贝尔、布里索、罗兰夫人、罗伯斯庇尔。一场以推翻国王统治,创立民主共和为目标的伟大革命,穿越欧洲最惊心动魄的血雨腥风,赢得历史的惊人倒退:巴黎人推翻了国王,最后得到一个皇帝———拿破仑。
因此,民主不是万应良方。还要看如何民主。
列宁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事实正是如此,在政治、文化和科学领域中,能够提出崭新意见,能够迅速认同新知识,能够接受新真理,能够率先冲破旧传统束缚、慨然向新世纪放歌的,永远是“少数”,而且通常会被视为“破坏秩序者”,正如萧伯纳所说:“许多伟大的真理开始时都被视为亵渎。”如果绝对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人类社会,根本不会进步。
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民主的要义并不在于少数服从多数。
一般说来,少数只好服从多数。因为,权贵比较容易获得“多数”。
民主的要义,在于保护少数!保护少数,经常就是保护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没有法律的民主,将沦为人民的独裁
那么,用什么来保护少数呢?
法律!
不是民主保证自由,而是法律保证自由。洛克说:“人类天生自由、平等和独立,不能剥夺任何人的这些权利,非经本人同意,不能令其受制于他人政治权力”,而保障自由的不二法门,是法律:“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因为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暴力侵犯。”“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洛克仅仅重复苏格拉底的话,就当了哲学大师。雅典法律判处苏格拉底死刑,但他却为了维护雅典法律的尊严而拒绝逃生。他要证明的,就是这句话。苏格拉底为自由和法律而死,替人类世界立下万世不倒之民主华表:严格遵守法律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没有法律的民主,最后只能沦为人民的独裁。
历史教育我们,世界上并不存在“好的独裁”。
哪怕是人民的独裁。
真正的悲剧,是两个合法道德的正面呼啸相撞,双方都有充足的存在理由,但却必得你死而我方可活。民主,是雅典城邦的伟大实践;法律与正义,是苏格拉底的伟大理想,双方冲突不可调和。苏格拉底以身殉道,慷慨奉上生命,为维护那部判他死刑的法律那至高无上的尊严。
苏格拉底之死,是真正的哲学之生。
苏格拉底之死,是独立自由的“人”面对集体的“人民”之生!
人的自我意识随之觉醒,人,终于看到他诞生以来的第一个真理,也是最后一个真理:认识你自己!
德尔菲女祭司被称为先知。然而,她们都只是习俗培养的不自觉的演员。
古希腊第一个伟大先知,是苏格拉底。他说,“如果你们指望用死刑来制止大家公开谴责你们的错误生活方式,那你们就错了。这种逃避方式既不可能又不可信。尽善易行的办法不是堵住别人的嘴,而是尽力向善。这是我对投票判我有罪者的最后告诫。”苏格拉底,全世界第一个为言论自由和法律尊严自愿奉献生命的圣哲。
高山仰止!
从此,这个笨拙矮小的“菜市场演说家”纵剑历史,马踏时空,赢得后世哲学家万众一致的推崇,这些谁也不服的超级大腕,独向苏格拉底低下高贵的头。
在西方文化中,他是惟一与耶稣并肩的思想殉道者。巧合的是,他俩都未留下自己的著作。他们的思想,都只见诸弟子的纪录。
以民主和自由为标榜的雅典审判苏格拉底,判词是:死刑。
一生追求法律和真理的苏格拉底用自己的生命在历史面前审判雅典民主,判词是:非正义!
拥有耀眼夺目古文明的伟大雅典,把“杀死苏格拉底”的耻辱十字架一直背到今天。并且,还将继续背下去。
这是苏格拉底判给雅典的无期徒刑。永不减刑。
因为,苏格拉底,只能死一次。
有时候,杀死对手,就是自己走进地狱。
请记住苏格拉底:民主,是美好的,是每一个现代国家的必需。
不过,还必须由至高无上、不容亵渎的法律来保证。
人物简述:
历史重新审判:苏格拉底之死
公元前399年的一天傍晚,当最后一缕夕阳穿过铁窗的时候,一位老人在囚室里,最后望了一眼爱琴海上满天的落霞,最后,举起一杯狱卒送来的毒酒,一饮而尽。14年后,雅典人民悲痛的为这宗冤案平了反,老人至死追寻的“公平正义”,终于重返希腊的故乡之路,这位年已七旬的先哲有一个不朽的名字——苏格拉底。其后,自柏拉图以来,无数先贤写就诸多著作文章,试图对此事件进行解读,找寻苏格拉底之死的根本原由。
以言论自由著称的一个城市竟然对一个除了运用言论自由以外没有犯任何其他罪行的哲学家提出起诉,为什么一个民主自由的制度不能容忍思想或信仰自由?为什么以民主著称的雅典会将苏格拉底这样的思想家判处死刑?或者说,苏格拉底为什么会死于民主的审判?有人说,苏格拉底的死“在民主身上永远留下了一个污点,这乃是雅典的悲剧性罪行。”他死于民主导致的“多数人的暴政”。
笔者以为,苏格拉底之死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民主,民主本身并没有过错。苏格拉底死于雅典的司法,死于披着民主外衣的审判制度,真正令苏格拉底丧命的是民主的审判,是背离了法的精神和灵魂的雅典“民主审判”。
一雅典审判的程序复杂而表面又处处彰显民主,“有公众法庭制度,这些法庭由全体公民或由全体公民中选出的人们组成,有权审判一切案件,至少大多数案件,包括那些最重大的案件,例如审查政务和财政报告、法律事项以及公私契约。”[4]其实雅典的法庭并不设法官,只设主持官,负责组织审判并维持法庭的秩序,判决的权力则在陪审团。陪审团成员从公民群体中抽签产生。每年初公民自愿报名竞争当年陪审团成员,而后从自愿者中抽出六千人,作为当年陪审团成员。如遇开庭之日,城邦官员实现根据案件大小确定审判每桩案件所需陪审员总人数。开庭之前,再以抽签的方式将这些陪审员分配到不同的法庭,审理不同的案件。判定被告是否有罪的唯一标准是陪审团的投票,如果被告获得的票数占多数,他即获得清白之名,有罪和无罪票数相等时则被告无罪释放;如果判定被告有罪,则由原告和被告本人分别提出具体的刑罚,再由陪审团投票选取其中之一作为最终判罚。固然,这种“民主审判”的程序和方法有合理之处,但却背离法的终极价值。仔细回味苏格拉底受审过程,不难发现雅典“民主审判”制度使得苏格拉底自被起诉之时就已在劫难逃,跌入一个悖论式的怪圈[6]并最终从容就死有其必然性。
其一,在雅典,没有公共检察官或公诉人,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提出控诉。诚然,这与现今“公民逮捕”的法律理论有相似之处——允许任何公民在看到有人犯罪时逮捕他,每个公民都有权利和责任在他认为法律遭到违反的时候提出诉讼,这符合雅典的参与性民主政府的概念[7],但起诉者却难免沾染个人情感偏好。苏格拉底案件中代表人民提起公诉的是三个雅典公民,为首的美莱德斯就与苏格拉底曾有过结,很难要求其完全站在现代公诉人只对法律与事实负责的独立检控立场。
其二,大众司法观念使得陪审团成员任职资格要求几乎为零,陪审团成员并不被要求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和审判能力,且其任期只有一年,而且终身只能担任两次,专业审判知识积累、能力培养无从谈起。
其三,审判就是民主的投票,依据的并不是法律条款,而简单遵从得票的多数与少数。在“苏案”陪审团中,有很多曾被苏格拉底驳斥的哑口无言、被他证明为一无所知却认为自己无所不知的人,这些人对苏格拉底狠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而正是这些人却将决定苏格拉底的生死,苏格拉底岂不注定在劫难逃。苏格拉底在第一轮的投票中以281票比220票被判有罪,然而在提出近乎玩笑的刑罚后惹怒众人,最终以361票比140票被判死刑。其中有80人原先认定苏格拉底无罪,但由于苏格拉底的表现,却在第二轮投票中倒戈,从无罪到死刑的跨越说明众人对苏格拉底的印象、态度成为了判决的根本。
二显然,苏格拉底之死让我们清醒的认识到,雅典司法遗憾的沦为被偏狭的激情左右的民众表达政治意志的工具。在讲求民主的社会中,人民作为主权者掌握公共权力合法性的源泉,而人民赋予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分支合法性的过程始末,我们不难寻觅到民主的踪迹,司法常常通过民主的途径获取正当性,但这并不意味人们行使司法权必须时刻通过民主的手段,民主与司法之间的天然鸿沟使得民主并不可随意侵入司法领域。
首先,民主与司法在自由层面的落脚点不同。民主的本质是人民主权,对民主最简单的理解即是少数服从多数,通常所说的人民当家作主实际就是人们行使其“积极自由”或“政治自由”,去分享社会权力,平等参与政治生活的自由。而现代人的目标是享受有保障的私人快乐;他们把对这些私人快乐的制度保障称作自由[8],即所谓“免于……的自由”的消极自由,苏格拉底之死实际上意味着积极自由或者直接民主剥夺了消极自由。消极自由的充要条件必然是一个人有自己最后的或者最低限度的不可侵犯的领域或者空间,而此项条件最忠实捍卫者便是作为社会生活最终底线的司法。“法律的目的不是要废除和限制人民的自由,而是要保护和扩大人民的自由。……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
其次,民主与司法的终极价值不同。法,其实便是“自然天理”,法起源于人类的“行为习惯”,法的本质就是“公平正义”,而司法的终极价值就是坚持、实现和维护“公平正义”,是一个社会的稳定器。民主的基本追求则是平等,“一个看重正义、法律与自由的国家,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必定是不平等的。”不可以对平等的追求野蛮的替代对公平正义的坚持,人人平等并不等同于公平正义,否则,司法将成为披着民主外衣扼杀少数人自由的刽子手。
其三,对于司法而言,最重要的是根据目的和理性实施法律。司法的本质是理性的判断,因此作为判断主体的法官,其素质高低直接影响司法价值能否真正实现。我们不能排除“苏案”陪审团成员中会有少数司法天才,但我们也不可能指望一个现代国家的司法制度建立在这少数司法天才的基础上。司法的过程是一个依靠理性和知识做出公正判断的过程,是一个不能掺杂个人利害关系在其中的推理过程。而对民主而言,最重要的是实现自身或自己所代表的那部分人的利益,且作为民主主体的人民做出判断时往往带有不理智的随意性,而这种随意性往往显得急躁,使得人民在判断或选择之后通常总会后悔曾经的行为。
三当然,上述论述并不表明司法将完全摈弃民主,否则司法权难以获取合法性。学者陈国刚先生认为,司法遭遇民主后产生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法官如何产生,他认为无论是民主选举还是任命都会引发矛盾性的疑问[11],其实这并不成为问题,他产生这样观点的原由在于孤立的考察法官个体的产生程序,主权者并不是将审判权力逐个给予每一个不论通过何种方式选拔出的法官,法官也不因为成功通过选拔而立即享有审判权力,他也并不是且也并不能用个人名义行使审判权。法官能够进行审判活动是其因获得司法机关中的某个职位从而获取此职位背后隐含的由民主赋予的司法权的使用权。人民将司法权授予司法机关集体,法官不过是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的工具罢了。绝大多数美国公民都倾向于认定辛普森有罪,但当美国法官依据法定程序宣告他无罪时,法官宣布的并不是他个人的判断,而是一个法律或者司法群体的判断,因此,即使这个判断错了,法官也无需对此承担责任,也没有人会因为这个决定事实上有错误而苛责法官。
由上可以引出陈国刚先生的另一个问题,即司法的民主责任。司法向代议机关负责更多意义上是指司法机关就其是否在法律轨道内合法合理运行、其整体行为是否忠实实施由民主制定的法律接受代议机关监督,而此种监督常被误读为个案监督。法院的判决依据的是由民意制定产生的法律,而不是在审判过程中将民意作为判断的条件之一。而且任何判决都难以取得所有当事双方的认同,人民对于司法机关的满意度并不应严格取决于个案判决,否则总会有另一半人(败诉者)对司法持不满意态度。司法的民主责任在于其只对法律负责,以民主基础上产生的法律为准绳,履行公平正义守护神的职责。
公元前399年的一天傍晚,当最后一缕夕阳穿过铁窗的时候,一位老人在囚室里,最后望了一眼爱琴海上满天的落霞,最后,举起一杯狱卒送来的毒酒,一饮而尽。14年后,雅典人民悲痛的为这宗冤案平了反,老人至死追寻的“公平正义”,终于重返希腊的故乡之路,这位年已七旬的先哲有一个不朽的名字——苏格拉底。其后,自柏拉图以来,无数先贤写就诸多著作文章,试图对此事件进行解读,找寻苏格拉底之死的根本原由。
以言论自由著称的一个城市竟然对一个除了运用言论自由以外没有犯任何其他罪行的哲学家提出起诉,为什么一个民主自由的制度不能容忍思想或信仰自由?为什么以民主著称的雅典会将苏格拉底这样的思想家判处死刑?或者说,苏格拉底为什么会死于民主的审判?有人说,苏格拉底的死“在民主身上永远留下了一个污点,这乃是雅典的悲剧性罪行。”他死于民主导致的“多数人的暴政”。
笔者以为,苏格拉底之死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民主,民主本身并没有过错。苏格拉底死于雅典的司法,死于披着民主外衣的审判制度,真正令苏格拉底丧命的是民主的审判,是背离了法的精神和灵魂的雅典“民主审判”。
一雅典审判的程序复杂而表面又处处彰显民主,“有公众法庭制度,这些法庭由全体公民或由全体公民中选出的人们组成,有权审判一切案件,至少大多数案件,包括那些最重大的案件,例如审查政务和财政报告、法律事项以及公私契约。”[4]其实雅典的法庭并不设法官,只设主持官,负责组织审判并维持法庭的秩序,判决的权力则在陪审团。陪审团成员从公民群体中抽签产生。每年初公民自愿报名竞争当年陪审团成员,而后从自愿者中抽出六千人,作为当年陪审团成员。如遇开庭之日,城邦官员实现根据案件大小确定审判每桩案件所需陪审员总人数。开庭之前,再以抽签的方式将这些陪审员分配到不同的法庭,审理不同的案件。判定被告是否有罪的唯一标准是陪审团的投票,如果被告获得的票数占多数,他即获得清白之名,有罪和无罪票数相等时则被告无罪释放;如果判定被告有罪,则由原告和被告本人分别提出具体的刑罚,再由陪审团投票选取其中之一作为最终判罚。固然,这种“民主审判”的程序和方法有合理之处,但却背离法的终极价值。仔细回味苏格拉底受审过程,不难发现雅典“民主审判”制度使得苏格拉底自被起诉之时就已在劫难逃,跌入一个悖论式的怪圈[6]并最终从容就死有其必然性。
其一,在雅典,没有公共检察官或公诉人,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提出控诉。诚然,这与现今“公民逮捕”的法律理论有相似之处——允许任何公民在看到有人犯罪时逮捕他,每个公民都有权利和责任在他认为法律遭到违反的时候提出诉讼,这符合雅典的参与性民主政府的概念[7],但起诉者却难免沾染个人情感偏好。苏格拉底案件中代表人民提起公诉的是三个雅典公民,为首的美莱德斯就与苏格拉底曾有过结,很难要求其完全站在现代公诉人只对法律与事实负责的独立检控立场。
其二,大众司法观念使得陪审团成员任职资格要求几乎为零,陪审团成员并不被要求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和审判能力,且其任期只有一年,而且终身只能担任两次,专业审判知识积累、能力培养无从谈起。
其三,审判就是民主的投票,依据的并不是法律条款,而简单遵从得票的多数与少数。在“苏案”陪审团中,有很多曾被苏格拉底驳斥的哑口无言、被他证明为一无所知却认为自己无所不知的人,这些人对苏格拉底狠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而正是这些人却将决定苏格拉底的生死,苏格拉底岂不注定在劫难逃。苏格拉底在第一轮的投票中以281票比220票被判有罪,然而在提出近乎玩笑的刑罚后惹怒众人,最终以361票比140票被判死刑。其中有80人原先认定苏格拉底无罪,但由于苏格拉底的表现,却在第二轮投票中倒戈,从无罪到死刑的跨越说明众人对苏格拉底的印象、态度成为了判决的根本。
二显然,苏格拉底之死让我们清醒的认识到,雅典司法遗憾的沦为被偏狭的激情左右的民众表达政治意志的工具。在讲求民主的社会中,人民作为主权者掌握公共权力合法性的源泉,而人民赋予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分支合法性的过程始末,我们不难寻觅到民主的踪迹,司法常常通过民主的途径获取正当性,但这并不意味人们行使司法权必须时刻通过民主的手段,民主与司法之间的天然鸿沟使得民主并不可随意侵入司法领域。
首先,民主与司法在自由层面的落脚点不同。民主的本质是人民主权,对民主最简单的理解即是少数服从多数,通常所说的人民当家作主实际就是人们行使其“积极自由”或“政治自由”,去分享社会权力,平等参与政治生活的自由。而现代人的目标是享受有保障的私人快乐;他们把对这些私人快乐的制度保障称作自由[8],即所谓“免于……的自由”的消极自由,苏格拉底之死实际上意味着积极自由或者直接民主剥夺了消极自由。消极自由的充要条件必然是一个人有自己最后的或者最低限度的不可侵犯的领域或者空间,而此项条件最忠实捍卫者便是作为社会生活最终底线的司法。“法律的目的不是要废除和限制人民的自由,而是要保护和扩大人民的自由。……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
其次,民主与司法的终极价值不同。法,其实便是“自然天理”,法起源于人类的“行为习惯”,法的本质就是“公平正义”,而司法的终极价值就是坚持、实现和维护“公平正义”,是一个社会的稳定器。民主的基本追求则是平等,“一个看重正义、法律与自由的国家,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必定是不平等的。”不可以对平等的追求野蛮的替代对公平正义的坚持,人人平等并不等同于公平正义,否则,司法将成为披着民主外衣扼杀少数人自由的刽子手。
其三,对于司法而言,最重要的是根据目的和理性实施法律。司法的本质是理性的判断,因此作为判断主体的法官,其素质高低直接影响司法价值能否真正实现。我们不能排除“苏案”陪审团成员中会有少数司法天才,但我们也不可能指望一个现代国家的司法制度建立在这少数司法天才的基础上。司法的过程是一个依靠理性和知识做出公正判断的过程,是一个不能掺杂个人利害关系在其中的推理过程。而对民主而言,最重要的是实现自身或自己所代表的那部分人的利益,且作为民主主体的人民做出判断时往往带有不理智的随意性,而这种随意性往往显得急躁,使得人民在判断或选择之后通常总会后悔曾经的行为。
三当然,上述论述并不表明司法将完全摈弃民主,否则司法权难以获取合法性。学者陈国刚先生认为,司法遭遇民主后产生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法官如何产生,他认为无论是民主选举还是任命都会引发矛盾性的疑问[11],其实这并不成为问题,他产生这样观点的原由在于孤立的考察法官个体的产生程序,主权者并不是将审判权力逐个给予每一个不论通过何种方式选拔出的法官,法官也不因为成功通过选拔而立即享有审判权力,他也并不是且也并不能用个人名义行使审判权。法官能够进行审判活动是其因获得司法机关中的某个职位从而获取此职位背后隐含的由民主赋予的司法权的使用权。人民将司法权授予司法机关集体,法官不过是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的工具罢了。绝大多数美国公民都倾向于认定辛普森有罪,但当美国法官依据法定程序宣告他无罪时,法官宣布的并不是他个人的判断,而是一个法律或者司法群体的判断,因此,即使这个判断错了,法官也无需对此承担责任,也没有人会因为这个决定事实上有错误而苛责法官。
由上可以引出陈国刚先生的另一个问题,即司法的民主责任。司法向代议机关负责更多意义上是指司法机关就其是否在法律轨道内合法合理运行、其整体行为是否忠实实施由民主制定的法律接受代议机关监督,而此种监督常被误读为个案监督。法院的判决依据的是由民意制定产生的法律,而不是在审判过程中将民意作为判断的条件之一。而且任何判决都难以取得所有当事双方的认同,人民对于司法机关的满意度并不应严格取决于个案判决,否则总会有另一半人(败诉者)对司法持不满意态度。司法的民主责任在于其只对法律负责,以民主基础上产生的法律为准绳,履行公平正义守护神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