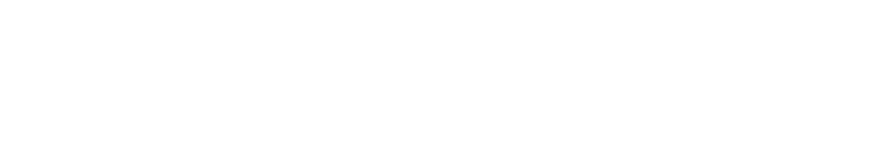超生游击队的故事:不是逃荒要饭-是进城打工
|
||||||||||||||||||
简介:
超生游击队的故事:不是逃荒要饭-是进城打工
1984 进城务工
撰稿 陈文森
1984年10月1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政府积极支持有经营能力和有技术专长的农民进入集镇经营工商业,公安部门应准予其落常住户口,统计为非农业人口,口粮自理。
从此,一部分农民获得了进入城市工作的自由,而且在计划经济的物资供应体制之外,拥有了在城市生存的合法权利。
从1958年就实行的禁止农民进城务工的规定,第一次出现了松动。这一年,外出打工的农民一下子突破了2000万,是1958年到1978年20年总和的20倍。对于这个突然涌现的群体,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雨林在《社会学通讯》上发表文章,第一次提出“农民工”一词,随后,这一称谓被广泛使用。
在“农民工”这个词汇出现之前,形容从农村进城务工者的词语是“盲流”。1990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黄宏、宋丹丹表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为超生四处打工逃避的夫妻俩称自己属于“盲流”——一个在这些人自己看来也是“离流氓不远”的身份。
“盲流”的说法背后,是1953年7月中央政务院发布的《关于制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紧急通知》,所谓“盲流”,其实就是指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之所以要以“盲目”来形容流动的性质,其实多少有些增强“制止”合理性的意思。
1958年1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区分出城市与农村户口,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由于在城市中,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票证都与户口挂钩,没有户口意味着得不到票证,而没有票证就无法获得生存必需品在城市生存,所以从1958年至70年代末,中国几乎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农民自由地流入城市。
到了1984年,放开包产到户后的农村粮食生产以飞速增长。从1982年到1984年,粮食产量从原来不到6000亿斤,连续跨越3个台阶,到1984年超过了8400亿斤。这是建国以来第1次过剩性的粮食供求波动,“粮贱伤农”的市场规律再一次上演,也促使中国的农民开始自发地大幅度调整产业结构,土地已不再是谋生的铁饭碗,而更先进农业技术的引入也使更多劳动力从耕种中脱身。在农民进城务工放开之前,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就已经吸收了大批富余的农村劳动力,闲置的劳动力暗潮汹涌,图谋涌入城市。
此时的城市,基础建设的持续发展和随着全面开放进入的大量外资企业对劳动力形成了巨大的需求。对于外资而言,决定优秀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大量低成本的劳动力,而农村的富余劳动力正是外资企业廉价工人的预备队。而对于城市居民来说,票证制度的逐渐消亡,和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也使得很多城里人做不了或不愿做,但又必须有人做的工作,诸如保姆、木工、清洁工等等岗位出现了用工需求。人口流动政策的适时松动,既有农村的暗潮汹涌,也有城市的劳动渴求。
就这样,随着一座座外资工厂、酒店在中国拔地而起,离开土地的农民们也找到了他们在城镇中的新归宿。当这些农民开始在日商的彩电流水线上焊接电子部件,或在港商的纺织车间里操作织机的时候,他们的身份也从纯粹的农民,转变为持有农业户口但从事工人职业的农民工。事实上,当时也许并没有太多人预料到,80年代初在北京街头推车收废品的河北农民、上海弄堂里抱孩子做饭的安徽姑娘,还有深圳特区建筑工地上扬沙子搬砖的河南汉子,竟在不知不觉中为20多年后中国2亿多外来务工者大军闯荡城市,充当了开路先锋。
第一代的务工者,生活丝毫不比农村轻松。在西安打工已经20年的山阳县农民王伯海,16岁来到西安的第一份工作是往汽车里装沙子,却因为年龄小做不动只作了一天就放弃。他卖过菜,卖过小吃,搬过蜂窝煤,有一次为送煤爬7楼爬了10多次,身上的衣服全部都被汗水湿透,累得流出了口水。当许多人已经用上煤气的时候,他又考了驾照,为别人开出租车,拉乘客时,他一般只是问对方去哪,之后就不怎么说话。“怕人听出我是外地人,欺负我”。在卖小吃的时候,小偷晚上撬开门将床边的三轮车偷走,他却一点也不知道。“你说,累成啥了?睡得多死!但总是要坚持下去,家里这么多人要吃饭、要生活,两个孩子要上学。再累我也没哭过,眼泪只能往肚子里咽。”20年下来,王伯海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他的眼睛时常干涩,每天回家就像瘫了一样动不了。
沿海的务工者则在外资企业的流水线上重复着六七十年代香港、东南亚工人做过的工作,每年春节蜂拥从广东、上海回到老家,过完年又坐上回城市的列车,拥挤的列车、千金难求的车票、摩肩接踵的车站都为“春运”这个词汇提供了最丰富的注脚。
这当中也有些人就此改变了命运。刚过40岁的李兴国从进车间当操作工、在流水线上用小锤子砸鞋底开始,用了11年时间,从一个农民打工仔到车间组长、主管、科长,一直做到生产车间的课长,更被台资公司派往越南、印度尼西亚负责新厂的管理,从河南山村的农民变成了大公司的驻外代表。
第一代农民工虽然已成为职业意义上的城市人,却因为没有城市户口和缺少对城市的文化归属感而难以成为制度和文化上的城市人。他们普遍抱有“到城里挣几年钱,然后回家”,或者“我们怎么能跟城里人比?”等想法。这种以短期赚钱为目的和刻意与城市保持距离的过客心态,不可避免地给城市造成了一些问题。
同样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农民工成了令几乎所有城市的公安、城管部门集体头疼的一类人。破坏城市治安的盗窃、抢劫活动好像总能与他们沾上边,而遍布各处的“城中村”则更是城里人眼中罪恶的渊薮,以及“脏乱差”的代名词。
城市对农村的歧视也在各个层面一览无遗,北京市政府于1985年11月发布的《关于暂住人口户口管理的规定》,使得“暂住证”成为京城直到今天都不能忽视的一大社会现象。
80年代末,在济南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农民工到理发馆,想要剪个平头。理发员见他是个农民,便说,“理个光头不行吗?”当时正值冬季,这位农民工解释道,“剃光头太冷了!”没想到理发员却不高兴了,他没好气地说,“你想理就理个光头,不理光头就另找地方!”接着便招呼下一位顾客。农民工再三恳求,怎奈理发员就是不同意。最后,这位农民工只得离去。就在他走出理发馆大门的时候,那位理发员在他身后说道,“乡巴佬还想学着城里人的样子理平头,没门!也不瞧瞧自己的模样。”这件事发生后,《人民日报》进行了专门的报道,并向全社会提出了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应如何对待农民的问题。
第一代农民工对待这些歧视可能是忍气吞声的,可以“80后”为主力的第二代农民工则不必然。随着父辈们年龄的增大和逐步返回农村,更年轻的一代农村人口陆续进入城市并成为外来务工者的主体。与还留着回乡务农一条后路的父辈不同,在城市文化冲击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务工者既没有务农的经历,也缺乏对农村身份的认同。他们也上网吧、用时新手机、听流行音乐,对工作的期望更高,成为“城里人”的梦想更强烈,对于歧视也更加敏感。
农村的社会形态也在这样的代际更替中发生结构性的变化。老一代的务工者在返回家乡后,往往把一生的积蓄花在医疗、育儿上,而子女外出打工自顾不暇更使得他们缺乏养老的必要保障。新生代的务工者则不再老老实实地待在最脏、最累、最“没出息”的工作岗位上,不再省吃俭用攒钱往家里寄,更不会挣够钱回家盖房娶媳妇。相反,他们会把第三代的子女送回老家让父母抚养,形成“留守家庭”。一到农闲季节,所有农村壮劳力倾巢外出,留下老幼互相扶持,颠覆几千年来农村最基本的家庭形态。留守儿童的心理、教育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无数农民工在辛苦工作一年后拿不到应得的薪水,甚至面临包工头携款潜逃的故事在上世纪末几乎从未停止发生,而层出不穷的农民工迫不得已用暴力甚至血腥讨得工资的新闻也折射出其无奈的辛酸。2003年10月2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重庆市云阳县龙泉村。在向乡亲们询问有什么困难时,农妇熊德明反映包工头拖欠丈夫薪资的问题。在总理的亲自批示下,熊德明夫妇当晚就拿到了全部工资。温总理为农民熊德明讨工资,也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讨薪风暴”。从中央到地方,向农民工按时发放薪资成为政府施政的一个重点。
政府的调整不止于此,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农民工明确划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一部分。“农民工”这个提法也逐渐从官方媒体上隐去,取而代之的是“外来务工者”甚至“新市民”的称呼,农民工当选为各级人大代表,宣传活动这也越来越多出现讴歌“城市建造者”辛劳的节目。20年前调侃“盲流”的小品已不再,取而代之的是王宝强在春晚上扮演的外来务工者小品拿下了收视率第一名。与“外来务工”这个名词一同改变的,是整个中国社会。
新中国人口迁徙简史“五万三千个干部”
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发布,数万名北方干部背井离乡、告别自己的妻子、丈夫、孩子,到南方去接管新解放区,执行土地改革、经济建设、剿灭土匪等任务。在上海和南京,有1万多名青年自愿加入刘伯承、邓小平组建的“西南服务团”,每解放一个县,就留下一些人负责政权组织工作,很多上海青年在解放后就留在了大西南,把家安在那里。从那时开始直至解放后,越来越多的中共干部加入到这支迁移队伍中,他们是新中国最早一批有组织、有计划的移民,人数不多,但却奠定了新中国的政权统治基础。
支援边疆建设
上个世纪50年代,为支援东北工业基地建设、边疆开垦等建设需要,国家组织了大规模的移民。在上海,1950到1956年间有20万名工人被送到华北各地的工业基地;在青海,为了国家的农业垦荒计划,十年间有近百万名青年来到了这里;在黑龙江,有10万官兵奔赴“北大荒”建设国营农场;为了建设新疆,从1949年开始,有数百万的居民迁入这块国家西北边陲之地。如今,新疆建设兵团人口已占到了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人口的七分之一以上。
迁徙自由时期
1954年9月2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了居民有迁徙的自由。这时期,农民能自由的进入城市,统计表明,这也是我国户口迁移最频繁的时期,仅在1954年到1956年的两年之间,就有7700万农民成为了城市居民。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
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联合指示规定了一系列措施,严厉制止农民进入城市,其中包括:交通部门严格检查,民政部门负责遣返“盲流”,公安机关严格控制城市户口,粮食部门不得向“盲流”供应粮食,用人单位一律不得擅自招收工人和临时工。1958年1月9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更是在以法律的形式将城乡有别的户口登记制度与限制迁徙制度固定了下来。
其中第10条第2款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从此,二元户籍制度正式确立。虽然直到1975年宪法才取消了公民的迁徙自由,但公民的迁徙自由从1957年就开始丧失了。
大型水库移民
50年代开始,国家就开始兴建三门峡、刘家峡、丹江口等大型水电工程,诞生大量移民。据统计,解放30年来我国共建设了2000多座规模不一的水电站,共有120多万移民。而90年代开始兴建的三峡工程,动态移民最终达113万人,更是打破了世界水库移民的记录。
大跃进时期
大跃进期间,全国各地掀起一股大干快上的风潮。当时,在国家确定的156个重点项目之外,各县市也确立了不少工业项目,为了尽快“赶英超美”,各地将招工指标大量下放到了农村,很多农民在此期间变成了工人。仅1958年一年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猛增到4532万人,比1957年增加了2000多万。1957年到1960年,城镇人口猛增3124万,达到1.3亿多人。
然而这些项目效益很差,而大量人口聚集在城市,加大了城市福利制度的负担。为缓解这种局面,国家又开始组织部分城镇职工返回农村。据统计,1962年上半年,全国共下放城镇人口2600多万,其中多为前几年招进城市的农民,当时的提法是“增强农业战线的劳动力”。60年代初期开始的返乡潮,也为之后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下放拉开了序幕。
三线建设
1965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其开始的背景是中苏交恶与美国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攻势。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工业迁移和人口迁移过程,其规模可与抗战时期的沿海工业内迁相提并论。
1964年—1980年、贯穿三个五年计划的16年中,中国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投入了2052.68亿元巨资;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上万的民工,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早在50年代,我国就组织青年学生到农村,1955年,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的一批中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这被认为是知青运动的开始,但这时的知青下放还不是强制性的,其动因,也和遣返城镇职工大体相似:缓解城市压力,支援农村建设。直到文革后,知青下放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毛泽东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第二年,大量赋闲在城市的青年下放农村,中学毕业生也被直接分配到了农村,到1971年,有583万青年到农村落户,知青下放达到高潮,直到文革结束才停止。在这场席卷中国的大规模人口迁徙运动中,共有2000万名青年被下放。
干部下放改造
在城镇职工、青年学生纷纷下放的同时,干部也开始了下放。尽管其绝对数量比不上前三者,但也成为了一个奇特现象。“五•七干校”,这一当时主要接受干部家庭下放劳动的地方,成了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词语。
1968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介绍了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柳河兴办“五·七干校”的经验,文章称:“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随后,全国各地都掀起了一场兴办“五·七干校”之风。仅国务院及中央各部委在河北、宁夏、湖南、江西等四省就建设了106所干校,约10万名干部在此进行了“改造”。直到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地五七干校才陆续停办。
打工潮
1984年10月1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政府积极支持有经营能力和有技术专长的农民进入集镇经营工商业,公安部门应准予其落常住户口,统计为非农业人口。
同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还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20多年严苛的城乡隔绝体制终于有所松动。此后几年间,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乡镇转移。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沿海地区的开放,农民涌向沿海的大城市。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打工潮呈波澜壮阔之势。
1993年开始,我国进一步放宽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据农业部抽样调查估计,1997年农民工人数为4461万人,1998年为5481万人,1999年6683万人,2001年为8961万人,2002年为9400多万人,而目前已达1.4亿多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
出国热
比起农民工来,那些更有条件的中国人,选择了出国。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邓小平说:“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要增大”,但在1978年,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地方,也仅有8人申请自费留学。1984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才算真正打开了自费出国留学的大门。此后,出国热一年比一年升温。
在1978到1992年短短的15年中,仅出国留学人员就达16万人之多。“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这是1993年红极一时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台词,加上1996年的《上海人在东京》,热播电视剧再次助推了出国热。如今,中国人出国的动因更加多样化:有为了学习去海外镀金的,有为了移民的,有为了外派海外工作的,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纯粹为了旅游观光。
打工妹翁纯贤回忆28年前的深圳蛇口
网易新闻:1982年,当你刚来蛇口的时候,蛇口是什么样子的?
翁纯贤:当时来深圳这里,一路上都是尘土飞扬的,到蛇口已经是晚上11、12点了,我看到那个工业厂房灯火通明就很兴奋。我从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楼,四层的标准工业厂房。然后日光灯通亮通亮的,感觉很兴奋。因为在内地没有这么大的工厂,这么新的工厂。我们家也有工厂,但是没有四层那么高。
想想当时80年代初期的时候,全国各地都很荒凉,经济很落后。我们的父母辈都算是高工资的,我妈40多块,我爸是50多块,好像已经是最高的了。那个时候我们家住的房子也算大,我跟着外婆住,我父母住学校,我从小跟我外婆住四层楼的,然后79个平方的。所以当时来到这边,真的是很兴奋。
网易新闻:当时你们来的一拨人,后来留下了多少?走了多少?
翁纯贤:第三天就走掉了20多个人。我记得到蛇口的时候是晚上,当时所谓的宿舍其实在当时是一个别墅,可能是中国的第一代别墅吧,比较土,我们就住在那里。第二天一醒过来,哇,我们发现自己住在半山腰,路也没修好,四周野草丛生,底下就是工厂,很偏僻。很多女孩子一下就哭了,觉得特别荒凉。但是我没哭,因为昨天晚上我看了工厂那么漂亮的厂房很兴奋,没有觉得很苦。三天以后每天都有人哭,有人走,不到三个月就走掉了三分之一。
但我妈妈就说既来之则安之,不要动不动就跟着人家回来,你先看一下究竟什么情况。因为我之前跟家里承诺过,我到三个月如果不行就回来。但是一到我就把这句话就忘掉了,我不会回去了。
网易新闻:当你1982年来蛇口的时候,家里人有不同的意见么?
翁纯贤:最开始是我哥哥和外婆不同意,他们觉得这边是资本主义的地方,很危险。不过我家人还是很尊重我的,不会很强硬的要求我怎么样。我父母说我的性格不像个女孩子,像个男孩子。我哥哥就很文静一点,他特别孝顺父母,父母说什么他会听,我不会的,我很叛逆的那种。所以家人也拿我没办法,就让我去了。哥哥是担心我去那里将来会被欺负。
网易新闻:那到什么时候你全家人对你在蛇口打工才觉得比较放心?
翁纯贤:很快吧。那时候我会写信回家,我会把整个工厂的情况,我的工作情况,我的生活情况写信告诉他们。而且我还会买东西托人带回家。一年以后我就让我爸妈和哥哥来这边看看。他们过来一看就笑了,很放心的,说不用担心了,孩子在这里很安全。而且那时候我经常买一些东西寄回去给家里,寄的那些东西可能比我妈一个月买的东西都多吧。
网易新闻:当时都买了些什么给家里?
翁纯贤: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利乐,像现在的饮料,三毛钱一盒,买一个芒果汁,菊花茶,公仔面,牙膏。这个芒果汁和菊花茶是老家汕头没有的,公仔面也是没有的,牙膏有,但是要到外汇店去买的。要买一个手表也没有的,我到这边没多久就托朋友在香港买一个精工表。刚来这边才一个月的时候我就寄一纸盒东西回去了。还有洗衣粉,落地灯,凳子,饭桌。反正那时候寄东西不停的,只要有休息,一下班我就会去小卖部买东西,买完东西存起来,托人带回去。
工作了才几个月过春节的时候我就回过汕头一趟,我整个都已经换了一个面貌了,穿的就跟家里不一样了,穿牛仔裤,穿T恤,很时髦的。打扮什么的都已经跟家乡那边的年轻人完全不一样了。我给所有家里的人都买了东西,我哥哥,妹妹,爸爸,妈妈,所有人我都给他们买衣服了,还买了很多东西送给同学的,买了美加净的发乳,牙膏也买了,很多东西,都不贵,我记得美加净的发乳一盒两块一,我买了很多。
网易新闻:所以基本上你最开始打工的十年里,给家里边添置了很多当时少见的东西?
翁纯贤:对啊。可能两年就把家里所有东西都添置完了。后来家里经济条件慢慢好了,不像前几年,很多东西基本上都有了。记得第一年,第二年,就是我们家有了,邻居家看我们家什么东西这么漂亮,能不能帮我买一个,我说可以呀。帮人家买电饭煲啊,电视,冰箱,洗衣机,什么的。把各种家里的电器都买了。
网易新闻:那最开始来蛇口的那段时间对你个人来说最艰难的挑战是什么?
翁纯贤:最艰难的挑战是没有鱼吃,整天吃肉。
网易新闻:整天吃肉还不高兴?
翁纯贤:因为我们是沿海城市嘛,我们吃鱼吃习惯了,当然有肉也很高兴啊,但是天天吃肉也不习惯。我们是一个外资企业嘛,当时排骨、鸡全部都是从香港进来的,也有菜,就是没有鱼。很想吃鱼。
网易新闻:你大概花多长时间才真正的融入到当时那种新的生活中?
翁纯贤:其实我很快就融入了,我们是4月31号到,正好五一碰上假期,就去海边玩儿,很漂亮的海边,现在你到哪里都找不到这种海边了。第二天到深圳市区,我们说到深圳去,当时只有两趟车,早上是8点半,下午回来是4点半。一个小时到罗湖,逛一下,买东西,当时来的时候带了几十块钱,全部花掉买东西了。(笑)
网易新闻:很多姐妹过来不适应,你却能很快适应,从性格来说,哪些性格特点帮助你适应?
翁纯贤:可能我比较独立吧。从小比较贪玩,而且从小没有在父母身边长大。我们这一代都不是独生子女,都是很多姐妹,我从小没在父母身边长大。这种独立和反叛的性格对我适应新生活很有帮助。
网易新闻:当时如何在工作上慢慢起步的?
翁纯贤:当时是因为我会说普通话。我在家乡我们是讲普通话的,语文课也都是说普通话的,偶尔读一下课文用普通话读。因为我家有亲戚是北方的,我父母又是教书的,我就比其他姐妹的普通话说得更好。当时我们的工厂管理员是香港的,又不会说普通话。所以我刚到这里,上班才第三天我就当上小组长了,负责跟管理层和工人两头沟通。一切就变得很顺利,好像没感觉多苦。
网易新闻:那你了解现在的新一代打工者么?你觉得他们现在的处境跟你当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翁纯贤:说实在的他们幸福多了。现在整个世界环境,周边环境好太多了。比如下班了他们可以去各种地方,可以大量地采购东西。但是他们现在很多工厂,吃的住的是不好,比如现在很多小企业他们的饭堂都没有我们以前的饭堂好,这是两个鲜明的对比。居住环境也是一样,我们那个时候虽然是几个人的宿舍,但是我们是不要钱的,现在人家要钱。最重要的是,那个时候我虽然是一个打工妹,但我依靠打工挣的钱可以成家立业,养活起自己家的人,能买房,能养孩子。现在的打工妹根本不可能买得起房,更不要说养孩子。
网易新闻:同样是在深圳,同样是一些外资企业或者是港资企业,同样是打工,你觉得为什么20年、30年过去了,打工者群体发生这么大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翁纯贤:经济条件不一样,素质不一样。现在的打工妹没有我们那个时候的打工妹那么自觉,那么自爱。我们是很拼命的,有可能是多劳多得的环境下没有人偷懒,现在的人会想尽方法偷懒。那个时候如果我也懂得“炒鱿鱼”,但是上班感觉很好,在这里上班,每天干活,那个时候不懂什么压力的,每天干完活,加班还有加班工资,感觉很好。不会想跳槽。现在的年轻人,三天两头换工作。我们那时还有很多人想读书,读夜校。你要考试,工头不喜欢你参加考试怎么样的,那我就偷着去读书,晚上下班回来,看两三个小时,现在的年轻人在深圳这边好像也不喜欢读书了。
网易新闻:刚来蛇口的时候,有没有设想过五年后是什么样子的,十年后是什么样的,二十年是什么样的?
翁纯贤:有想过。这里变的很快,很快变得很漂亮,虽然没有去过什么大城市,但是在电影里看到的,感觉这里到处都是工地,没过几天又有一栋新楼了。因为蛇口没有多大的高楼,我们星期天就跑到罗湖去,感觉很漂亮。深圳的建楼速度特别快,没几天又有一栋楼,那个时候就想待在这里应该不错。我觉得这里应该是比家里好,然后不到一年就回家探亲了,回到家里就不适应了。你看在这里跟老家简直是两个环境。在这里干活,看每个人干活,每条生产线,干活都是那么卖命,那么勤劳的,上洗手间都是小步跑着去的,很积极的。而回家去一看老家那边的工厂做工磨磨蹭蹭在那里聊天,一看就不习惯。难怪咱们内地的发展速度那么慢,深圳那么快,就是这样的,有一种鲜明的对比。
网易新闻:所以来深圳这28年来你回想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翁纯贤:现在真的有一点既来之则安之那种。虽然前面我很大胆,很叛逆,但是后来我好像没有什么,很平静,不像很多女孩子要出国了,或者自己做生意了,我没想过,没有这种胆量。我有想过,但是觉得那很累,不干了。我没有想过我怎么样,后面该去怎么处理,我没有,好像就是觉得蛮好的,顺着过下去。我有一个一直感觉比较好的,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我都会很认真的做。
网易新闻:那如果现在我们回顾一下,蛇口这28年给你个人最大的收获也好,或者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对你个人来说?
翁纯贤:我觉得不光是蛇口。改革开放这30年带着我成长,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就不会在蛇口,如果没在蛇口我就不会有今天。也许在香港,也许跟很多同学一样下岗了,也许在家里默默无闻的当家庭主妇的。
网易新闻:你后来有见过最开始跟你一批去蛇口的姐妹们吗?你们在一起会聊些什么?
翁纯贤:我们经常回去一帮人聚在一起聊,聊以前怎么样啊,因为现在孩子都比较大了,还是聊以前的事。我们来到这里大概三年以后,汕头经济发展的比较快,外资比较多,那个时间段回去的人特别多。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谈恋爱了,就没想过回去。我们要快结婚了,然后就想算了,回去也没房子,这里两个人就可以拥有一套房子,因为房子的事没有回去。
网易新闻:现在在当年那一批人里面,你觉得你算是幸运的吗?
翁纯贤:应该算幸运的,最后坚持到现在,我比他们,就是可能有一两个比我过的好一点,回家的,但是总体来说我比他们过的比较好一点。
网易新闻:你算成功的吗?自己觉得?
翁纯贤:不算成功,但是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
网易新闻: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吗?
翁纯贤:满意。
网易新闻:你会跟你的孩子讲之前的事情么?
翁纯贤:有时候我们一帮同事聚在一起会说,他会看到一些什么东西他会问,因为以前有一些小玩具或者什么东西,像我的衣服还会放在那边,他说那个时候怎么穿这样的衣服,他就问,我就讲给他听,他也愿意听。
网易新闻:你觉得你的孩子,他能够理解当年你们这一批外来打工者的感情吗?
翁纯贤:他不认同,但是他能理解,为什么这里的人那么勤劳,他也觉得内地的人干活没有这里的人这么认真,这么拼命,他能感觉为什么家里那么落后,他回去就说家里的人就是松松散散的,难怪这么落后。他是在这地出生,在这里长大的。他小的时候很喜欢回老家的,他现在长大了不喜欢了。从上高中开始他就不喜欢,他觉得家里比这里落后多了,然后他觉得家里的人比这里的人懒,他自己这么说。
网易新闻:你们一家人现在完全把深圳当做自己的家?
翁纯贤:对。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因为我觉得我是深圳人。
网易新闻:你介意被当成这几十年外来打工妹的标本吗?
翁纯贤:是打工妹的缩影,没有特别失败,也没有特别成功的,就是规规矩矩的打工妹,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没有什么了不起,规规矩矩的。
翁纯贤,1963年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一教师家庭。
1981年,高中毕业后偶然在马路边看到深圳经济特区第一家港资玩具厂“香港凯达玩具厂”的招工广告,参加招聘考试,成为首批来深的打工者之一。
1982年4月30日,来到深圳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凯达玩具厂,由于普通话说得好,很快成为车缝组组长。
1983年,在到西丽湖游玩过程中,结识来自同一城市,并同在蛇口工业区工作的吴甦峰。吴甦峰是1983年2月来到深圳的,当时他是华美钢厂的一名工人。
1987年2月7日,相恋三年之后,翁纯贤与吴甦峰结婚。
1987年3月,夫妻俩在玫瑰园购买第一套63平米两居室住房,开始快乐的二人世界生活。
1990年2月10日,儿子吴捷骥在蛇口联合医院出生。
1990年,孩子出生后,翁纯贤离开凯达玩具厂,进入南玻集团工作;吴甦峰工作几经变化,先后在远东面粉厂、蛇口工业区结算中心工作,最后调入南山区税务局。
1994年,夫妻俩第一次自费到泰国旅游,此前两人也曾多次出国,但都是单位组织的,这是他们第一次自费出国旅游。
1996年9月,儿子从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第二幼儿园毕业,正式进入学校读书,为庆祝儿子上学,翁纯贤特别把房子重新装修了一遍。
1999年底,购买现在居住的第二套90平米三居室住房。
2000年初,购买家庭第一辆轿车,如今他们已经有了第二辆轿车。
1984 进城务工
撰稿 陈文森
1984年10月1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政府积极支持有经营能力和有技术专长的农民进入集镇经营工商业,公安部门应准予其落常住户口,统计为非农业人口,口粮自理。
从此,一部分农民获得了进入城市工作的自由,而且在计划经济的物资供应体制之外,拥有了在城市生存的合法权利。
从1958年就实行的禁止农民进城务工的规定,第一次出现了松动。这一年,外出打工的农民一下子突破了2000万,是1958年到1978年20年总和的20倍。对于这个突然涌现的群体,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雨林在《社会学通讯》上发表文章,第一次提出“农民工”一词,随后,这一称谓被广泛使用。
在“农民工”这个词汇出现之前,形容从农村进城务工者的词语是“盲流”。1990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黄宏、宋丹丹表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为超生四处打工逃避的夫妻俩称自己属于“盲流”——一个在这些人自己看来也是“离流氓不远”的身份。
“盲流”的说法背后,是1953年7月中央政务院发布的《关于制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紧急通知》,所谓“盲流”,其实就是指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之所以要以“盲目”来形容流动的性质,其实多少有些增强“制止”合理性的意思。
1958年1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区分出城市与农村户口,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由于在城市中,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票证都与户口挂钩,没有户口意味着得不到票证,而没有票证就无法获得生存必需品在城市生存,所以从1958年至70年代末,中国几乎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农民自由地流入城市。
到了1984年,放开包产到户后的农村粮食生产以飞速增长。从1982年到1984年,粮食产量从原来不到6000亿斤,连续跨越3个台阶,到1984年超过了8400亿斤。这是建国以来第1次过剩性的粮食供求波动,“粮贱伤农”的市场规律再一次上演,也促使中国的农民开始自发地大幅度调整产业结构,土地已不再是谋生的铁饭碗,而更先进农业技术的引入也使更多劳动力从耕种中脱身。在农民进城务工放开之前,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就已经吸收了大批富余的农村劳动力,闲置的劳动力暗潮汹涌,图谋涌入城市。
此时的城市,基础建设的持续发展和随着全面开放进入的大量外资企业对劳动力形成了巨大的需求。对于外资而言,决定优秀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大量低成本的劳动力,而农村的富余劳动力正是外资企业廉价工人的预备队。而对于城市居民来说,票证制度的逐渐消亡,和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也使得很多城里人做不了或不愿做,但又必须有人做的工作,诸如保姆、木工、清洁工等等岗位出现了用工需求。人口流动政策的适时松动,既有农村的暗潮汹涌,也有城市的劳动渴求。
就这样,随着一座座外资工厂、酒店在中国拔地而起,离开土地的农民们也找到了他们在城镇中的新归宿。当这些农民开始在日商的彩电流水线上焊接电子部件,或在港商的纺织车间里操作织机的时候,他们的身份也从纯粹的农民,转变为持有农业户口但从事工人职业的农民工。事实上,当时也许并没有太多人预料到,80年代初在北京街头推车收废品的河北农民、上海弄堂里抱孩子做饭的安徽姑娘,还有深圳特区建筑工地上扬沙子搬砖的河南汉子,竟在不知不觉中为20多年后中国2亿多外来务工者大军闯荡城市,充当了开路先锋。
第一代的务工者,生活丝毫不比农村轻松。在西安打工已经20年的山阳县农民王伯海,16岁来到西安的第一份工作是往汽车里装沙子,却因为年龄小做不动只作了一天就放弃。他卖过菜,卖过小吃,搬过蜂窝煤,有一次为送煤爬7楼爬了10多次,身上的衣服全部都被汗水湿透,累得流出了口水。当许多人已经用上煤气的时候,他又考了驾照,为别人开出租车,拉乘客时,他一般只是问对方去哪,之后就不怎么说话。“怕人听出我是外地人,欺负我”。在卖小吃的时候,小偷晚上撬开门将床边的三轮车偷走,他却一点也不知道。“你说,累成啥了?睡得多死!但总是要坚持下去,家里这么多人要吃饭、要生活,两个孩子要上学。再累我也没哭过,眼泪只能往肚子里咽。”20年下来,王伯海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他的眼睛时常干涩,每天回家就像瘫了一样动不了。
沿海的务工者则在外资企业的流水线上重复着六七十年代香港、东南亚工人做过的工作,每年春节蜂拥从广东、上海回到老家,过完年又坐上回城市的列车,拥挤的列车、千金难求的车票、摩肩接踵的车站都为“春运”这个词汇提供了最丰富的注脚。
这当中也有些人就此改变了命运。刚过40岁的李兴国从进车间当操作工、在流水线上用小锤子砸鞋底开始,用了11年时间,从一个农民打工仔到车间组长、主管、科长,一直做到生产车间的课长,更被台资公司派往越南、印度尼西亚负责新厂的管理,从河南山村的农民变成了大公司的驻外代表。
第一代农民工虽然已成为职业意义上的城市人,却因为没有城市户口和缺少对城市的文化归属感而难以成为制度和文化上的城市人。他们普遍抱有“到城里挣几年钱,然后回家”,或者“我们怎么能跟城里人比?”等想法。这种以短期赚钱为目的和刻意与城市保持距离的过客心态,不可避免地给城市造成了一些问题。
同样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农民工成了令几乎所有城市的公安、城管部门集体头疼的一类人。破坏城市治安的盗窃、抢劫活动好像总能与他们沾上边,而遍布各处的“城中村”则更是城里人眼中罪恶的渊薮,以及“脏乱差”的代名词。
城市对农村的歧视也在各个层面一览无遗,北京市政府于1985年11月发布的《关于暂住人口户口管理的规定》,使得“暂住证”成为京城直到今天都不能忽视的一大社会现象。
80年代末,在济南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农民工到理发馆,想要剪个平头。理发员见他是个农民,便说,“理个光头不行吗?”当时正值冬季,这位农民工解释道,“剃光头太冷了!”没想到理发员却不高兴了,他没好气地说,“你想理就理个光头,不理光头就另找地方!”接着便招呼下一位顾客。农民工再三恳求,怎奈理发员就是不同意。最后,这位农民工只得离去。就在他走出理发馆大门的时候,那位理发员在他身后说道,“乡巴佬还想学着城里人的样子理平头,没门!也不瞧瞧自己的模样。”这件事发生后,《人民日报》进行了专门的报道,并向全社会提出了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应如何对待农民的问题。
第一代农民工对待这些歧视可能是忍气吞声的,可以“80后”为主力的第二代农民工则不必然。随着父辈们年龄的增大和逐步返回农村,更年轻的一代农村人口陆续进入城市并成为外来务工者的主体。与还留着回乡务农一条后路的父辈不同,在城市文化冲击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务工者既没有务农的经历,也缺乏对农村身份的认同。他们也上网吧、用时新手机、听流行音乐,对工作的期望更高,成为“城里人”的梦想更强烈,对于歧视也更加敏感。
农村的社会形态也在这样的代际更替中发生结构性的变化。老一代的务工者在返回家乡后,往往把一生的积蓄花在医疗、育儿上,而子女外出打工自顾不暇更使得他们缺乏养老的必要保障。新生代的务工者则不再老老实实地待在最脏、最累、最“没出息”的工作岗位上,不再省吃俭用攒钱往家里寄,更不会挣够钱回家盖房娶媳妇。相反,他们会把第三代的子女送回老家让父母抚养,形成“留守家庭”。一到农闲季节,所有农村壮劳力倾巢外出,留下老幼互相扶持,颠覆几千年来农村最基本的家庭形态。留守儿童的心理、教育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无数农民工在辛苦工作一年后拿不到应得的薪水,甚至面临包工头携款潜逃的故事在上世纪末几乎从未停止发生,而层出不穷的农民工迫不得已用暴力甚至血腥讨得工资的新闻也折射出其无奈的辛酸。2003年10月2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重庆市云阳县龙泉村。在向乡亲们询问有什么困难时,农妇熊德明反映包工头拖欠丈夫薪资的问题。在总理的亲自批示下,熊德明夫妇当晚就拿到了全部工资。温总理为农民熊德明讨工资,也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讨薪风暴”。从中央到地方,向农民工按时发放薪资成为政府施政的一个重点。
政府的调整不止于此,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农民工明确划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一部分。“农民工”这个提法也逐渐从官方媒体上隐去,取而代之的是“外来务工者”甚至“新市民”的称呼,农民工当选为各级人大代表,宣传活动这也越来越多出现讴歌“城市建造者”辛劳的节目。20年前调侃“盲流”的小品已不再,取而代之的是王宝强在春晚上扮演的外来务工者小品拿下了收视率第一名。与“外来务工”这个名词一同改变的,是整个中国社会。
新中国人口迁徙简史“五万三千个干部”
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发布,数万名北方干部背井离乡、告别自己的妻子、丈夫、孩子,到南方去接管新解放区,执行土地改革、经济建设、剿灭土匪等任务。在上海和南京,有1万多名青年自愿加入刘伯承、邓小平组建的“西南服务团”,每解放一个县,就留下一些人负责政权组织工作,很多上海青年在解放后就留在了大西南,把家安在那里。从那时开始直至解放后,越来越多的中共干部加入到这支迁移队伍中,他们是新中国最早一批有组织、有计划的移民,人数不多,但却奠定了新中国的政权统治基础。
支援边疆建设
上个世纪50年代,为支援东北工业基地建设、边疆开垦等建设需要,国家组织了大规模的移民。在上海,1950到1956年间有20万名工人被送到华北各地的工业基地;在青海,为了国家的农业垦荒计划,十年间有近百万名青年来到了这里;在黑龙江,有10万官兵奔赴“北大荒”建设国营农场;为了建设新疆,从1949年开始,有数百万的居民迁入这块国家西北边陲之地。如今,新疆建设兵团人口已占到了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人口的七分之一以上。
迁徙自由时期
1954年9月2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了居民有迁徙的自由。这时期,农民能自由的进入城市,统计表明,这也是我国户口迁移最频繁的时期,仅在1954年到1956年的两年之间,就有7700万农民成为了城市居民。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
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联合指示规定了一系列措施,严厉制止农民进入城市,其中包括:交通部门严格检查,民政部门负责遣返“盲流”,公安机关严格控制城市户口,粮食部门不得向“盲流”供应粮食,用人单位一律不得擅自招收工人和临时工。1958年1月9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更是在以法律的形式将城乡有别的户口登记制度与限制迁徙制度固定了下来。
其中第10条第2款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从此,二元户籍制度正式确立。虽然直到1975年宪法才取消了公民的迁徙自由,但公民的迁徙自由从1957年就开始丧失了。
大型水库移民
50年代开始,国家就开始兴建三门峡、刘家峡、丹江口等大型水电工程,诞生大量移民。据统计,解放30年来我国共建设了2000多座规模不一的水电站,共有120多万移民。而90年代开始兴建的三峡工程,动态移民最终达113万人,更是打破了世界水库移民的记录。
大跃进时期
大跃进期间,全国各地掀起一股大干快上的风潮。当时,在国家确定的156个重点项目之外,各县市也确立了不少工业项目,为了尽快“赶英超美”,各地将招工指标大量下放到了农村,很多农民在此期间变成了工人。仅1958年一年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猛增到4532万人,比1957年增加了2000多万。1957年到1960年,城镇人口猛增3124万,达到1.3亿多人。
然而这些项目效益很差,而大量人口聚集在城市,加大了城市福利制度的负担。为缓解这种局面,国家又开始组织部分城镇职工返回农村。据统计,1962年上半年,全国共下放城镇人口2600多万,其中多为前几年招进城市的农民,当时的提法是“增强农业战线的劳动力”。60年代初期开始的返乡潮,也为之后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下放拉开了序幕。
三线建设
1965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其开始的背景是中苏交恶与美国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攻势。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工业迁移和人口迁移过程,其规模可与抗战时期的沿海工业内迁相提并论。
1964年—1980年、贯穿三个五年计划的16年中,中国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投入了2052.68亿元巨资;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上万的民工,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早在50年代,我国就组织青年学生到农村,1955年,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的一批中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这被认为是知青运动的开始,但这时的知青下放还不是强制性的,其动因,也和遣返城镇职工大体相似:缓解城市压力,支援农村建设。直到文革后,知青下放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毛泽东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第二年,大量赋闲在城市的青年下放农村,中学毕业生也被直接分配到了农村,到1971年,有583万青年到农村落户,知青下放达到高潮,直到文革结束才停止。在这场席卷中国的大规模人口迁徙运动中,共有2000万名青年被下放。
干部下放改造
在城镇职工、青年学生纷纷下放的同时,干部也开始了下放。尽管其绝对数量比不上前三者,但也成为了一个奇特现象。“五•七干校”,这一当时主要接受干部家庭下放劳动的地方,成了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词语。
1968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介绍了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柳河兴办“五·七干校”的经验,文章称:“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随后,全国各地都掀起了一场兴办“五·七干校”之风。仅国务院及中央各部委在河北、宁夏、湖南、江西等四省就建设了106所干校,约10万名干部在此进行了“改造”。直到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地五七干校才陆续停办。
打工潮
1984年10月1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政府积极支持有经营能力和有技术专长的农民进入集镇经营工商业,公安部门应准予其落常住户口,统计为非农业人口。
同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还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20多年严苛的城乡隔绝体制终于有所松动。此后几年间,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乡镇转移。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沿海地区的开放,农民涌向沿海的大城市。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打工潮呈波澜壮阔之势。
1993年开始,我国进一步放宽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据农业部抽样调查估计,1997年农民工人数为4461万人,1998年为5481万人,1999年6683万人,2001年为8961万人,2002年为9400多万人,而目前已达1.4亿多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
出国热
比起农民工来,那些更有条件的中国人,选择了出国。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邓小平说:“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要增大”,但在1978年,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地方,也仅有8人申请自费留学。1984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才算真正打开了自费出国留学的大门。此后,出国热一年比一年升温。
在1978到1992年短短的15年中,仅出国留学人员就达16万人之多。“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这是1993年红极一时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台词,加上1996年的《上海人在东京》,热播电视剧再次助推了出国热。如今,中国人出国的动因更加多样化:有为了学习去海外镀金的,有为了移民的,有为了外派海外工作的,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纯粹为了旅游观光。
打工妹翁纯贤回忆28年前的深圳蛇口
网易新闻:1982年,当你刚来蛇口的时候,蛇口是什么样子的?
翁纯贤:当时来深圳这里,一路上都是尘土飞扬的,到蛇口已经是晚上11、12点了,我看到那个工业厂房灯火通明就很兴奋。我从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楼,四层的标准工业厂房。然后日光灯通亮通亮的,感觉很兴奋。因为在内地没有这么大的工厂,这么新的工厂。我们家也有工厂,但是没有四层那么高。
想想当时80年代初期的时候,全国各地都很荒凉,经济很落后。我们的父母辈都算是高工资的,我妈40多块,我爸是50多块,好像已经是最高的了。那个时候我们家住的房子也算大,我跟着外婆住,我父母住学校,我从小跟我外婆住四层楼的,然后79个平方的。所以当时来到这边,真的是很兴奋。
网易新闻:当时你们来的一拨人,后来留下了多少?走了多少?
翁纯贤:第三天就走掉了20多个人。我记得到蛇口的时候是晚上,当时所谓的宿舍其实在当时是一个别墅,可能是中国的第一代别墅吧,比较土,我们就住在那里。第二天一醒过来,哇,我们发现自己住在半山腰,路也没修好,四周野草丛生,底下就是工厂,很偏僻。很多女孩子一下就哭了,觉得特别荒凉。但是我没哭,因为昨天晚上我看了工厂那么漂亮的厂房很兴奋,没有觉得很苦。三天以后每天都有人哭,有人走,不到三个月就走掉了三分之一。
但我妈妈就说既来之则安之,不要动不动就跟着人家回来,你先看一下究竟什么情况。因为我之前跟家里承诺过,我到三个月如果不行就回来。但是一到我就把这句话就忘掉了,我不会回去了。
网易新闻:当你1982年来蛇口的时候,家里人有不同的意见么?
翁纯贤:最开始是我哥哥和外婆不同意,他们觉得这边是资本主义的地方,很危险。不过我家人还是很尊重我的,不会很强硬的要求我怎么样。我父母说我的性格不像个女孩子,像个男孩子。我哥哥就很文静一点,他特别孝顺父母,父母说什么他会听,我不会的,我很叛逆的那种。所以家人也拿我没办法,就让我去了。哥哥是担心我去那里将来会被欺负。
网易新闻:那到什么时候你全家人对你在蛇口打工才觉得比较放心?
翁纯贤:很快吧。那时候我会写信回家,我会把整个工厂的情况,我的工作情况,我的生活情况写信告诉他们。而且我还会买东西托人带回家。一年以后我就让我爸妈和哥哥来这边看看。他们过来一看就笑了,很放心的,说不用担心了,孩子在这里很安全。而且那时候我经常买一些东西寄回去给家里,寄的那些东西可能比我妈一个月买的东西都多吧。
网易新闻:当时都买了些什么给家里?
翁纯贤: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利乐,像现在的饮料,三毛钱一盒,买一个芒果汁,菊花茶,公仔面,牙膏。这个芒果汁和菊花茶是老家汕头没有的,公仔面也是没有的,牙膏有,但是要到外汇店去买的。要买一个手表也没有的,我到这边没多久就托朋友在香港买一个精工表。刚来这边才一个月的时候我就寄一纸盒东西回去了。还有洗衣粉,落地灯,凳子,饭桌。反正那时候寄东西不停的,只要有休息,一下班我就会去小卖部买东西,买完东西存起来,托人带回去。
工作了才几个月过春节的时候我就回过汕头一趟,我整个都已经换了一个面貌了,穿的就跟家里不一样了,穿牛仔裤,穿T恤,很时髦的。打扮什么的都已经跟家乡那边的年轻人完全不一样了。我给所有家里的人都买了东西,我哥哥,妹妹,爸爸,妈妈,所有人我都给他们买衣服了,还买了很多东西送给同学的,买了美加净的发乳,牙膏也买了,很多东西,都不贵,我记得美加净的发乳一盒两块一,我买了很多。
网易新闻:所以基本上你最开始打工的十年里,给家里边添置了很多当时少见的东西?
翁纯贤:对啊。可能两年就把家里所有东西都添置完了。后来家里经济条件慢慢好了,不像前几年,很多东西基本上都有了。记得第一年,第二年,就是我们家有了,邻居家看我们家什么东西这么漂亮,能不能帮我买一个,我说可以呀。帮人家买电饭煲啊,电视,冰箱,洗衣机,什么的。把各种家里的电器都买了。
网易新闻:那最开始来蛇口的那段时间对你个人来说最艰难的挑战是什么?
翁纯贤:最艰难的挑战是没有鱼吃,整天吃肉。
网易新闻:整天吃肉还不高兴?
翁纯贤:因为我们是沿海城市嘛,我们吃鱼吃习惯了,当然有肉也很高兴啊,但是天天吃肉也不习惯。我们是一个外资企业嘛,当时排骨、鸡全部都是从香港进来的,也有菜,就是没有鱼。很想吃鱼。
网易新闻:你大概花多长时间才真正的融入到当时那种新的生活中?
翁纯贤:其实我很快就融入了,我们是4月31号到,正好五一碰上假期,就去海边玩儿,很漂亮的海边,现在你到哪里都找不到这种海边了。第二天到深圳市区,我们说到深圳去,当时只有两趟车,早上是8点半,下午回来是4点半。一个小时到罗湖,逛一下,买东西,当时来的时候带了几十块钱,全部花掉买东西了。(笑)
网易新闻:很多姐妹过来不适应,你却能很快适应,从性格来说,哪些性格特点帮助你适应?
翁纯贤:可能我比较独立吧。从小比较贪玩,而且从小没有在父母身边长大。我们这一代都不是独生子女,都是很多姐妹,我从小没在父母身边长大。这种独立和反叛的性格对我适应新生活很有帮助。
网易新闻:当时如何在工作上慢慢起步的?
翁纯贤:当时是因为我会说普通话。我在家乡我们是讲普通话的,语文课也都是说普通话的,偶尔读一下课文用普通话读。因为我家有亲戚是北方的,我父母又是教书的,我就比其他姐妹的普通话说得更好。当时我们的工厂管理员是香港的,又不会说普通话。所以我刚到这里,上班才第三天我就当上小组长了,负责跟管理层和工人两头沟通。一切就变得很顺利,好像没感觉多苦。
网易新闻:那你了解现在的新一代打工者么?你觉得他们现在的处境跟你当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翁纯贤:说实在的他们幸福多了。现在整个世界环境,周边环境好太多了。比如下班了他们可以去各种地方,可以大量地采购东西。但是他们现在很多工厂,吃的住的是不好,比如现在很多小企业他们的饭堂都没有我们以前的饭堂好,这是两个鲜明的对比。居住环境也是一样,我们那个时候虽然是几个人的宿舍,但是我们是不要钱的,现在人家要钱。最重要的是,那个时候我虽然是一个打工妹,但我依靠打工挣的钱可以成家立业,养活起自己家的人,能买房,能养孩子。现在的打工妹根本不可能买得起房,更不要说养孩子。
网易新闻:同样是在深圳,同样是一些外资企业或者是港资企业,同样是打工,你觉得为什么20年、30年过去了,打工者群体发生这么大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翁纯贤:经济条件不一样,素质不一样。现在的打工妹没有我们那个时候的打工妹那么自觉,那么自爱。我们是很拼命的,有可能是多劳多得的环境下没有人偷懒,现在的人会想尽方法偷懒。那个时候如果我也懂得“炒鱿鱼”,但是上班感觉很好,在这里上班,每天干活,那个时候不懂什么压力的,每天干完活,加班还有加班工资,感觉很好。不会想跳槽。现在的年轻人,三天两头换工作。我们那时还有很多人想读书,读夜校。你要考试,工头不喜欢你参加考试怎么样的,那我就偷着去读书,晚上下班回来,看两三个小时,现在的年轻人在深圳这边好像也不喜欢读书了。
网易新闻:刚来蛇口的时候,有没有设想过五年后是什么样子的,十年后是什么样的,二十年是什么样的?
翁纯贤:有想过。这里变的很快,很快变得很漂亮,虽然没有去过什么大城市,但是在电影里看到的,感觉这里到处都是工地,没过几天又有一栋新楼了。因为蛇口没有多大的高楼,我们星期天就跑到罗湖去,感觉很漂亮。深圳的建楼速度特别快,没几天又有一栋楼,那个时候就想待在这里应该不错。我觉得这里应该是比家里好,然后不到一年就回家探亲了,回到家里就不适应了。你看在这里跟老家简直是两个环境。在这里干活,看每个人干活,每条生产线,干活都是那么卖命,那么勤劳的,上洗手间都是小步跑着去的,很积极的。而回家去一看老家那边的工厂做工磨磨蹭蹭在那里聊天,一看就不习惯。难怪咱们内地的发展速度那么慢,深圳那么快,就是这样的,有一种鲜明的对比。
网易新闻:所以来深圳这28年来你回想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翁纯贤:现在真的有一点既来之则安之那种。虽然前面我很大胆,很叛逆,但是后来我好像没有什么,很平静,不像很多女孩子要出国了,或者自己做生意了,我没想过,没有这种胆量。我有想过,但是觉得那很累,不干了。我没有想过我怎么样,后面该去怎么处理,我没有,好像就是觉得蛮好的,顺着过下去。我有一个一直感觉比较好的,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我都会很认真的做。
网易新闻:那如果现在我们回顾一下,蛇口这28年给你个人最大的收获也好,或者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对你个人来说?
翁纯贤:我觉得不光是蛇口。改革开放这30年带着我成长,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就不会在蛇口,如果没在蛇口我就不会有今天。也许在香港,也许跟很多同学一样下岗了,也许在家里默默无闻的当家庭主妇的。
网易新闻:你后来有见过最开始跟你一批去蛇口的姐妹们吗?你们在一起会聊些什么?
翁纯贤:我们经常回去一帮人聚在一起聊,聊以前怎么样啊,因为现在孩子都比较大了,还是聊以前的事。我们来到这里大概三年以后,汕头经济发展的比较快,外资比较多,那个时间段回去的人特别多。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谈恋爱了,就没想过回去。我们要快结婚了,然后就想算了,回去也没房子,这里两个人就可以拥有一套房子,因为房子的事没有回去。
网易新闻:现在在当年那一批人里面,你觉得你算是幸运的吗?
翁纯贤:应该算幸运的,最后坚持到现在,我比他们,就是可能有一两个比我过的好一点,回家的,但是总体来说我比他们过的比较好一点。
网易新闻:你算成功的吗?自己觉得?
翁纯贤:不算成功,但是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
网易新闻: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吗?
翁纯贤:满意。
网易新闻:你会跟你的孩子讲之前的事情么?
翁纯贤:有时候我们一帮同事聚在一起会说,他会看到一些什么东西他会问,因为以前有一些小玩具或者什么东西,像我的衣服还会放在那边,他说那个时候怎么穿这样的衣服,他就问,我就讲给他听,他也愿意听。
网易新闻:你觉得你的孩子,他能够理解当年你们这一批外来打工者的感情吗?
翁纯贤:他不认同,但是他能理解,为什么这里的人那么勤劳,他也觉得内地的人干活没有这里的人这么认真,这么拼命,他能感觉为什么家里那么落后,他回去就说家里的人就是松松散散的,难怪这么落后。他是在这地出生,在这里长大的。他小的时候很喜欢回老家的,他现在长大了不喜欢了。从上高中开始他就不喜欢,他觉得家里比这里落后多了,然后他觉得家里的人比这里的人懒,他自己这么说。
网易新闻:你们一家人现在完全把深圳当做自己的家?
翁纯贤:对。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因为我觉得我是深圳人。
网易新闻:你介意被当成这几十年外来打工妹的标本吗?
翁纯贤:是打工妹的缩影,没有特别失败,也没有特别成功的,就是规规矩矩的打工妹,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没有什么了不起,规规矩矩的。
翁纯贤,1963年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一教师家庭。
1981年,高中毕业后偶然在马路边看到深圳经济特区第一家港资玩具厂“香港凯达玩具厂”的招工广告,参加招聘考试,成为首批来深的打工者之一。
1982年4月30日,来到深圳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凯达玩具厂,由于普通话说得好,很快成为车缝组组长。
1983年,在到西丽湖游玩过程中,结识来自同一城市,并同在蛇口工业区工作的吴甦峰。吴甦峰是1983年2月来到深圳的,当时他是华美钢厂的一名工人。
1987年2月7日,相恋三年之后,翁纯贤与吴甦峰结婚。
1987年3月,夫妻俩在玫瑰园购买第一套63平米两居室住房,开始快乐的二人世界生活。
1990年2月10日,儿子吴捷骥在蛇口联合医院出生。
1990年,孩子出生后,翁纯贤离开凯达玩具厂,进入南玻集团工作;吴甦峰工作几经变化,先后在远东面粉厂、蛇口工业区结算中心工作,最后调入南山区税务局。
1994年,夫妻俩第一次自费到泰国旅游,此前两人也曾多次出国,但都是单位组织的,这是他们第一次自费出国旅游。
1996年9月,儿子从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第二幼儿园毕业,正式进入学校读书,为庆祝儿子上学,翁纯贤特别把房子重新装修了一遍。
1999年底,购买现在居住的第二套90平米三居室住房。
2000年初,购买家庭第一辆轿车,如今他们已经有了第二辆轿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