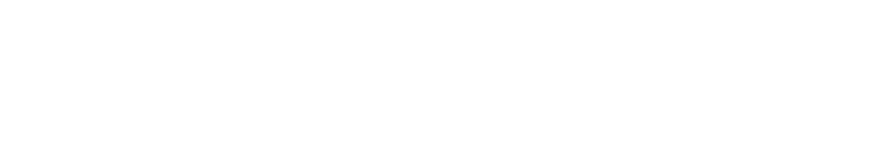当涂县呵:你为什么失去了我心中的丹阳湖?
|
||||||||||||||||||
简介:
当涂县呵:你为什么失去了我心中的丹阳湖?
如今,在早已消失的丹阳湖区和日益缩小的石臼湖区,放眼看到的都是滩涂与水田。

从安徽省当涂县往南,穿过姑孰镇,逆姑溪河而上,沿着小花津去寻找湖山画稿似的丹阳湖,已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站在湖阳大桥上极目远眺,曾经碧波万顷的湖泊早被历史的涂抹改变了模样—滩涂遍地,围网层层。丹阳湖往日风帆出没、远山浮黛的风采,烟波浩渺的磅礴气势,如今只有回到历史的记忆里去探寻。
位于安徽省当涂县东南部的丹阳湖,东靠湖阳镇与石臼湖相通,西邻大公圩东堤埂,北界新市镇,其东南角与江苏省高淳县交界。北面有姑溪河、西南面有水阳江与长江相接。“丹阳旧多红杨,一望皆丹,故曰丹杨,杨与阳同音,遂称丹阳湖”,这就是古称“巨浸”的江南大泽得名的由来。
如今到处是农田和水塘的丹阳湖在历史上经历过由小变大,再变小的过程。丹阳湖的原貌已不复存在,只剩下运粮河道水面与姑溪河相连,运粮河也成了丹阳湖古老历史的见证。
水色傲溟渤的江南“巨浸”
丹阳湖地区古为中江流域,地质构造属于南京凹陷部分,中生代时期曾有多次的垂直上升与下降,最终形成了广袤的冲积平原、湖泊和沼泽洼地,四周高中间低的地势使得皖南之宣城、黄山北麓等地区之水大都汇集于此,逐渐成为皖南山洪的汇集之区、长江西水东流入震泽的通道。
“中江出西南,东至阳羡入海。”《汉书·地理志》中对芜湖地区这样记载。汉代的芜湖县在今芜湖市之东,阳羡在今江苏宜兴以南,此中江之西段正是水阳江与青弋江下游,东段则是当今的胥溪与荆溪,中间连接的便是丹阳大泽。当时由于中江通顺,排水便利,所以丹阳湖面积并不很大。但是随着这一地区陆地的不断下沉,加上气候的变迁以及中江的自然淤积、排水不畅,于是湖泊面积自东汉以后日益扩展,最大湖面积3000平方公里,今丹阳、石臼、固城、南漪四湖以及当涂、宣城、芜湖、溧水、高淳等县沿湖圩区,原均属古丹阳湖地。正如唐《元和郡县志》记述“丹阳湖周三百余里,与溧水(县)分湖为界”,这“三百余里”的丹阳湖谓称中,石臼湖与固城湖自然包括在内。诗人李白留下的“水色傲溟渤,川光秀菰蒲”诗句便成了傲比大海的丹阳湖三百余里湖面风光的写照。
丹阳大泽的分化现象,其实早在春秋晚期已经出现。那个时候的丹阳古地,江湖相连,十分宽阔。而也正是这个时期,古丹阳湖开始瓦解,直到两汉中江淤塞,随水阳江、青弋江而来的泥沙逐年沉积形成湖滩,湖泊才逐渐定型,于是形成石臼、固城等众多湖泊。但由于彼时诸湖之间牵绊相连,所以,那时的丹阳湖仍然呈现出“夏秋一片汪洋,冬春则露滩”的奇美景象。
延至宋代,三湖开始真正走向分离,宋代乐史撰写的《太平寰宇记》开始有了对石臼湖的记载。丹阳、石臼、固城三湖的名称在此时也已经有所专指,不再将丹阳湖作为三湖的统称。此后的几百年间,丹阳湖地的概念更是进一步被分化,且随着生齿日繁,军屯兴起,沿湖的滩地由零星围垦逐渐发展成为连片的圩区,湖泊面积日渐缩小,至今已狭长如带—丹阳湖早已成为一个仅仅用于记忆的地理名词。
渔歌唱晚的圩区和湖滩
沧海桑田,星移斗转,未竟的湖区圩田开发史背后,是丹阳湖畔水乡儿女自力更生、围田造屋的奋斗历程。
圩田是一种在浅水沼泽地带或湖淤滩上通过围堤筑圩,围田于内,挡水于外,围内开沟渠,设涵闸,实现排灌的水利田,是江南地区人民在漫长的治田治水实践中创造出的独特的生存形式。
据当涂县环保局局长杨家金介绍,丹阳湖筑圩肇自三国,迅速发展于唐宋,全盛于明清。三国时期,魏、吴在江淮地区长期对峙,为解决粮秣补给问题,东吴就近在古丹阳湖区屯兵垦殖,从而拉开了丹阳湖圈圩垦殖的序幕,今青弋江、水阳江下游一带的当涂大公圩、宣城金宝圩、芜湖万春圩等圩均始筑于三国东吴时期,而大公圩更可视作历史上江南人民对丹阳湖的围垦之始。
围湖造田、开垦荒滩,造成了丹阳湖面积的不断缩小,然而这却是水乡人民为自己以及后代谋得的生存方式。要在这片沼泽浅滩生活下去,“与水争地”是那时候人们直觉想到,又能付诸行动的唯一方法,就连移民也不例外—这和“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又有什么分别呢?
于是,后来的丹阳湖也就愈发生动热闹了:浩瀚无垠的湖面上,帆樯林立,白鸥点点,日落则渔歌四起,一唱一和,曳声悠扬。当地的老人还说,这里从前不仅琼田万顷、物产丰饶,景色尤其散发水乡灵秀的韵味,夏日莲花盛开,荷叶蔽日,芦苇丛生,家家户户忙着到湖里去采野莲藕、摘红菱角;冬天时,丹顶鹤、白鹳、大雁到湖内越冬,成群的野鸭从东边的石臼湖飞到丹阳湖时,像乌云一样低空掠过,鸣叫声很远也能听见……多少年后,当水乡的人们回过头,看着他们垦荒开发的圩田与湖滩,也许,依然无悔。
丹阳湖地区,史上较大的移民活动共有四次。最大的一次是发生在安史之乱以后的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当时,皖南地区作为接受移民的区域之一,户数激增,人口压力迅速增大。人地的压力也日益显现出紧张的势态,除了加剧与水争地的速度,别无他法。
与此同时,对于三湖的归属问题伴随着当涂、宣城、高淳三县民众的围垦进程日益显现,原本模糊的边界因民众隶属的行政层级的不同而成为矛盾产生的源泉。在这其中,丹阳湖因为本身变动较大,处于三县交界,历史上对其归属一直记载模糊,当人地关系紧张之时,该地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三县民众争夺的焦点。
再加上冬春枯水期,湖泊面积缩减,肥沃的滩地裸露,沿湖居民可以坐船前去收割湖草、芦苇,甚至有的滩地因地势以及肥力而可以收获一季农作物。但是湖泊水位变化不定,裸露的滩地面积也不一而足,随着沿湖居民人口的增加,如何分配这无主滩地上的物产就经常成为沿湖居民纠纷的导火索。
万历初年,高淳县南荡圩杨姓居民越河至当涂县忠惠圩,沿河修筑一道堤埂,以期作为抵挡湖水的外围屏障,以免南荡圩受到湖水的直接冲击,湖阳乡居姓民众随后向当涂县告状,认为杨姓民众“长侵入民人业地”,要求拆除杨姓修筑的堤埂。双方争执不下,引发了一场缠讼17年之久的官司争斗。
万历二十七年(1599)三月,又有当涂县民高富敬状告高淳县民孙庆义越界刈取丹阳湖的湖草一案,最终结果将丹阳湖全部判属当涂县,并且在双方争议之处竖立石碑,“为此令行委官监立禁碑于告争处所,自令二县之民各守疆界,高淳再不许越界混砍茭草,复起争扰。如有故违,定行究处不贷”。
直到清朝嘉庆年间,又爆发了仍以丹阳湖归属问题为焦点的溧水县监生图谋越境刈取湖草案,规模更大,牵涉人员更多。
小花滩血案
丹阳湖区上承皖南之水,下通长江。在夏秋汛期,湖区进水量远远大于出水量,湖面因而迅速扩大。如果在湖区进行开发,建造圩田,使湖的储水容积减小,加上原本排水不畅,就会造成湖区周围圩田的受灾。人们的这种认识当然是在不断的灾害打击下逐渐形成的,在开始的时候大量围湖造田,你争我夺,等到生态环境失衡,遭到大自然报复时,才想到如何去解决,进而走向合作。对于丹阳湖区的开发就是经历了这样一种从争斗到默契形成的过程—“水泛则同禁同采,水涸则各执各业”。
例如明末,中央政府就曾严下禁令,禁止一切对丹阳湖水利有害的行为,允许周边民众在湖中打鱼、取草、放牧、采菱,但是严禁民众进行开垦,甚至特别提到,最近修成的圩田如果影响湖水排泄,就算属富豪之家也要拆毁,这表明了政府禁垦的坚决立场。
因此一直到民国初年,丹阳湖依然保持着这样一种均衡的原始状态。但是随着民国的兴起,规模化经营理念的引进与推广,像丹阳湖这样具有巨大垦殖潜力的地段就成为很多人觊觎的对象,想方设法要圈垦丹阳湖滩地,此时矛盾的双方便成了基层民众与承垦者。
从1925年5月起,垦务公司与丹阳湖地的民众因是否开垦丹阳湖滩而产生的矛盾便一直存在,由于事件涉及省界纠纷而久悬未决。虽然最后由行政院作出裁决,规定一切垦务一律停止,但是垦务公司继续私下执行垦务的行为加剧了民众的不满与恐慌。面对切身利益可能遭受的损害,高淳县民甚至激动高喊“公司有的是金钱,淳民有的是生命,如果政府不爱惜民众生命,我们民众只有仗自己的生命来同金钱争斗”等语句。不久,双方矛盾因为抗战的到来,只得不了了之。
抗战过后,国民政府鼓励恢复生产,兴办实业。丹阳湖滩地纠纷再起。
小花滩血案是民国时期丹阳湖苏皖两省省界纠纷过程中规模最大且结果最为惨烈的一次。
1946年5月,夏旭东、李慰农等组建的利民垦务公司和高淳民众在丹阳湖大滩发生严重的暴力冲突,双方械斗不止。高淳民业麦滩遭毁,损失大小麦六七百担,刈草居民遭拘捕,小花村遭放火,村民遭威吓,高淳农民3人失踪,两人被击毙,尸体被抢;利民垦务公司在此次冲突中死伤50余人,公司经理冯宏全等10余人被囚禁,垦民棚屋计128所被烧毁,物品用具被抢劫一空,重伤者被加以处死,所有尸体被转移。
此次的暴力冲突仍然由垦务公司圈垦丹阳湖滩而起,双方从1942年利民垦务公司强行圈占丹阳湖滩,高淳县民强烈抗议未果开始积怨,至1946年利民公司强行搭棚垦地,矛盾进一步升级,最后引发械斗,血染小花滩。
血案发生后,利民公司和高淳县民都上书国民政府,从各自的角度陈述了此案发生的缘由和经过。双方均各执一词,指责对方为罪魁元凶。苏皖双方为了尽快善后处理小花滩血案,事隔15年之后再次进行两省联合会勘,然而此时利民公司将安澜中学(即今芜湖市第二中学前身)牵涉进来,企图寻求以公益方式开垦丹阳湖。苏皖政府眼见矛盾此起彼伏,为了解决持续不断的丹阳湖垦务纠纷,提请行政院再次划分省界。
事实上,丹阳湖自民国以来的纠纷其症结都是违反丹阳湖永禁开垦的法令,不顾水利进行圈垦。省界划分只不过是图谋侵占湖滩的一种手段而已。如果寄希望于用划界的方式来解决垦务纠纷,“无异于抱薪救火,将来得寸进尺,势必垦荒害熟,自祸祸人”。为此高淳全县民众“为生命之驱迫,誓决挣扎到底”。
后来,政府为了处理这个历史难题,刻意回避“省界划分”的敏感字眼,采取湖泊收归国有的方式,平息了民众的怨气,减少了来自民间的阻力,丹阳湖的开发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名存实亡的丹阳湖
自从民国以来,延续了近30年的丹阳湖省界之争终于尘埃落定,随着边界线的确定,丹阳湖的开发也就除去了最大的阻碍。
村上的老人们告诉笔者,解放初期的丹阳湖滩生长着红菱、莼菜等水生植物,也是野鸭等水禽的栖息之处。汛期鱼类、大龙虾、金脚红毛蟹,洄游湖间,沿湖有“日产斗金”的说法。但湖滩的部分洼地,却是钉螺的巢穴,逐渐蔓延的血吸虫病成了沿湖民众的一块心病。“围湖灭螺”便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大量围垦造田的初衷之一。
1966年12月,解放军南京部队某部报安徽省批准,围垦丹阳湖20平方公里,建造起了丹阳湖军垦农场。此后的许多年,一批又一批青年人潮水一般涌向这里,穿起绿色军装,为防治血吸虫病、开垦条田贡献出青春。
然而,纵横的良田沟渠,交错的“圩子”—丹阳湖早已面目全非,仅剩一条运粮河道,南通水阳江,北接姑溪河,日夜奔流着,向长江呜咽它也曾波澜壮阔的脚步和轨迹。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讲师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徐建平)
如今,在早已消失的丹阳湖区和日益缩小的石臼湖区,放眼看到的都是滩涂与水田。

从安徽省当涂县往南,穿过姑孰镇,逆姑溪河而上,沿着小花津去寻找湖山画稿似的丹阳湖,已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站在湖阳大桥上极目远眺,曾经碧波万顷的湖泊早被历史的涂抹改变了模样—滩涂遍地,围网层层。丹阳湖往日风帆出没、远山浮黛的风采,烟波浩渺的磅礴气势,如今只有回到历史的记忆里去探寻。
位于安徽省当涂县东南部的丹阳湖,东靠湖阳镇与石臼湖相通,西邻大公圩东堤埂,北界新市镇,其东南角与江苏省高淳县交界。北面有姑溪河、西南面有水阳江与长江相接。“丹阳旧多红杨,一望皆丹,故曰丹杨,杨与阳同音,遂称丹阳湖”,这就是古称“巨浸”的江南大泽得名的由来。
如今到处是农田和水塘的丹阳湖在历史上经历过由小变大,再变小的过程。丹阳湖的原貌已不复存在,只剩下运粮河道水面与姑溪河相连,运粮河也成了丹阳湖古老历史的见证。
水色傲溟渤的江南“巨浸”
丹阳湖地区古为中江流域,地质构造属于南京凹陷部分,中生代时期曾有多次的垂直上升与下降,最终形成了广袤的冲积平原、湖泊和沼泽洼地,四周高中间低的地势使得皖南之宣城、黄山北麓等地区之水大都汇集于此,逐渐成为皖南山洪的汇集之区、长江西水东流入震泽的通道。
“中江出西南,东至阳羡入海。”《汉书·地理志》中对芜湖地区这样记载。汉代的芜湖县在今芜湖市之东,阳羡在今江苏宜兴以南,此中江之西段正是水阳江与青弋江下游,东段则是当今的胥溪与荆溪,中间连接的便是丹阳大泽。当时由于中江通顺,排水便利,所以丹阳湖面积并不很大。但是随着这一地区陆地的不断下沉,加上气候的变迁以及中江的自然淤积、排水不畅,于是湖泊面积自东汉以后日益扩展,最大湖面积3000平方公里,今丹阳、石臼、固城、南漪四湖以及当涂、宣城、芜湖、溧水、高淳等县沿湖圩区,原均属古丹阳湖地。正如唐《元和郡县志》记述“丹阳湖周三百余里,与溧水(县)分湖为界”,这“三百余里”的丹阳湖谓称中,石臼湖与固城湖自然包括在内。诗人李白留下的“水色傲溟渤,川光秀菰蒲”诗句便成了傲比大海的丹阳湖三百余里湖面风光的写照。
丹阳大泽的分化现象,其实早在春秋晚期已经出现。那个时候的丹阳古地,江湖相连,十分宽阔。而也正是这个时期,古丹阳湖开始瓦解,直到两汉中江淤塞,随水阳江、青弋江而来的泥沙逐年沉积形成湖滩,湖泊才逐渐定型,于是形成石臼、固城等众多湖泊。但由于彼时诸湖之间牵绊相连,所以,那时的丹阳湖仍然呈现出“夏秋一片汪洋,冬春则露滩”的奇美景象。
延至宋代,三湖开始真正走向分离,宋代乐史撰写的《太平寰宇记》开始有了对石臼湖的记载。丹阳、石臼、固城三湖的名称在此时也已经有所专指,不再将丹阳湖作为三湖的统称。此后的几百年间,丹阳湖地的概念更是进一步被分化,且随着生齿日繁,军屯兴起,沿湖的滩地由零星围垦逐渐发展成为连片的圩区,湖泊面积日渐缩小,至今已狭长如带—丹阳湖早已成为一个仅仅用于记忆的地理名词。
渔歌唱晚的圩区和湖滩
沧海桑田,星移斗转,未竟的湖区圩田开发史背后,是丹阳湖畔水乡儿女自力更生、围田造屋的奋斗历程。
圩田是一种在浅水沼泽地带或湖淤滩上通过围堤筑圩,围田于内,挡水于外,围内开沟渠,设涵闸,实现排灌的水利田,是江南地区人民在漫长的治田治水实践中创造出的独特的生存形式。
据当涂县环保局局长杨家金介绍,丹阳湖筑圩肇自三国,迅速发展于唐宋,全盛于明清。三国时期,魏、吴在江淮地区长期对峙,为解决粮秣补给问题,东吴就近在古丹阳湖区屯兵垦殖,从而拉开了丹阳湖圈圩垦殖的序幕,今青弋江、水阳江下游一带的当涂大公圩、宣城金宝圩、芜湖万春圩等圩均始筑于三国东吴时期,而大公圩更可视作历史上江南人民对丹阳湖的围垦之始。
围湖造田、开垦荒滩,造成了丹阳湖面积的不断缩小,然而这却是水乡人民为自己以及后代谋得的生存方式。要在这片沼泽浅滩生活下去,“与水争地”是那时候人们直觉想到,又能付诸行动的唯一方法,就连移民也不例外—这和“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又有什么分别呢?
于是,后来的丹阳湖也就愈发生动热闹了:浩瀚无垠的湖面上,帆樯林立,白鸥点点,日落则渔歌四起,一唱一和,曳声悠扬。当地的老人还说,这里从前不仅琼田万顷、物产丰饶,景色尤其散发水乡灵秀的韵味,夏日莲花盛开,荷叶蔽日,芦苇丛生,家家户户忙着到湖里去采野莲藕、摘红菱角;冬天时,丹顶鹤、白鹳、大雁到湖内越冬,成群的野鸭从东边的石臼湖飞到丹阳湖时,像乌云一样低空掠过,鸣叫声很远也能听见……多少年后,当水乡的人们回过头,看着他们垦荒开发的圩田与湖滩,也许,依然无悔。
丹阳湖地区,史上较大的移民活动共有四次。最大的一次是发生在安史之乱以后的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当时,皖南地区作为接受移民的区域之一,户数激增,人口压力迅速增大。人地的压力也日益显现出紧张的势态,除了加剧与水争地的速度,别无他法。
与此同时,对于三湖的归属问题伴随着当涂、宣城、高淳三县民众的围垦进程日益显现,原本模糊的边界因民众隶属的行政层级的不同而成为矛盾产生的源泉。在这其中,丹阳湖因为本身变动较大,处于三县交界,历史上对其归属一直记载模糊,当人地关系紧张之时,该地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三县民众争夺的焦点。
再加上冬春枯水期,湖泊面积缩减,肥沃的滩地裸露,沿湖居民可以坐船前去收割湖草、芦苇,甚至有的滩地因地势以及肥力而可以收获一季农作物。但是湖泊水位变化不定,裸露的滩地面积也不一而足,随着沿湖居民人口的增加,如何分配这无主滩地上的物产就经常成为沿湖居民纠纷的导火索。
万历初年,高淳县南荡圩杨姓居民越河至当涂县忠惠圩,沿河修筑一道堤埂,以期作为抵挡湖水的外围屏障,以免南荡圩受到湖水的直接冲击,湖阳乡居姓民众随后向当涂县告状,认为杨姓民众“长侵入民人业地”,要求拆除杨姓修筑的堤埂。双方争执不下,引发了一场缠讼17年之久的官司争斗。
万历二十七年(1599)三月,又有当涂县民高富敬状告高淳县民孙庆义越界刈取丹阳湖的湖草一案,最终结果将丹阳湖全部判属当涂县,并且在双方争议之处竖立石碑,“为此令行委官监立禁碑于告争处所,自令二县之民各守疆界,高淳再不许越界混砍茭草,复起争扰。如有故违,定行究处不贷”。
直到清朝嘉庆年间,又爆发了仍以丹阳湖归属问题为焦点的溧水县监生图谋越境刈取湖草案,规模更大,牵涉人员更多。
小花滩血案
丹阳湖区上承皖南之水,下通长江。在夏秋汛期,湖区进水量远远大于出水量,湖面因而迅速扩大。如果在湖区进行开发,建造圩田,使湖的储水容积减小,加上原本排水不畅,就会造成湖区周围圩田的受灾。人们的这种认识当然是在不断的灾害打击下逐渐形成的,在开始的时候大量围湖造田,你争我夺,等到生态环境失衡,遭到大自然报复时,才想到如何去解决,进而走向合作。对于丹阳湖区的开发就是经历了这样一种从争斗到默契形成的过程—“水泛则同禁同采,水涸则各执各业”。
例如明末,中央政府就曾严下禁令,禁止一切对丹阳湖水利有害的行为,允许周边民众在湖中打鱼、取草、放牧、采菱,但是严禁民众进行开垦,甚至特别提到,最近修成的圩田如果影响湖水排泄,就算属富豪之家也要拆毁,这表明了政府禁垦的坚决立场。
因此一直到民国初年,丹阳湖依然保持着这样一种均衡的原始状态。但是随着民国的兴起,规模化经营理念的引进与推广,像丹阳湖这样具有巨大垦殖潜力的地段就成为很多人觊觎的对象,想方设法要圈垦丹阳湖滩地,此时矛盾的双方便成了基层民众与承垦者。
从1925年5月起,垦务公司与丹阳湖地的民众因是否开垦丹阳湖滩而产生的矛盾便一直存在,由于事件涉及省界纠纷而久悬未决。虽然最后由行政院作出裁决,规定一切垦务一律停止,但是垦务公司继续私下执行垦务的行为加剧了民众的不满与恐慌。面对切身利益可能遭受的损害,高淳县民甚至激动高喊“公司有的是金钱,淳民有的是生命,如果政府不爱惜民众生命,我们民众只有仗自己的生命来同金钱争斗”等语句。不久,双方矛盾因为抗战的到来,只得不了了之。
抗战过后,国民政府鼓励恢复生产,兴办实业。丹阳湖滩地纠纷再起。
小花滩血案是民国时期丹阳湖苏皖两省省界纠纷过程中规模最大且结果最为惨烈的一次。
1946年5月,夏旭东、李慰农等组建的利民垦务公司和高淳民众在丹阳湖大滩发生严重的暴力冲突,双方械斗不止。高淳民业麦滩遭毁,损失大小麦六七百担,刈草居民遭拘捕,小花村遭放火,村民遭威吓,高淳农民3人失踪,两人被击毙,尸体被抢;利民垦务公司在此次冲突中死伤50余人,公司经理冯宏全等10余人被囚禁,垦民棚屋计128所被烧毁,物品用具被抢劫一空,重伤者被加以处死,所有尸体被转移。
此次的暴力冲突仍然由垦务公司圈垦丹阳湖滩而起,双方从1942年利民垦务公司强行圈占丹阳湖滩,高淳县民强烈抗议未果开始积怨,至1946年利民公司强行搭棚垦地,矛盾进一步升级,最后引发械斗,血染小花滩。
血案发生后,利民公司和高淳县民都上书国民政府,从各自的角度陈述了此案发生的缘由和经过。双方均各执一词,指责对方为罪魁元凶。苏皖双方为了尽快善后处理小花滩血案,事隔15年之后再次进行两省联合会勘,然而此时利民公司将安澜中学(即今芜湖市第二中学前身)牵涉进来,企图寻求以公益方式开垦丹阳湖。苏皖政府眼见矛盾此起彼伏,为了解决持续不断的丹阳湖垦务纠纷,提请行政院再次划分省界。
事实上,丹阳湖自民国以来的纠纷其症结都是违反丹阳湖永禁开垦的法令,不顾水利进行圈垦。省界划分只不过是图谋侵占湖滩的一种手段而已。如果寄希望于用划界的方式来解决垦务纠纷,“无异于抱薪救火,将来得寸进尺,势必垦荒害熟,自祸祸人”。为此高淳全县民众“为生命之驱迫,誓决挣扎到底”。
后来,政府为了处理这个历史难题,刻意回避“省界划分”的敏感字眼,采取湖泊收归国有的方式,平息了民众的怨气,减少了来自民间的阻力,丹阳湖的开发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名存实亡的丹阳湖
自从民国以来,延续了近30年的丹阳湖省界之争终于尘埃落定,随着边界线的确定,丹阳湖的开发也就除去了最大的阻碍。
村上的老人们告诉笔者,解放初期的丹阳湖滩生长着红菱、莼菜等水生植物,也是野鸭等水禽的栖息之处。汛期鱼类、大龙虾、金脚红毛蟹,洄游湖间,沿湖有“日产斗金”的说法。但湖滩的部分洼地,却是钉螺的巢穴,逐渐蔓延的血吸虫病成了沿湖民众的一块心病。“围湖灭螺”便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大量围垦造田的初衷之一。
1966年12月,解放军南京部队某部报安徽省批准,围垦丹阳湖20平方公里,建造起了丹阳湖军垦农场。此后的许多年,一批又一批青年人潮水一般涌向这里,穿起绿色军装,为防治血吸虫病、开垦条田贡献出青春。
然而,纵横的良田沟渠,交错的“圩子”—丹阳湖早已面目全非,仅剩一条运粮河道,南通水阳江,北接姑溪河,日夜奔流着,向长江呜咽它也曾波澜壮阔的脚步和轨迹。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讲师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徐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