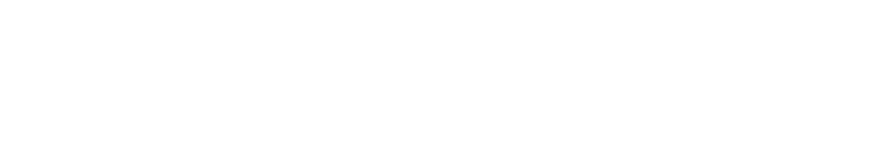王良其律师:关于阿进演出合同纠纷案二审代理词
|
|
|||||||||||||||||
简介:
王良其律师:关于阿进演出合同纠纷案二审代理词
2007-5-18
代 理 词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审判员:
安徽王良其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上诉人徐进(以下简称阿进)的委托,指派本律师作为其代理人参与本案的诉讼活动。根据刚才的法庭调查,本代理人在阿进上诉意见的基础上依法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一、琴港公司与阿进签订的《演出合同书》系现代“卖身契”,属于无效合同
根据刚才的法庭调查,琴港公司在与阿进签订的《演出合同书》第二条规定:“乙方(注:指阿进,下同)为甲方提供的演出期限为:2002年5月11日至2007年5月11日止。”第四条规定:“乙方在琴港期间提前解除或擅自终止合同,须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300万元(叁佰万元)。”第七条规定:“甲、乙双方合同到期后,双方若继续合作,工资报酬由甲乙双方另议。若达不成协议,乙方不得在合肥另一家单位演出。违约须向甲方付违约金人民币300万元(叁佰万元)”。
从琴港公司的上述规定可以得出,阿进自2002年5月11日与琴港公司签订了《演出合同书》后,就与琴港公司有了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即只要当演员就必须在琴港演出,否则就不能在合肥从事演员职业,或要向琴港公司支付300万元的天价代价!这样苛刻的合同规定,客观上让作为职业演员的阿进在合同期满后没有任何选择,只能选择继续给琴港公司充当“演奴”!因此,本代理人认为,琴港公司在与阿进签订的《演出合同书》完全是现代“卖身契”,琴港公司提供的格式化演出合同书,其目的就是为了垄断和限制阿进的演员生涯,其违法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很显然,我国的合同法对于琴港公司的违法行为也是持否定的态度。因此,该“卖身契”性质的演出合同书明显无效。
二、阿进去电视台、广播电台参加演出的行为不构成对琴港公司的违约
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中认为,“琴港公司作为营业性演出场所与徐进订立合同第六条的目的在于限定徐进的演出空间,垄断其表演,确保演出质量,提升并借助其知名度及影响力,形成琴港公司的品牌效应……而自2005年初以来,徐进致合同相对人合同目的落空,其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
本代理人认为,一审法院关于琴港公司合同目的“在于限定徐进的演出空间,垄断其表演,确保演出质量,提升并借助其知名度及影响力,形成琴港公司的品牌效应”的认定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关于阿进“未经琴港公司同意,多次以节目主持人或其他表演者身份在广播电台、电视台及其他场所进行了一系列商业及非商业性演出(直接或借助技术设备以声音、表情、动作当众表现技艺的活动)活动,未能遵守合同第六条关于在合同履行期间其不得擅自在其他单位演出、串场之约定”的认定,一审法院在这里把演出合同中第六条“串场、演出”作了无限制和扩大化地解释,曲解了合同当事人签订合同时的合同原意。
此外,一审法院关于阿进“仅对己方合同的加以关注,而致琴港公司合同目的落空”的认定、以及对阿进构成违约的认定,不仅违背了本案的客观事实,亦违背了合同法的基本规定,同时一审法院还混淆了阿进与琴港公司之间劳务法律关系的性质。
众所周知,对于合同条款的解释,应当依据《合同法》第125条第1款之规定,即“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条款的真实意思”。不仅如此,本案所涉《演出合同书》系由琴港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合同,其中的违约责任规定并不是琴港公司与阿进协商一致的结果。既然本案所涉演出合同系琴港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合同,如果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根据《合同法》第41条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
本代理人认为,琴港公司作为一个以营利为目的演出公司,其与阿进签订演出合同的目的在于:防止阿进到与琴港公司经营同类营业的单位去演出而与琴港公司形成同业竞争,从而导致琴港公司演出收入的减少。这种目的是一种很“实”的目的,而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确保演出质量,提升并借助其知名度及影响力,形成琴港公司的品牌效应”这些很“虚”、且没有事实根据的目的。事实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有关单位与琴港公司不仅不属于同类营业,而且与琴港公司也不构成同业竞争,更不可能分享琴港公司的演出收入利润。
相反,阿进通过去广播电台、电视台等有关单位参加演出,不仅提升了阿进的知名度和观众的认同度,亦带动了琴港公司营业性演出场所的美誉度和知名度,从而更加有利于琴港公司合同目的的实现,增加琴港公司的演出收入。关于这一事实,根据刚才法庭调查过程中的证人证言、琴港公司的相关宣传手册和宣传海报等证据,以及从琴港公司不断在其营业性演出场所附近使用阿进在电视台演出的剧照招揽观众便可得知。
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只是机械地按合同的字面意思去解释合同,这不仅违背了当事人双方在签订合同时的真实目的,而且其结论会变得非常荒谬:即一审法院将合同中的“演出”定义为“直接或间接借助技术设备以声音、表情、动作等表现技艺活动”,如果这种观点能够成立,那么假如阿进参加亲友聚会唱歌或在与朋友相聚KTV唱歌娱乐,难道也属于阿进与琴港公司签订的演出合同中的串场演出吗?也要承担支付300万元违约金的责任吗?
很显然,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认定阿进去广播电台、电视台等有关单位演出构成违约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也是很荒诞的!本代理人认为,根据琴港公司的合同目的,区分是否构成违约的标准,应当是以阿进是否参与了与琴港公司属于同类营业并构成竞争关系的演出单位的演出为标准。
此外,一审法院还认为,“合同第六条将徐进构成违约的时间及空间界定为‘履行合同期间’及‘其他单位’,当事人并无明确意思表示,亦无法推知两概念内涵可被缩小解释为‘约定的具体演出时间’及‘其他营业性演出单位’……”。
本代理人认为,演出合同第六条构成违约的时间和空间不是“被缩小解释为‘约定的具体演出时间’”,而是阿进与琴港公司之间所签订演出合同中的应有之意。因为阿进与琴港公司签订的《演出合同书》第三条约定:“甲方按乙方的演出场次向乙方付劳动报酬,每场的演出报酬为1500元整,按10天结算一次”。
从这一约定可以得出,阿进与琴港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平等主体间的的劳务法律关系,而不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根据《劳动法》所形成的劳动法律关系,即阿进向琴港公司提供的是劳动,而不是劳动力。因此,所谓的《演出合同书》第六条约定的“履行合同期间”,仅仅是指双方约定的、阿进向琴港公司提供演出劳务时的具体时间和空间,而不是指阿进“一天二十四小时”的全部时间和空间。唯有这种解释,才符合双方之间劳务法律关系的应有之意。因为在为琴港公司演出劳务结束后,琴港公司与阿进之间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演出劳务结束后的其余时间双方也就不存在劳务合同关系。
因此,阿进按约定在为琴港公司提供演出劳务结束后,有权支配自已其余的时间和空间参加其他单位的演出而不构成违约。由此可见,一审法院认定阿进在为琴港公司提供演出劳务结束后去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单位去演出构成违约的认定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同时亦混淆了劳务关系与劳动关系的本质区别。
三、在琴港公司没有任何一分钱经济损失的情况下,判决阿进向琴港公司支付违约金90万元无事实根据和显失公平,亦违反合同法有关违约金支付的法律规定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演出合同第六条文义,该条违约金责任的适用仅须徐进具有擅自在其他单位演出、串场的违约行为即可,而与是否致守约方遭受损失无必然联系,此种约定表明,该违约金具有惩罚性。
我国《合同法》突出了违约金具有补偿性,但并不否认民事主体基于真实意思表示作出惩罚性违约金约定的效力,故琴港公司与徐进有权就惩罚性违约金进行约定……”。本代理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演出合同书》第六条的违约金具有惩罚性并确认它的法律效力没有事实根椐和法律依据,同时亦违反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法律规定,而且也是很荒谬的!
《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合同法》第5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合同法》第114条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得出,我国的现行法律对于民事活动的基本要求是公平和等价有偿,不允许有过高的违约金存在。违约金与损失悬殊时可以要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增减。因此,我国合同法中的违约金制度突出的是违约金的补偿性,实质精神是以补偿性违约金为原则的,约定违约金只是合同当事人预先对违约行为所造成经济损失的估算和预定,对于过分高于造成损失的违约金约定,我国的《合同法》等法律并不保护。
从表面上看,一审法院把违约金的数额从300万元减至90万元,但联系本案实际,90万元的违约金仍然属于“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并且达到了显失公平的程度。因为在阿进去广播电台、电视台演出的行为没有给琴港公司造成任何一分钱的经济损失,且琴港公司在诉讼过程中亦没有举出阿进的“违约行为”给其造成经济损失的任何证据。相反,事实上本案当事人都清楚,阿进去广播电台、电视台等相关单位演出的行为,不仅大大提高了琴港公司营业性演出场所的知名度,而且还增加了琴港公司的美誉度,从而必然会增加琴港公司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
否则,我们便不好理解为什么琴港公司不断在其营业性演出场所附近使用阿进在电视台演出的剧照来招揽观众!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一审法院不依据现行法律明确规定,而是通过曲解合同条款,扩大对《演出合同书》第六条规定的串场、演出的范围,轻而易举地为琴港公司赢得了额外的90万元违约金收入。所以,在琴港公司没有任何经济损失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要求阿进向琴港公司支付90万元的违约金不符合《民法通则》及《合同法》第5条、第114条的关于违约金支付的相关规定。
此外,《演出合同书》第六条约定的违约金的违法性亦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即使阿进一年365天每天都演出一场,阿进5年的收入总计也亦不过为274万元,而双方约定的违约金却高达300万元之巨。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判决书中确认的惩罚性违约金亦合法有效的观点,阿进一旦违约、哪怕就是外出演出一场,阿进也要向琴港公司支付300万元的违约金!
由此可见,一审法院在作出一审判决时,根本未考虑民事行为应当遵守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违约金应当具有补偿性等法律基本原则,在琴港公司没有任何损失依据的情况下,判决阿进向琴港公司支付违约金90万元属于很典型的凭空“擅断”!
本代理人认为,违约金的数额与经济损失额应大体一致,这是商品交换等价原则的要求在法律责任上的反映,这是合同正义的内容之一,也是我国合同法所追求的理想之一。违约金的数额过高和过低时要予以调整,其具体标准是过高或过低已经达到了显失公平的程度。
四、阿进与琴港公司之间签订的《演出合同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
本案所涉演出合同签订于2002年,根据“场所和时间支配行为”的适用法律原则,阿进与琴港公司签订演出合同时应当适用1997年国务院发布的《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10条规定:“申请设立营业性文艺表演团体,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审批权限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核批准的,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的……方可从事营业性演出活动……”;第12条规定:“申请设立营业性演出场所,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审批权限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核批准的,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
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的……方可在该演出场所内从事营业性演出活动。”;第17条规定:“个体演员从事营业性演出活动……按照国家规定的审批权限向户籍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核批准,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第35条规定:“营业性演出场所不得为无《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的……或者个体演员以及未经批准的营业性演出活动提供场地服务”;第40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批准,擅自设立营业性演出单位的,或者未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从事营业性演出的,由文化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
很明显,既然营业性演出是政府部门的行政许可行为,《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的上述规定很显然是一种强制性规定。而阿进与琴港公司在签订合同时,琴港公司并不是文艺表演团体,亦未依法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而且阿进作为演员也未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况且双方在签订的演出合同中,琴港公司仅仅是向阿进“提供演出场所”。
因此,阿进与琴港公司在签订演出合同时并不具备《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所规定的举办营业性演出活动的主体资格。显然,作为签约主体的阿进与琴港公司明显表现为演出合同主体不适格,从而违反了国务院颁布的《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作为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52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阿进与琴港公司签订的《演出合同书》属于无效合同。
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演出合同有效,不仅表现为适用法律不当,同时亦直接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明文规定。
琴港公司所举的合肥市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出具的《琴港公司文化经营项目审批情况说明》,本代理人认为,该情况说明不能作为证据。
因为:第一,该情况说明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任何一种法定证据形式,不具有证据的合法性;第二,琴港公司持有的《文化经营许可证》不能替代《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第三,既然营业性演出是政府的许可行为,琴港公司没有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就是违反了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四,合肥市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是内设机构,不是行政法规定的行政行为主体,其没有出具的有关情况说明的主体资格。
很显然,徐进与琴港公司之间签订的《演出合同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
五、一审法院对阿进依法举出的事实证据未能依法认定、对于阿进主张的《演出合同书》第七条为无效条款未予审理,属于程序违法和司法不公。
本案在一审诉讼过程中,阿进依法举出了琴港公司在其营业性营业场所附近使用阿进在电视台演出的剧照来招揽观众的现场照片7幅和宣传海报1幅以及琴港公司的宣传画册等,用以证明琴港公司在履行《演出合同书》过程中并不认为阿进去电台、电视台演出构成违约,也用于证明琴港公司对于阿进参加电视台的演出行为是经过其同意、认可的,阿进不存在“擅自”到其他单位演出或串场事实。
但是,一审法院对于阿进依法举出的这些关键事实证据不仅没有依法采纳,而且在一审判决书中也只字未提。本代理人认为,一审法院对于阿进依法举出的证据无论是否采纳,均应表明其对这些证据的立场;一审法院对于阿进依法举出的证据采取回避的态度只能说明一审法院在诉讼程序上是违法的,同时亦属于司法不公。
此外,一审法院还认为,“本案演出合同第七条关于琴港公司与徐进若不能续签演出合同,则徐进不能在合肥市另一家单位演出,否则应向琴港公司支付违约金300万元的约定,因琴港公司诉请与该条无涉;徐进虽提出无效主张,但并未单独成讼,故本院对此不予审理”。本代理人认为,一审法院对于阿进该条款无效的主张不予审理没有法律依据,而且更加表现出一审法院对于本案的判决存在严重的司法不公。
因为,演出合同第七条是演出合同书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演出合同是否有效,决定是否可以根据该第七条规定续签演出合同。也就是说,本案所涉演出合同有效,该第七条将来便可以适用。此外,演出合同第七条规定的内容,则更进一步证明了琴港公司在签订演出合同过程中严重违反了《民法通则》第4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和原则”、《合同法》第5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也更进一步印证了演出合同第六条所约定的违约金的违法性。
所以,一审法院对于当事人关于演出合同第七条是否有效的争议应当在法律上作出确认以解决纷争。相反,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演出合同合法有效,另一方面对于该条款又不予审理,这种认定结果只会让合同当事人在本案诉讼结束后再燃“战火”,并人为地加大双方的矛盾。与此同时,一审法院该认定的严重司法不公还表现在,该演出合同在将来产生纷争时会作出有利于琴港公司、而不利于阿进的解释和认定。
本代理人认为,一审法院的上述作法,完全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最近倡导的“和谐司法”理念,即肖扬院长所说的“无论是公正高效权威的民事审判制度,还是司法为民、司法民主、司法公开的各项措施,均需要在和谐的诉讼秩序下运行,需要和谐的司法环境提供保障。”肖扬说,“民事诉讼应当是和谐的、有利于纠纷及时了结的诉讼,不应当是相互顶牛的、没完没了的诉讼。”
事实上,我们通过阅读本案一审庭审笔录,一审法院曾经同意将《演出合同书》第七条的合同条款是否有效作为本案的焦点之一,双方对还进行了举证、质证和辩论,但一审法院为什么在一审判决书中又表述“对此不予审理”呢?
六、琴港公司两点上诉理由是毫无事实根据的空穴来风,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1、琴港公司在上诉状中称,“在合同履行期间,上诉人公司斥巨资对被上诉人包装培训,带其外出考察学习,将其从一名摇滚歌手培养成主持人,从一名无人知晓的艺人培养成琴港的知名演员”。
本代理人认为,琴港公司在上诉理由中称其对阿进的培养,不仅没有举出任何可信的事实证据,而且也与其诉讼请求无关。因为本案中琴港公司与阿进之间是劳务合同关系,是否对阿进进行培养,并不是双方在签订《演出合同书》中约定的权利和义务,况且,如果琴港公司要求阿进支付培养费损失,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该项诉讼请求,但琴港公司在本案中并没有提出该诉讼请求。很显然,既然琴港公司没有提出支付培养费诉讼请求,又在这里浓墨重彩毫无意义地大谈其对阿进的培养,琴港公司的这一作法就是妄图把本案的焦点和法官的注意力引入歧途,借以干扰法庭的思路,让人们对阿进产生“忘恩负义”的印象,以期不正当地获得有利于自已的判决结果。
琴港公司在一审过程中虽然举出了合肥市文化局出具的《关于琴港演艺广场经营发展情况的说明》,但该说明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因为:第一,该说明不符合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任何一种证据形式,不具有合法性;第二,该说明都是无事实根据的结论性主观判断,基本上是对琴港公司的溢美之辞,法庭亦无法对其查证,不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和客观性;第三,所要说明的情况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2、琴港公司在上诉状中还称:“被上诉人的恶意违约行为致使上诉人每晚的演出质量下降,严重影响了上诉人公司的正常秩序,在演员和公司内部造成极坏的影响,‘琴港’品牌效应遭到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其违约行为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无法计算”。本代理人认为,根据法庭查的结果,琴港公司在上诉状中的这一段谴责阿进的话,完全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空穴来风!所谓的“损失无法计算”,事实上就是没有损失!
综上所述,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合民二初字第76号民事判决是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结果无法律依据、并明显存在程序违法和司法不公。本代理人请求合议庭依法对该错误判决予以撤销,并依法改判驳回琴港公司的诉讼请求。
以上代理意见,敬请合议庭采纳,谢谢!
代理人:安徽王良其律师事务所
王 良 其 律师
二00七年二月九日
2007-5-18
代 理 词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审判员:
安徽王良其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上诉人徐进(以下简称阿进)的委托,指派本律师作为其代理人参与本案的诉讼活动。根据刚才的法庭调查,本代理人在阿进上诉意见的基础上依法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一、琴港公司与阿进签订的《演出合同书》系现代“卖身契”,属于无效合同
根据刚才的法庭调查,琴港公司在与阿进签订的《演出合同书》第二条规定:“乙方(注:指阿进,下同)为甲方提供的演出期限为:2002年5月11日至2007年5月11日止。”第四条规定:“乙方在琴港期间提前解除或擅自终止合同,须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300万元(叁佰万元)。”第七条规定:“甲、乙双方合同到期后,双方若继续合作,工资报酬由甲乙双方另议。若达不成协议,乙方不得在合肥另一家单位演出。违约须向甲方付违约金人民币300万元(叁佰万元)”。
从琴港公司的上述规定可以得出,阿进自2002年5月11日与琴港公司签订了《演出合同书》后,就与琴港公司有了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即只要当演员就必须在琴港演出,否则就不能在合肥从事演员职业,或要向琴港公司支付300万元的天价代价!这样苛刻的合同规定,客观上让作为职业演员的阿进在合同期满后没有任何选择,只能选择继续给琴港公司充当“演奴”!因此,本代理人认为,琴港公司在与阿进签订的《演出合同书》完全是现代“卖身契”,琴港公司提供的格式化演出合同书,其目的就是为了垄断和限制阿进的演员生涯,其违法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很显然,我国的合同法对于琴港公司的违法行为也是持否定的态度。因此,该“卖身契”性质的演出合同书明显无效。
二、阿进去电视台、广播电台参加演出的行为不构成对琴港公司的违约
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中认为,“琴港公司作为营业性演出场所与徐进订立合同第六条的目的在于限定徐进的演出空间,垄断其表演,确保演出质量,提升并借助其知名度及影响力,形成琴港公司的品牌效应……而自2005年初以来,徐进致合同相对人合同目的落空,其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
本代理人认为,一审法院关于琴港公司合同目的“在于限定徐进的演出空间,垄断其表演,确保演出质量,提升并借助其知名度及影响力,形成琴港公司的品牌效应”的认定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关于阿进“未经琴港公司同意,多次以节目主持人或其他表演者身份在广播电台、电视台及其他场所进行了一系列商业及非商业性演出(直接或借助技术设备以声音、表情、动作当众表现技艺的活动)活动,未能遵守合同第六条关于在合同履行期间其不得擅自在其他单位演出、串场之约定”的认定,一审法院在这里把演出合同中第六条“串场、演出”作了无限制和扩大化地解释,曲解了合同当事人签订合同时的合同原意。
此外,一审法院关于阿进“仅对己方合同的加以关注,而致琴港公司合同目的落空”的认定、以及对阿进构成违约的认定,不仅违背了本案的客观事实,亦违背了合同法的基本规定,同时一审法院还混淆了阿进与琴港公司之间劳务法律关系的性质。
众所周知,对于合同条款的解释,应当依据《合同法》第125条第1款之规定,即“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条款的真实意思”。不仅如此,本案所涉《演出合同书》系由琴港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合同,其中的违约责任规定并不是琴港公司与阿进协商一致的结果。既然本案所涉演出合同系琴港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合同,如果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根据《合同法》第41条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
本代理人认为,琴港公司作为一个以营利为目的演出公司,其与阿进签订演出合同的目的在于:防止阿进到与琴港公司经营同类营业的单位去演出而与琴港公司形成同业竞争,从而导致琴港公司演出收入的减少。这种目的是一种很“实”的目的,而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确保演出质量,提升并借助其知名度及影响力,形成琴港公司的品牌效应”这些很“虚”、且没有事实根据的目的。事实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有关单位与琴港公司不仅不属于同类营业,而且与琴港公司也不构成同业竞争,更不可能分享琴港公司的演出收入利润。
相反,阿进通过去广播电台、电视台等有关单位参加演出,不仅提升了阿进的知名度和观众的认同度,亦带动了琴港公司营业性演出场所的美誉度和知名度,从而更加有利于琴港公司合同目的的实现,增加琴港公司的演出收入。关于这一事实,根据刚才法庭调查过程中的证人证言、琴港公司的相关宣传手册和宣传海报等证据,以及从琴港公司不断在其营业性演出场所附近使用阿进在电视台演出的剧照招揽观众便可得知。
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只是机械地按合同的字面意思去解释合同,这不仅违背了当事人双方在签订合同时的真实目的,而且其结论会变得非常荒谬:即一审法院将合同中的“演出”定义为“直接或间接借助技术设备以声音、表情、动作等表现技艺活动”,如果这种观点能够成立,那么假如阿进参加亲友聚会唱歌或在与朋友相聚KTV唱歌娱乐,难道也属于阿进与琴港公司签订的演出合同中的串场演出吗?也要承担支付300万元违约金的责任吗?
很显然,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认定阿进去广播电台、电视台等有关单位演出构成违约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也是很荒诞的!本代理人认为,根据琴港公司的合同目的,区分是否构成违约的标准,应当是以阿进是否参与了与琴港公司属于同类营业并构成竞争关系的演出单位的演出为标准。
此外,一审法院还认为,“合同第六条将徐进构成违约的时间及空间界定为‘履行合同期间’及‘其他单位’,当事人并无明确意思表示,亦无法推知两概念内涵可被缩小解释为‘约定的具体演出时间’及‘其他营业性演出单位’……”。
本代理人认为,演出合同第六条构成违约的时间和空间不是“被缩小解释为‘约定的具体演出时间’”,而是阿进与琴港公司之间所签订演出合同中的应有之意。因为阿进与琴港公司签订的《演出合同书》第三条约定:“甲方按乙方的演出场次向乙方付劳动报酬,每场的演出报酬为1500元整,按10天结算一次”。
从这一约定可以得出,阿进与琴港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平等主体间的的劳务法律关系,而不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根据《劳动法》所形成的劳动法律关系,即阿进向琴港公司提供的是劳动,而不是劳动力。因此,所谓的《演出合同书》第六条约定的“履行合同期间”,仅仅是指双方约定的、阿进向琴港公司提供演出劳务时的具体时间和空间,而不是指阿进“一天二十四小时”的全部时间和空间。唯有这种解释,才符合双方之间劳务法律关系的应有之意。因为在为琴港公司演出劳务结束后,琴港公司与阿进之间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演出劳务结束后的其余时间双方也就不存在劳务合同关系。
因此,阿进按约定在为琴港公司提供演出劳务结束后,有权支配自已其余的时间和空间参加其他单位的演出而不构成违约。由此可见,一审法院认定阿进在为琴港公司提供演出劳务结束后去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单位去演出构成违约的认定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同时亦混淆了劳务关系与劳动关系的本质区别。
三、在琴港公司没有任何一分钱经济损失的情况下,判决阿进向琴港公司支付违约金90万元无事实根据和显失公平,亦违反合同法有关违约金支付的法律规定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演出合同第六条文义,该条违约金责任的适用仅须徐进具有擅自在其他单位演出、串场的违约行为即可,而与是否致守约方遭受损失无必然联系,此种约定表明,该违约金具有惩罚性。
我国《合同法》突出了违约金具有补偿性,但并不否认民事主体基于真实意思表示作出惩罚性违约金约定的效力,故琴港公司与徐进有权就惩罚性违约金进行约定……”。本代理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演出合同书》第六条的违约金具有惩罚性并确认它的法律效力没有事实根椐和法律依据,同时亦违反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法律规定,而且也是很荒谬的!
《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合同法》第5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合同法》第114条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得出,我国的现行法律对于民事活动的基本要求是公平和等价有偿,不允许有过高的违约金存在。违约金与损失悬殊时可以要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增减。因此,我国合同法中的违约金制度突出的是违约金的补偿性,实质精神是以补偿性违约金为原则的,约定违约金只是合同当事人预先对违约行为所造成经济损失的估算和预定,对于过分高于造成损失的违约金约定,我国的《合同法》等法律并不保护。
从表面上看,一审法院把违约金的数额从300万元减至90万元,但联系本案实际,90万元的违约金仍然属于“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并且达到了显失公平的程度。因为在阿进去广播电台、电视台演出的行为没有给琴港公司造成任何一分钱的经济损失,且琴港公司在诉讼过程中亦没有举出阿进的“违约行为”给其造成经济损失的任何证据。相反,事实上本案当事人都清楚,阿进去广播电台、电视台等相关单位演出的行为,不仅大大提高了琴港公司营业性演出场所的知名度,而且还增加了琴港公司的美誉度,从而必然会增加琴港公司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
否则,我们便不好理解为什么琴港公司不断在其营业性演出场所附近使用阿进在电视台演出的剧照来招揽观众!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一审法院不依据现行法律明确规定,而是通过曲解合同条款,扩大对《演出合同书》第六条规定的串场、演出的范围,轻而易举地为琴港公司赢得了额外的90万元违约金收入。所以,在琴港公司没有任何经济损失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要求阿进向琴港公司支付90万元的违约金不符合《民法通则》及《合同法》第5条、第114条的关于违约金支付的相关规定。
此外,《演出合同书》第六条约定的违约金的违法性亦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即使阿进一年365天每天都演出一场,阿进5年的收入总计也亦不过为274万元,而双方约定的违约金却高达300万元之巨。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判决书中确认的惩罚性违约金亦合法有效的观点,阿进一旦违约、哪怕就是外出演出一场,阿进也要向琴港公司支付300万元的违约金!
由此可见,一审法院在作出一审判决时,根本未考虑民事行为应当遵守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违约金应当具有补偿性等法律基本原则,在琴港公司没有任何损失依据的情况下,判决阿进向琴港公司支付违约金90万元属于很典型的凭空“擅断”!
本代理人认为,违约金的数额与经济损失额应大体一致,这是商品交换等价原则的要求在法律责任上的反映,这是合同正义的内容之一,也是我国合同法所追求的理想之一。违约金的数额过高和过低时要予以调整,其具体标准是过高或过低已经达到了显失公平的程度。
四、阿进与琴港公司之间签订的《演出合同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
本案所涉演出合同签订于2002年,根据“场所和时间支配行为”的适用法律原则,阿进与琴港公司签订演出合同时应当适用1997年国务院发布的《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10条规定:“申请设立营业性文艺表演团体,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审批权限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核批准的,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的……方可从事营业性演出活动……”;第12条规定:“申请设立营业性演出场所,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审批权限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核批准的,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
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的……方可在该演出场所内从事营业性演出活动。”;第17条规定:“个体演员从事营业性演出活动……按照国家规定的审批权限向户籍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核批准,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第35条规定:“营业性演出场所不得为无《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的……或者个体演员以及未经批准的营业性演出活动提供场地服务”;第40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批准,擅自设立营业性演出单位的,或者未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从事营业性演出的,由文化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
很明显,既然营业性演出是政府部门的行政许可行为,《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的上述规定很显然是一种强制性规定。而阿进与琴港公司在签订合同时,琴港公司并不是文艺表演团体,亦未依法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而且阿进作为演员也未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况且双方在签订的演出合同中,琴港公司仅仅是向阿进“提供演出场所”。
因此,阿进与琴港公司在签订演出合同时并不具备《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所规定的举办营业性演出活动的主体资格。显然,作为签约主体的阿进与琴港公司明显表现为演出合同主体不适格,从而违反了国务院颁布的《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作为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52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阿进与琴港公司签订的《演出合同书》属于无效合同。
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演出合同有效,不仅表现为适用法律不当,同时亦直接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明文规定。
琴港公司所举的合肥市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出具的《琴港公司文化经营项目审批情况说明》,本代理人认为,该情况说明不能作为证据。
因为:第一,该情况说明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任何一种法定证据形式,不具有证据的合法性;第二,琴港公司持有的《文化经营许可证》不能替代《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第三,既然营业性演出是政府的许可行为,琴港公司没有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就是违反了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四,合肥市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是内设机构,不是行政法规定的行政行为主体,其没有出具的有关情况说明的主体资格。
很显然,徐进与琴港公司之间签订的《演出合同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
五、一审法院对阿进依法举出的事实证据未能依法认定、对于阿进主张的《演出合同书》第七条为无效条款未予审理,属于程序违法和司法不公。
本案在一审诉讼过程中,阿进依法举出了琴港公司在其营业性营业场所附近使用阿进在电视台演出的剧照来招揽观众的现场照片7幅和宣传海报1幅以及琴港公司的宣传画册等,用以证明琴港公司在履行《演出合同书》过程中并不认为阿进去电台、电视台演出构成违约,也用于证明琴港公司对于阿进参加电视台的演出行为是经过其同意、认可的,阿进不存在“擅自”到其他单位演出或串场事实。
但是,一审法院对于阿进依法举出的这些关键事实证据不仅没有依法采纳,而且在一审判决书中也只字未提。本代理人认为,一审法院对于阿进依法举出的证据无论是否采纳,均应表明其对这些证据的立场;一审法院对于阿进依法举出的证据采取回避的态度只能说明一审法院在诉讼程序上是违法的,同时亦属于司法不公。
此外,一审法院还认为,“本案演出合同第七条关于琴港公司与徐进若不能续签演出合同,则徐进不能在合肥市另一家单位演出,否则应向琴港公司支付违约金300万元的约定,因琴港公司诉请与该条无涉;徐进虽提出无效主张,但并未单独成讼,故本院对此不予审理”。本代理人认为,一审法院对于阿进该条款无效的主张不予审理没有法律依据,而且更加表现出一审法院对于本案的判决存在严重的司法不公。
因为,演出合同第七条是演出合同书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演出合同是否有效,决定是否可以根据该第七条规定续签演出合同。也就是说,本案所涉演出合同有效,该第七条将来便可以适用。此外,演出合同第七条规定的内容,则更进一步证明了琴港公司在签订演出合同过程中严重违反了《民法通则》第4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和原则”、《合同法》第5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也更进一步印证了演出合同第六条所约定的违约金的违法性。
所以,一审法院对于当事人关于演出合同第七条是否有效的争议应当在法律上作出确认以解决纷争。相反,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演出合同合法有效,另一方面对于该条款又不予审理,这种认定结果只会让合同当事人在本案诉讼结束后再燃“战火”,并人为地加大双方的矛盾。与此同时,一审法院该认定的严重司法不公还表现在,该演出合同在将来产生纷争时会作出有利于琴港公司、而不利于阿进的解释和认定。
本代理人认为,一审法院的上述作法,完全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最近倡导的“和谐司法”理念,即肖扬院长所说的“无论是公正高效权威的民事审判制度,还是司法为民、司法民主、司法公开的各项措施,均需要在和谐的诉讼秩序下运行,需要和谐的司法环境提供保障。”肖扬说,“民事诉讼应当是和谐的、有利于纠纷及时了结的诉讼,不应当是相互顶牛的、没完没了的诉讼。”
事实上,我们通过阅读本案一审庭审笔录,一审法院曾经同意将《演出合同书》第七条的合同条款是否有效作为本案的焦点之一,双方对还进行了举证、质证和辩论,但一审法院为什么在一审判决书中又表述“对此不予审理”呢?
六、琴港公司两点上诉理由是毫无事实根据的空穴来风,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1、琴港公司在上诉状中称,“在合同履行期间,上诉人公司斥巨资对被上诉人包装培训,带其外出考察学习,将其从一名摇滚歌手培养成主持人,从一名无人知晓的艺人培养成琴港的知名演员”。
本代理人认为,琴港公司在上诉理由中称其对阿进的培养,不仅没有举出任何可信的事实证据,而且也与其诉讼请求无关。因为本案中琴港公司与阿进之间是劳务合同关系,是否对阿进进行培养,并不是双方在签订《演出合同书》中约定的权利和义务,况且,如果琴港公司要求阿进支付培养费损失,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该项诉讼请求,但琴港公司在本案中并没有提出该诉讼请求。很显然,既然琴港公司没有提出支付培养费诉讼请求,又在这里浓墨重彩毫无意义地大谈其对阿进的培养,琴港公司的这一作法就是妄图把本案的焦点和法官的注意力引入歧途,借以干扰法庭的思路,让人们对阿进产生“忘恩负义”的印象,以期不正当地获得有利于自已的判决结果。
琴港公司在一审过程中虽然举出了合肥市文化局出具的《关于琴港演艺广场经营发展情况的说明》,但该说明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因为:第一,该说明不符合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任何一种证据形式,不具有合法性;第二,该说明都是无事实根据的结论性主观判断,基本上是对琴港公司的溢美之辞,法庭亦无法对其查证,不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和客观性;第三,所要说明的情况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2、琴港公司在上诉状中还称:“被上诉人的恶意违约行为致使上诉人每晚的演出质量下降,严重影响了上诉人公司的正常秩序,在演员和公司内部造成极坏的影响,‘琴港’品牌效应遭到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其违约行为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无法计算”。本代理人认为,根据法庭查的结果,琴港公司在上诉状中的这一段谴责阿进的话,完全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空穴来风!所谓的“损失无法计算”,事实上就是没有损失!
综上所述,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合民二初字第76号民事判决是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结果无法律依据、并明显存在程序违法和司法不公。本代理人请求合议庭依法对该错误判决予以撤销,并依法改判驳回琴港公司的诉讼请求。
以上代理意见,敬请合议庭采纳,谢谢!
代理人:安徽王良其律师事务所
王 良 其 律师
二00七年二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