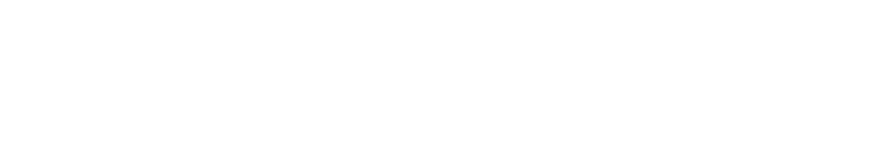|
|
|||||||||||||||||
简介:
里约热内卢 奥运是否会让我们胆颤心惊
——暴力之城 去年5000人死于非命
2009-12-06 10:53:05 来源: 南方都市报(广州)
去年里约热内卢有近5000人在黑帮火并或警方扫荡毒贩的努力中死于非命。巴西成功申办2016年奥运会之时,总统卢拉信誓旦旦要把里约热内卢的贫民区“清洗干净”,举办一届“无暴力奥运会”,他做得到吗?

一场枪战之后,警察将据说是毒贩的死者尸体抬走。
南方都市报12月6日报道 去年里约热内卢有近5000人在黑帮火并或警方扫荡毒贩的努力中死于非命。巴西成功申办2016年奥运会之时,总统卢拉信誓旦旦要把里约热内卢的贫民区“清洗干净”,举办一届“无暴力奥运会”,他做得到吗?
31岁的艾拉是一位苗条少妇,但同时也是一名黑帮分子,作为帮派“纯正第三司令部”的代表,管理着里约热内卢的贫民区帕克罗亚尔。我见到艾拉时,她正在为最小的三女儿举行10周岁生日派对。她穿着T恤、短裤、沙滩鞋,马尾辫上扣着一顶黑色的棒球帽。T恤上有葡萄牙语文字:“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护他们脱离那恶者。约翰福音17:15.”衣服下摆处有个鼓包,那是因为她短裤口袋里有把手枪。
艾拉专门负责处理帕克罗亚尔的“社区关系”。这个职位是新设的,但非常必要。“过去有不少问题,主要是帮派成员对本地居民不够尊重,”她说。艾拉一般通过“谈话”解决问题,但是如果事情太严重,她会“请示山上”———指的是帮派老大费尔南丁所居住的贫民区莫罗丁德。头天就出了一点事:“有个男人打他老婆。她想离婚,他就把她揍了一顿。”艾拉没说事情是怎么解决的,但总之是解决了。
我们正在贫民区中穿行———到处是铁皮和砖头搭成的握手楼,电线四处乱搭,吓人地垂着,墙上满是涂鸦,窄巷里开满了小商店和装修粗劣、专卖啤酒和巴西朗姆酒的小酒吧。帕克罗亚尔所在地方过去是一片遍布红树林的沼泽,艾拉的家就在海湾边一条遍布垃圾的小道旁。空气中飘着一股污水的恶臭,但周围的人似乎毫无感觉。全副武装的年轻人———来自艾拉帮派的毒贩子———守卫着这条窄巷。她跟他们说了几句话,以免他们伤害我。
艾拉的左臂文着一只黑色的蝎子,环以她最爱的人的姓名缩写:三个女儿、妈妈、姐姐、外甥女和外甥。艾拉一岁时,父亲就丢下她母亲走了。妈妈是个酒鬼,她说,“但现在不喝了,信了教。”少女时艾拉加入了足球队,踢得不错,能跟职业球员比赛。她甚至上过电视,但哥哥为此打她,“他说我是个女同性恋。”
于是14岁时艾拉加入了“纯正第三司令部”。“我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哥哥殴打,同时赢得尊敬,”她说:“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受到他的骚扰。”艾拉的哥哥现在班古,里约热内卢西边的一个监狱,巴西大部分帮派分子都在那儿服刑,因此该监狱也是在黑帮控制之下。“他是第六次进去了,”她说:“又贩毒又抢劫。”
艾拉的大女儿过来跟她说了些什么。她穿着粉色的T恤和短裤。女儿离开后,艾拉骄傲地说:“她是个好女孩,非常负责任。她甚至会责备我。”作为黑帮派驻帕克罗亚尔的管理人员,艾拉每周可以拿到大约250美元的薪水。加上贩毒分成,通常每周可以赚到500美元左右,足够养家。“唯一的问题是我吸毒,”她大笑起来:“如果按我自己的意思,每天吸四次就够了,但问题是,不管我什么时候出去,总有人请我吸。”
她说,本来去年她已经“金盆洗手”,但她的继任者后来被人打死,帮派另一个头目吉尔伯托(人称吉尔)要求她回到工作岗位上,她只好照办。吉尔是费尔南丁从小玩到大的好友,据说比费尔南丁还要暴力。
艾拉不怎么考虑未来。她能想象的最完美生活就是“活着,跟我的女儿们在一起。”
稍后她主动说出,跟大女儿差不多年纪时,她被人强奸了。“我当时太小了,所以他用一把刀割开我的阴道。”她说:“我缝了七针,在医院住了一星期。”后来,她离家和另一个人同居,“他就是我女儿们的父亲,人不错。”但他吸毒太厉害,一段时间后,她又离开了他。现在独自生活。
我问艾拉是否信教。她说不,尽管有时会陪姨妈上教堂。她很喜欢西德尼牧师,当地福音教会一个很受欢迎的传教士。“因为他愿意跟每个人说话,如果有人要被处死,他会去跟老大讲情,”她说。
帕克罗亚尔位于巴西东南部瓜纳巴拉湾中最大的岛屿总督岛。该岛因殖民时代一个葡萄牙总督而得名,此人在那里建了一个蔗糖加工厂。现在岛屿位于正在扩张的里约热内卢边缘,通过桥梁和公路与陆地相连。加利昂国际机场就在那里,此外还有一个空军基地、一个自然保护区、一个造船厂、一些石化厂,以及差不多50万居民,其中约20%住在贫民区。
里约热内卢第一批贫民区的出现要上溯至1888年,巴西废除奴隶制那一年。获得自由的奴隶们没有栖息之所,只好在山坡的开阔地或部分排干水的沼泽地上建起了简陋的棚屋。随后失业的士兵和大批涌进城市的农民陆续加入他们的行列。20年前,据说在里约热内卢有300个贫民区;10年前这一数字攀升到了600个。没人知道今天这里到底有多少贫民区,但估计至少有1000个,里约热内卢1400万居民中可能有300万住在这样的地方。
在里约热内卢,贫民区靠着机场高速向远方蔓延。子弹时不时在头顶呼啸,那是敌对黑帮守在高速两边,互相对射。他们还常持枪到路上抢劫司机。大部分观光客会直接从机场前往位于里约热内卢南部富裕的Zona Sul区住宿,但Zona Sul也有贫民区,总之你无法完全无视里约热内卢的痛苦。
由于黑帮不断扩张,贫民区的居民事实上生活在黑帮老大私人武装的管治下。艾拉的“老大”费尔南丁是个31岁的毒贩,总督岛有18个贫民区,几乎全被他的“纯正第三司令部”控制。除了卖毒品,他还从合法商户那里收取保护费。2007年,警方估计费尔南丁每月贩毒所得约为30万美元,其他方面的收入还要远远超过这个数。他父亲是个砖匠、酒鬼,常常虐待他和他妈妈,现在已经死了。费尔南丁的妈妈靠当收银员生活,据说拒绝儿子给她的钱。
尽管到处贴着通缉令,费尔南丁却公开居住在莫罗丁德。警方曾数次采取重大行动,想抓住或杀掉费尔南丁。2005年11月,在费尔南丁举行27岁生日派对前夜,警方突袭了莫罗丁德,没有抓到他,只是没收了10000罐啤酒。2007年警方再次行动,当时费尔南丁在举行另外一个派对,庆祝主要对手马塞洛M arcelo PQ D被抓。他再次成功逃脱。
“纯正第三司令部”最初是“红色司令部”的一个分支,后来独立出来。“红色司令部”是里约热内卢毒品集团中资历最老、势力最大的一个。它源自一个囚犯组织,1979年建立,当时普通罪犯和政治激进分子一起被关押在里约热内卢西部的大总督岛上的卡迪诺·蒙德斯监狱。该监狱号称巴西的“恶魔岛”,从1964年到1985年统治巴西的军事独裁政权专门在这里关押游击队员。
“红色司令部”的创立者从共产主义狱友那里学得了一些组织技巧和社会思想,甚至采用了“和平、公平和自由”的座右铭,到现在仍然保持。但到了1980年代中期,“红色司令部”和其分支已经完全放弃了任何政治主张。今日这个帮派纯粹是犯罪组织,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向巴西的同胞们卖毒品。
和哥伦比亚、墨西哥以“出口”为导向的毒品集团不同,里约热内卢的黑帮全是批发进口商———从玻利维亚、秘鲁和哥伦比亚买进可卡因,从巴拉圭买进大麻———同时也是毒品零售网络管理商。至少有10万人为里约热内卢的贩毒集团工作,层次结构分明,完全效仿企业:贫民区的头头们是gerentes gerais,即总经理,他们的代表是sub-gerentes,副总经理,黑帮老大是donos,即董事长。
当我到里约热内卢北部一个小山上的另外一个贫民区参观时,一个名叫西科利亚的女士告诉我,“纯正第三司令部”控制着山顶地区,而山坡部分是“红色司令部”的地盘。“在这儿,我们绝对不能穿红的。”她说:“弗拉明戈队球迷也只穿红黑相间的球衣,但不能只穿红的。”曾有个女孩穿着红衣服上山,“他们没有杀掉她,因为她是一名福音教会信徒,但把她的衣服割得乱七八糟。”去年一天,帮派分子把一个女孩的指甲拔了下来,因为她涂着全红的指甲油。“现在我们都不用指甲油了,”西科利亚说。管着山顶的帮派小头目是她开办的社区中心计算机班的毕业生,因此他手下的人一般不来骚扰,让她安心工作。
在贫民区,政府几乎完全缺位。贩毒集团在这里按自己的一套来“执法”和收税,他们有武力作后盾。和墨西哥一样,巴西很多走私武器来自美国,近年来俄罗斯军火也开始在黑市出现。黑帮装备有机枪和防空武器,半自动步枪和手榴弹更是司空见惯。
在“暴力致死”榜单上,里约热内卢在全球城市中名列前茅。根据官方数字,去年只发生了近5000起谋杀事件,其中一半与毒品集团有关。22名警察遇害,同样这里的警察干掉的人也比任何地方的同行都多———2008年,他们承认杀死了1188名“拒捕者”,平均每天三个多一点(美国警察同期只“正当杀害”了371个人),此外“流弹”每天还要杀或伤至少一个人。不管以何种标准衡量,里约热内卢的公共安全都是一场灾难。
“里约热内卢有些区域整个都由不属于国家的武装力量控制,这是世所罕见的现象,”里约热内卢议员阿尔弗雷德·瑟吉斯说,他过去曾是一名游击队员。“现在最小的毒品集团都比我们以前拥有的武器多。我们一般只有一把步枪、两挺机枪和两枚手榴弹,靠这个把整个国家搅得风生水起。”他摇摇头:“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手里有枪的人不想搞革命,他们想的是赚钱花钱。这在精神上像孩子一样幼稚,而且他们也像孩子一样随意杀人。”他说,这些人如果掌握了某种意识形态,就会威胁到国家。“目前他们还是乌合之众,想得到的无非是衣服、汽车和一点尊重。”
58岁的瑟吉斯出生于里约热内卢。他父母是波兰犹太人,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后移民巴西。作为1960年代末的大学生,瑟吉斯加入了“人民革命先锋”,一个城市游击组织。他抢过好几家银行,还绑架过瑞士及德国驻巴西大使。1971年,当他的同志们被追捕和杀害时,瑟吉斯逃离巴西,在圣地亚哥、布宜诺斯艾利斯、巴黎和里斯本度过等地流亡将近9年,军政府发布特赦令后才回来。在1980年出版的一本畅销书中,瑟吉斯批判了政治暴力主义。现在他是一名环保分子,巴西绿党领导人之一,1998年曾作为绿党候选人竞选总统。
7月10日,瑟吉斯儿子的一个好友,一个年方22岁的大学生,在里约热内卢被杀害,尸体在一辆出租车上被发现,他和司机都被射杀。瑟吉斯给报社写了一封信,指出这样的事件已经变得如此普通,甚至都不成为新闻。他告诉我:“里约热内卢的破案率是很可笑的———90%的谋杀案都成了悬案。”他说,这部分应归罪于巴西的“政治正确文化”,“里约热内卢精神分裂。每个人都讲究政治正确,将暴力视作某种不公平导致的结果。与此同时,他们又希望贫民区被夷为平地。”
瑟吉斯还将里约热内卢黑帮的壮大与“基地”对一些年轻人的吸引联系起来。“这是一种不断催生年轻暴徒的文化,”他说:“男孩们都羡慕手持A R-15、穿着耐克鞋的毒贩子,觉得很神气,可以吸引女孩,赢得同龄人的尊重。”他说黑帮成员近年来越来越小,有的只有10岁。
费尔南丁控制总督岛后不久,就上了里约热内卢报纸头条。这一代黑帮成员喜欢开派对,追捧一种名为carioca的说唱乐,周末会举行大型街头派对,提供啤酒,出售毒品,吸引贫民区内外的年轻人。费尔南丁被人拍到和手下的“战士”同乐,一起喝酒、唱歌、吹牛是如何把对手赶走的。在2005年拍的一段视频上,费尔南丁对着麦克风说唱:“我充满了仇恨。我是个好人,但我不是个软蛋。我告诉每个人,我这个人不坏,不坏。我不喜欢PQ D和N oquinha,如果你站在他们一边,我就把你剁成碎片。你可以跟他们,可是一旦被我捉到,狮子就把你吃掉。”
抓捕费尔南丁的第一份通缉令就是那年发出的。在附近的贫民区普拉亚发现了两具被肢解的尸体。受害者是N oquinha(费尔南丁在说唱中提到的对手)的助手;2007年,一名警察在一个宗教庆典上公然被人杀害;几个月后,莫罗丁德一名男子被斩首,罪名是参与了一个敌对帮派举行的街头派对。事件中费尔南丁的手下都是首要怀疑对象。当地一名居民告诉我,在普拉亚,费尔南丁的手下被称为“屠夫”。“他们会把杀掉的人斩成碎块,扔到海里,给螃蟹吃,”这个人说。
2008年3月,在两架武装直升机和一台装甲车的支援下,100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出动,围住一所房子,抓捕费尔南丁。5名黑帮成员被打死,好几个受了伤。警方说费尔南丁也中了弹,但是跳上房顶逃掉了。
有关费尔南丁的报道———他的挥霍、他喜欢肢解对手的怪癖、他奇迹般的逃生经历———开始催生一种神话。接下来的故事是:费尔南丁皈依了宗教。2007年8月20日,里约热内卢小报M e iaH ora头条标题是:“暴徒斩首异端”,小标题说:“莫罗丁德的老板费尔南丁·瓜拉布用一把斧头处死了受害者。这些信奉福音教会的毒贩子甚至禁止贫民区举行马库姆巴(巴西黑人一种宗教仪式)”。费尔南丁跟西德尼牧师变得很友好,他以极大的热情追随新的信仰。他在前臂上文上大大的字母“Jesus Cristo”,他所居住的贫民区被宗教涂鸦所覆盖。据说费尔南丁还命令手下不要犯“暴力罪行”,比如抢劫、谋杀,虽然他还在贩毒。
莱斯利·莱托是巴西日报O D ia头号记者,该报大部分有关费尔南丁的报道都是他写的。我去报社找他。莱托说,他经常到巴西最受欢迎的社交网站Orkut上收集材料,警方也经常在这里寻找线索,因为很多帮派成员会在这儿贴消息、视频和照片。莱托本人从未去过莫罗丁德,只在电话里和费尔南丁交谈过。自从O G lobe电视网著名记者提姆·洛佩斯于2002年神秘消失,巴西的记者们都不再敢去贫民区。当时提姆带了一个偷拍摄像机,参加贫民区举行的一次派对。几天后,洛佩斯的尸体被发现,他是被折磨致死的———受过毒打,然后被一把日本短剑割成碎片,然后遭到焚烧———施暴者是“红色司令部”。
对于记者而言,危险不仅来自黑帮。去年,O Dia两名记者和他们雇的司机在贫民区被绑架并折磨了几个小时。折磨他们的人后来身份泄露,证明是警察,一个民兵组织的成员。大概10年前,警察和消防员成立了这样的组织,目的是打击毒品集团,暗杀黑帮分子,直到他们被“清除”。现在里约热内卢至少有100个贫民区处于这些组织的控制之下,结果这些组织自己也成了某种帮派。总督岛唯一不在费尔南丁控制下的贫民区位于空军基地外,处于民兵组织掌握之下。
“现在如果你住在莫罗丁德就必须投靠费尔南丁,”莱托说。他不知道费尔南丁的宗教信仰是出于真心还是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公众形象,“可能两者兼有吧,”他说。
为了进一步了解费尔南丁,我找到一位前毒贩,人们都叫他“大豆”。此人矮小壮实,33岁,穿着耐克运动服,戴着粗大的金链,曾是“纯正第三司令部”一名小头头,但是后来“退休”,试图“转型”为一名房地产发展商。不过,警方依然在通缉他,2006年他被逮捕,罪名是盗窃军火。“大豆”把大部分积蓄花在了诉讼上,蹲了一个月监狱后获释,现在他在为非政府组织A froReggae工作,该组织试图在政府和黑帮之间进行调停,为双方筑起一道沟通之桥。
“大豆”说,他与费尔南丁相识多年。“他是一个疯子!”他说:“他嗜好抽烟喝酒,太热衷于举行派对了。他有好的一面,但也有残忍的一面。他杀了很多人,把他们的尸体丢在街上,他老是上报纸,老是有他肩膀上扛着枪跳舞的照片。他有很多武器,还有偷来的汽车。问题就是,如果你干了太多这样的勾当,他们就会盯着你不放,直到把你抓住为止。如果费尔南丁进去了,他恐怕就出不来了。”
我问“大豆”是否认为费尔南丁广为宣传的宗教信仰是真的。他沉思了一下,说:“我想他可能真的相信,因为在这样的生活中,你很快就会懂得,只有上帝才不会背叛你。”
据说在费尔南丁的皈依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西德尼牧师住在帕克罗亚尔,距艾拉的住所只有几条街。他穿着黑色裤子,熨得平平整整的米色衬衫,打着斑纹领带,体格与我想像中的传教士不同,相当壮实。
西德尼牧师说,2007年他才认识费尔南丁。当时费尔南丁和对手们之间爆发了一系列枪战,让整个社区心惊胆战。“就像战争区一样,”西德尼牧师说:“非常危险。”而他曾穿行在最危险的地方为信徒祈祷,这为他赢得了一些尊敬。“就是在毒贩子中间工作。我会出去,当街祈祷。我会接近他们,好像他们只是被魔鬼附了身。他们很接受这个。但我一直避免和费尔南丁打交道,我听说过一些关于他的事,那些我都不喜欢。”最终,“费尔南丁自己来找我了。他看着我祷告,请求我为他祈祷一下。”
近年来,福音教派在传统的天主教区域巴西取得了令人惊愕的进展。在里约热内卢一些贫民区,有很多福音派小教堂,夜复一夜,人们在喊叫和乐声中赞颂着上帝。在西德尼牧师的教堂,他和执事———其中包括好几个前黑帮成员———唱着歌,演奏着乐器,创造出一种混杂着斯卡(牙买加一种流行音乐)、嘻哈和巴西福音摇滚的歌曲。教区居民们伏在地上,让身上的魔鬼被驱走。
西德尼牧师这样解释他眼中的“魔鬼”:“被魔鬼附身的人会盯着某个点不放,周围有种冷漠———他们的眼睛不会眨。主体本身是缺位的。”每次看到这样的人,他就会“请求耶稣把他们带走,于是天使就会过来,把魔鬼从他们身上抓走。”
我说听说费尔南丁因为受到他的影响停止了杀人。西德尼牧师看上去有些怀疑。他是否认为费尔南丁真的相信上帝?“只有上帝知道一个人心里在想什么,”他说:“但是在我看来,费尔南丁距离接受上帝还很远,他往前走了一步,改变了一点,这是真的。过去,他们会直接从莫罗丁德过来,抢劫人家和汽车,现在这些都被禁止。现在他多数只是买卖毒品。”
但最近他和费尔南丁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我们希望把他拉回来,这样他才能看见周围都有什么,自己站在什么地方。”但几周前有人被杀死,“这些杀戮让我觉得自己不受尊重,”西德尼牧师说:“现在我厌烦了前去莫罗丁德,现在去那儿我只是待在当地居民中间。我不再试图去感化毒贩。如果他们主动来找我,我只是为他们祈祷。”一些福音教徒的表现也让他感到恼火,因为这些人试图迎合费尔南丁,“他们只说他想听的话,不说他需要听的话。”
我问西德尼牧师能否介绍我去见费尔南丁。他皱起了眉,说自己不想见费尔南丁,但可以带我到莫罗丁德,进行必要的介绍,剩下的就看我自己的了。
一天夜里,在等着去见费尔南丁的时候,我和一个名叫塞利奥的人驱车行进在里约热内卢北部郊区。塞利奥过去是特种部队士兵,为消防局工作,专门负责从街上清理尸体。
我们来到一条土路上,见到两个穿着制服的人,正从一辆汽车里拖出一具尸体。一辆汽车跟在我们后面,那是死者的家属。一个女人出来确认了死者身份。死者很年轻,只穿着红色内裤。随着他们搬动尸体,一股血流从背后———也许是肺部———的弹孔中喷涌而出,射向空中。他的头盖骨里还有更多子弹,手和脚都用塑料绳紧紧地绑在背上。他是大约3个小时前被处决的。
从外表和被处决的方式看,死者可能是个毒贩。处决他的人可能是由警察和消防队员———塞利奥的同事———组成的某个“死刑小分队”,也可能是其他毒贩。
里约热内卢一名警察贝托爽快地向我承认,警方会“私自处决”罪犯。他寻求赞同似的伸出双手。“这是因为我们是男人!”他说:“我们有感觉的,你懂吗?这些家伙向我们开枪。有时候我也救了他们的命,我曾经看到一个朋友待在他们中间……我说,算了,让他们走吧。但有些时候我不能这样。坦白地说,也有些时候,你不想那样,但也不真的在乎。”
一次白天驾车经过市区时,贝托把手枪解下来,藏在两腿中间。他的警察证也是“死亡证明”,因为如果黑帮成员发现了这玩意,会把他杀掉的。在他们眼中,里约热内卢10000名民事警察仅比那40000名军事警察稍好一点。“军事警察大多数经验不足,而且本身也很坏,”贝托说:“黑帮成员会毫不犹豫地把他们杀掉。”至于他,他说:“他们可能会犹豫一分钟,但最后还是会把我杀了。”
2005年3月,29名市民在里约热内卢北部一个贫穷的社区被下班后的警察杀害。警方之所以实施这样的屠杀是为了抗议另外一些警察的被捕。同样,针对警察的袭击也不时发生。2006年12月,“红色司令部”派人杀进城内发泄怒火,多个警察站受到自动武器和手榴弹的袭击,十余辆城市巴士被焚毁,至少19人死亡。
议员瑟吉斯告诉我:“那些收到钱的警察会在贫民区保护黑帮,而没有拿到钱的则会跑去杀人,并把责任推到另外一个帮派头上。”瑟吉斯说,里约热内卢警察收入不够高。“基本上每个警察都有第二职业,”他说:“此外,他们跟普通市民没有交流,他们只是坐在巡逻车里周游……30年前,帮派很少会杀害警察。如果这样做了,也很少能够侥幸逃脱。现在警察已经失去了尊重,黑帮视他们为同行和对手,所以才会对他们下手。”
7月份,我与新上任的里约热内卢警察局长阿兰·塔诺斯基对了话。我们问他这个城市的安全状况是不是一场灾难。
“灾难?”他说:“不。这里还没有变成巴格达或者墨西哥。我们有能力控制城中任何地方。问题是我们不能等待,要立即行动。”塔诺斯基谈到要打击警察私自组成的“民兵组织”,提高警察的技能和薪水。他提到一个被“清洗干净”的贫民区样本圣塔玛塔,政府在那里大笔投资,建设基础设施。我指出圣塔玛塔只有一个,还有1000多个贫民区无人问津,他点着头,说:“这需要时间。”
西德尼牧师带着我钻进他的汽车。我们穿过总督岛的街道,转过一个居民区后,进入贫民区的黑暗角落。西德尼打开了车内灯光,摇下了所有车窗,以便别人能看见我们的样子。在第一个十字路口,带着枪的年轻人拦住了汽车。他们戴着棒球帽,穿着写有口号的T恤和冲浪短裤。他们来到车窗前,认出了西德尼牧师,冲我们做出了认可的手势。
然后一种奇怪的仪式开始了。一个接一个,这些枪手把武器交给同伴,来到牧师打开的车窗前,站在那儿,手放在两侧,紧闭双眼,牧师大声用快速的葡萄牙语祈祷,然后伸出手来,放在枪手的前额上,反复大喊“走开”。最后他会对着他们猛地吹气,或者重击他们的脑袋,直到他们带着震惊的表情醒过来,睁开双眼,无言地微笑着,感谢牧师。
整个过程中,一位年轻人始终守在位于巷子的入口处的岗哨上,他面前有一个张开口的塑料袋,装满了一包包的可卡因,随时等人来购买。
我们开着车,沿着巷子缓慢地前进,旁边的男男女女不得不贴在墙上,让我们通过。我闻到了大麻和烧焦的橡胶爆裂的气味。我们再次被拦住。西德尼牧师再次举行他的驱魔仪式。我们开进了一个很大的肮脏的广场,这里就是普拉亚。到处都有枪手。气氛很紧张。
又经过三个检查站,我们来到一个岔路口,两条小道边的墙上都绘有与耶稣有关的涂鸦。我们来到了莫罗丁德。毒贩们尊敬地欢迎西德尼牧师的到来,问他是否要见“老板”。“不,我到此为止,”他说:“他知道为什么。”他们有些困惑,但都点着头。西德尼牧师说希望有个能负责任的人把我带去见费尔南丁。一个将近40岁的男人走上前来。西德尼牧师告诉我:“没事的,你可以跟他去,就像在自己家一样。”然后他开车走了。
男人带着我顺着一条陡峭的街道向上走去。在山顶上,他停下来,示意我等一下,然后消失了。街对面有几名身穿运动服的武装人员,人们不时走过来,找他们买可卡因。
费尔南丁出现了。六名保镖手持武器,呈扇形在他周围排开。我根据一张看过的照片认出了他,他的右前臂用哥特式字母绘着耶稣的名字,他戴着棒球帽,穿着短裤和无袖的圣保罗足球队T恤,上面写着LG两个字母。他戴着巨大的金链,大部分手指上都有特大号的金戒指,还有沉重的金表。每件东西都闪耀着珠光宝气。
他肤色白净,娃娃脸,中等身材,棕色头发剪得很短。他亲切地欢迎我。建议我们到他家去聊聊。他的保镖和我们共同前进。他们都是十几岁的少年,拿着A K -47或A R-15.我们走了几个楼梯,然后穿过小巷,转过两个弯,进了一所房子,通过一个狭窄的走廊,进了费尔南丁的卧室。
房间不是很大。他的床占据了大部分空间,上面铺着一张绘有卡通形象的床单。周围还有闪光的宗教贴纸,墙上挂着好几幅镶了框的圣歌。在一个角落是一个水族缸,另外一个角落摆着一部健身单车。一台巨大的等离子电视挂在正对着床的墙上。费尔南丁坐在床垫一角,把旁边一个小沙发上的衣服收拾干净,让我坐在那儿。他的保镖待在走廊里。
一个漂亮的年轻孕妇进来,送上一些饮料。她走后,我问费尔南丁那是否他的妻子,她肚里的孩子是不是他的。不,她只是个朋友,他妻子不在,他说,然后又自我纠正,“我们还没有真正结婚。”他有6个孩子,还有两个即将降生。他说妻子正怀着他们第一个孩子,对其他孩子,她基本不知情。他说打算等她生了之后再告诉她。我说这是个聪明的决定。
费尔南丁说,他在莫罗丁德的角色跟一名市长差不多。“人们有了问题,就过来找我,我会替他们解决。”他把自己戴着的金饰递给我。“我自己设计的,”他说:“重半公斤。”他说,他是一个毒贩子,没错,但他贩毒只是因为别人要消费毒品。我提到让他声名狼藉的谋杀事件,他说他没有亲手杀过人,有人代表他完成这些事。
“小时候我想成为足球运动员,”他说:“最后我意识到那只是一个白日梦。”他八九岁加入黑帮。我问他是否能想象自己的生活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不,”他说:“有这么多通缉令要抓我,我甚至都不能离开贫民区。”他已经有两年没有离开莫罗丁德了,从2003年以来也只离开过两次。
电视一直开着。正在放着的是发现频道的巴西版,内容是关于梦游杀手的纪录片。费尔南丁转到一个地方新闻台,那里正在直播犯罪分子和圣保罗警察之间的枪战。
“是这样子的吗?”我问。“嗯,有时是,”费尔南丁说。但他补充说,他尽量避免跟警方对峙。每次警方发动突袭,只要可能,他和手下就会藏起来。
费尔南丁打开衣柜门,到处翻找。最后他找到两瓶男士香水,还未开封。“拿去,”他说:“给你的。”他说,他做了很多祈祷,甚至为敌人祈祷。好像是为了证明这番声明的真实性,他关上了卧室的门,走到床边跪下。他像孩子做游戏般,两手合拢,双眼紧闭,嘴唇动着,喃喃祈祷。他站起来,找到《圣经》,然后坐在我面前的床上,打开到做了标记的那一页,大概是整本书四分之一的地方。他说下决心要通读一遍。
我赞扬了他的努力。但是之后,在指出他的宗教信仰和毒贩生活存在矛盾之后,我问:“对你来说,是非之间的分界线在哪里?”
费尔南丁微笑着,说:“这有什么紧要呢?”
两天后我回帕克罗亚尔去见西德尼牧师。他邀请我品尝feijoada,由黑豆和猪肉做成的巴西炖菜。他问我跟费尔南丁的会面如何,我说费尔南丁说了很多关于宗教信仰的东西。西德尼点点头。我感觉他似乎想进一步清晰地表述他与黑帮老大之间的不和。“发生什么事了?”我问:“我想他已经承诺停止杀人了。”
“是的,这正是我远离他的原因,因为他打破了诺言。”
他指责的重点是吉尔,费尔南丁的副手。吉尔之前住院了,他不在的时候,一切都挺好,然后吉尔回来了。西德尼牧师说:“他非常嗜血。我预见到了,告诉费尔南丁一周之内,谋杀又要开始。结果,一周之内,真的发生了。”西德尼牧师听说要处死四名告密者。他飞奔前去莫罗丁德,想拯救他们的生命。他要求见费尔南丁,但保镖说老板正在休息,不能受打扰。他说起那些被抓住的人,他们告诉他:“别担心。”于是他就放心地离开了。
后来他听说他们被杀了,感到自己受到了背叛。“我去找费尔南丁,告诉他,我们之间形成的联盟破裂了。”西德尼牧师说:“两年来他们立誓不会再杀一个人,我提醒他,那段时间里,他们的人也没有一个被杀或被捕,”他补充说:“我预言他们之中很快就要有人丧命了。”
“费尔南丁说什么?”
“他根本没有回答。我看到魔鬼又回到了他的眼睛里。”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翻译:G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