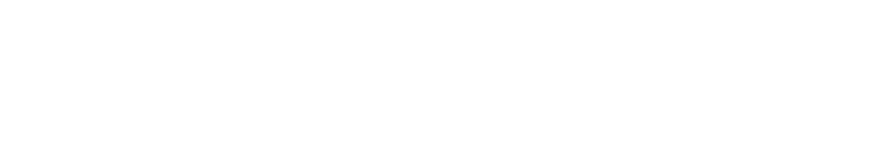|
||||||||||||||||||
简介:
死去的政府 请安抚你的穆斯林
2010-01-09 11:08:25 来源: 南方周末(广州)
发生在伊朗的流血示威,从去年底持续到今年初,反对大选舞弊的口号换成了“政府去死”。
每过三四十年,伊朗人就要从根子上重新修补国家共识,不幸的是,这种修补往往以社会动荡为代价。建国时的理想、政治结构能保持多大的灵活性,能否应对新时代和新命题,将是决定伊朗政治未来动荡程度大小的主要因素。而能否再次应对国家共识的分裂,将是伊朗领导人逃不掉的宿命。

人人都能意识到:脸皮已经撕破,分歧在扩大。
2009年年底,宗教纪念日上的示威游行并没有过多打扰德黑兰1500万人民的平静。食品价格略有上调,不是因为社会动荡,而是季节。反对者与政府的冲突已经持续了近半年,但拐点尚未到来,谁赢谁输暂时难以预料。
不过,人人都能意识到:脸皮已经撕破,分歧在扩大。
反对大选舞弊的口号换成了“政府去死”。伊朗似乎难逃“三十年一次动荡”的魔咒。100年来国际社会的巨大变革严重干预了这个国家近代化的进程,造成国家共识的分裂,政治、经济、社会以及观念各个层面无一例外。而地理位置、经济结构和民情又意味着这种干预无法避免。于是每过三四十年,伊朗人就要从根子上重新修补国家共识,不幸的是,这种修补往往以社会动荡为代价。
走向决裂
由去年6月伊朗总统大选激发的改革与保守派之争,在持续半年后不可避免地走向决裂。2009年12月22日,改革派资格最老地位最高的那棵大树蒙泽塔里倒下。当地习俗中,传统葬礼是死者亲戚、朋友集会的重要时刻,蒙泽塔里的葬礼自然而然成为改革派一次大规模示威活动。
蒙泽塔里本人身份极其特殊,一方面他根正苗红,曾在上个世纪整个1980年代被视为最高领袖霍梅尼的接班人,直到霍梅尼去世那年才被排挤出局。那时候,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不过是一名小弟。
另一方面,他在下台后成为坚定的改革派人物。80年代正是伊朗最困难的时期,两伊战争打了8年,伊朗死伤上百万,GDP连年负增长,元气大伤。检讨这一时期的要求,为蒙泽塔里“开放和人权”的主张,提供了最原始的动力。
蒙泽塔里的双重身份为改革派和政府的对话提供了路径。而他的去世,则对于改革派能否在体制内与主政的保守派达成共识增加了相当大的悬念。
巧的是,12月22日这场十几万人的大游行,恰恰发生在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圣地库姆。31年前,1978年1月,库姆最先爆发了由当地学生与巴扎商人进行的反政府示威游行,遭到当局残酷镇压。在镇压40天后,为死难者举行的集会活动再次演变成示威游行,重新遭到镇压。在接下来近一年的时间里,一轮又一轮的“死亡-集会-镇压”循环持续演变,并在当年9月的德黑兰发生了黑色星期五大屠杀。巴列维王朝的军人动用了坦克、武装直升机镇压示威,血流成河,导致在国王与人民之间留下了不可愈合的创伤。
而现在,库姆兼葬礼集会示威,似乎是历史的重演。当年伊斯兰革命的主角们而今正坐在主席台、办公桌的后面扮演着当年他们所要打倒的角色。一群后生小辈在昔日同僚的领导下,故伎重演。
接下来,12月27日,在首都德黑兰再次发生示威冲突。这一天是当地的传统纪念日阿舒拉节。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反对派与政府支持者发生冲突导致8人死亡。
在信息受到严密封锁的情况下,这场游行引起国外观察者的诸多猜测,改革派的海外支持者甚至开始预言“新伊朗”的诞生。但由于伊朗政府事先采取了相对有效的遏制措施,这场示威规模比库姆的示威要小很多,对德黑兰的直接影响也并不剧烈。反倒是政府以及保守派的支持者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态度。
随后一周,伊朗当局多次严厉谴责示威者的行径,大选期间支持改革派的大佬拉夫桑贾尼这次成了最早跳出来反对这次示威的人之一。政府三大首脑,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议会发言人阿里·拉里贾尼和他的弟弟司法总监萨德格·拉里贾尼则在多个场合称示威者是伊斯兰共和体制的敌人。在上周日三人开会讨论之后,司法总监萨德格·拉里贾尼在周一称将对示威者严惩不贷。1月初,伊朗政府已经将示威者定性为反伊斯兰政权者。
和往常一样,外国势力再次“荣获”示威幕后推手的称号。
伊朗改革派的尴尬境地
保守派的强硬态度势必令改革派的领袖穆萨维、哈塔米等人处于尴尬境地。改革派领袖和保守派人士一样同样是31年前伊斯兰革命的继承者,无论其温和还是激烈的态度,都没有推翻伊斯兰共和体制的政治诉求。面对政府及其支持者的强大压力,不对自己支持者进行声援,则丧失群众基础,在得不到最高领袖和实权派人物支持的情况下,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等于失去了一切。但反过来,声援则面临颠覆政权的指控。随着局势的恶化,改革派领导人越来越面对需要被迫站队的危险。
不过,改革派的命运至今尚未清晰,是分化成革命派和改良派还是集体成为新的革命派犹未可知。更为重要的是,至今尚未有一份能够体现改革派内部共识、成系统的纲领性文件出台。而早在1971年,霍梅尼已经为7年后才爆发的革命制定了革命手册——《伊斯兰法学家的政府》(Government of the Islamic Jurist)。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核心思想之一是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
对于保守派来说,短时的强势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半年以来,反对派的游行越来越多地从大选不公转化为更激烈的对体制的不满。这也正是执政的保守派必须回答的问题——伊斯兰共和体制的合法性依据究竟在哪里。
31年前,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创建了这一政教合一的体制,宗教势力凌驾于世俗的三权分立制度之上。这一体制不仅在波斯人的历史上绝无仅有,就是在几千年人类文明史上也实属罕见。
在伊朗业已建立的现代的国家体系中,宗教系统究竟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承载什么样的功能?社会财富的分配、公共管理、国际关系,这些政治核心机能究竟需要宗教做什么?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不仅仅关系到伊朗若干官僚的饭碗,而且也关系到伊朗整个国家的前途。
30年一动荡的格局不可避免
与诸多媒体报道造成的想象不同,伊朗并不是一个被黑色纱布遮盖起来的封闭国家。德黑兰郊外刚刚建成的霍梅尼国际机场和北京首都机场3号楼不相上下。年轻人手上拿着MP3,放着流行的饶舌音乐,有些还是本土地下乐队自创的。而好莱坞大片也以各种各样的地下渠道渗透到伊朗全境。蜘蛛侠和米老鼠的造型甚至被绣在传统波斯地毯上。
从历史上说,这个国家从来没有过闭关锁国的历史。从大流士时期疆域横跨亚非欧的波斯帝国到陆地、海上丝绸之路的中间掮客,开放一直是伊朗的传统。而石油天然气的经济支柱产业又是造成今天伊朗不得不面对世界的必然。
这意味着整个伊朗近现代过程是在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中进行的。
100年前,伊朗引进西方思潮掀起立宪运动,1920年代礼萨汗在英国人的帮助下创建巴列维王朝,又在1940年代初被盟军驱逐。1960年代巴列维国王发起改革,但经济发展贫富不均进一步造成了社会动荡。到70年代末期,伊斯兰共和国成立,被西方学者称作中东地区的“一次突来洪水”。
在全球化时期,能否长期地维系国内各方的政治共识,为伊朗内部发展、各方利益协调创造出政治“绿坝”,将所谓“不良因素”屏蔽,对于伊斯兰共和体制来说,显然是严峻挑战。
30年前,在冷战与石油危机的背景下,革命者关注的是,民族主义、独立、反殖民主义、反美、国有化、传统、伊斯兰化、反君主制,伊斯兰共和制成了解决问题的实际方案。 而在30年后,自由、私有化、经济增长、通货膨胀、核计划、对外关系、与美国关系甚至政教分离、贫富差异、年轻国家成为解读伊朗政治的关键词,这意味着建国时的理想、理念到政治结构能保持多大的灵活性,能否应对新时代和新命题,将是决定伊朗政治未来动荡程度大小的主要因素。
而能否再次应对国家共识的分裂,将是伊朗领导人逃不掉的宿命,这一点哈梅内伊或者艾哈迈迪内贾德面临的问题,与巴列维国王并无两样。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蒲黄榆)
2010-01-09 11:08:25 来源: 南方周末(广州)
发生在伊朗的流血示威,从去年底持续到今年初,反对大选舞弊的口号换成了“政府去死”。
每过三四十年,伊朗人就要从根子上重新修补国家共识,不幸的是,这种修补往往以社会动荡为代价。建国时的理想、政治结构能保持多大的灵活性,能否应对新时代和新命题,将是决定伊朗政治未来动荡程度大小的主要因素。而能否再次应对国家共识的分裂,将是伊朗领导人逃不掉的宿命。

人人都能意识到:脸皮已经撕破,分歧在扩大。
2009年年底,宗教纪念日上的示威游行并没有过多打扰德黑兰1500万人民的平静。食品价格略有上调,不是因为社会动荡,而是季节。反对者与政府的冲突已经持续了近半年,但拐点尚未到来,谁赢谁输暂时难以预料。
不过,人人都能意识到:脸皮已经撕破,分歧在扩大。
反对大选舞弊的口号换成了“政府去死”。伊朗似乎难逃“三十年一次动荡”的魔咒。100年来国际社会的巨大变革严重干预了这个国家近代化的进程,造成国家共识的分裂,政治、经济、社会以及观念各个层面无一例外。而地理位置、经济结构和民情又意味着这种干预无法避免。于是每过三四十年,伊朗人就要从根子上重新修补国家共识,不幸的是,这种修补往往以社会动荡为代价。
走向决裂
由去年6月伊朗总统大选激发的改革与保守派之争,在持续半年后不可避免地走向决裂。2009年12月22日,改革派资格最老地位最高的那棵大树蒙泽塔里倒下。当地习俗中,传统葬礼是死者亲戚、朋友集会的重要时刻,蒙泽塔里的葬礼自然而然成为改革派一次大规模示威活动。
蒙泽塔里本人身份极其特殊,一方面他根正苗红,曾在上个世纪整个1980年代被视为最高领袖霍梅尼的接班人,直到霍梅尼去世那年才被排挤出局。那时候,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不过是一名小弟。
另一方面,他在下台后成为坚定的改革派人物。80年代正是伊朗最困难的时期,两伊战争打了8年,伊朗死伤上百万,GDP连年负增长,元气大伤。检讨这一时期的要求,为蒙泽塔里“开放和人权”的主张,提供了最原始的动力。
蒙泽塔里的双重身份为改革派和政府的对话提供了路径。而他的去世,则对于改革派能否在体制内与主政的保守派达成共识增加了相当大的悬念。
巧的是,12月22日这场十几万人的大游行,恰恰发生在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圣地库姆。31年前,1978年1月,库姆最先爆发了由当地学生与巴扎商人进行的反政府示威游行,遭到当局残酷镇压。在镇压40天后,为死难者举行的集会活动再次演变成示威游行,重新遭到镇压。在接下来近一年的时间里,一轮又一轮的“死亡-集会-镇压”循环持续演变,并在当年9月的德黑兰发生了黑色星期五大屠杀。巴列维王朝的军人动用了坦克、武装直升机镇压示威,血流成河,导致在国王与人民之间留下了不可愈合的创伤。
而现在,库姆兼葬礼集会示威,似乎是历史的重演。当年伊斯兰革命的主角们而今正坐在主席台、办公桌的后面扮演着当年他们所要打倒的角色。一群后生小辈在昔日同僚的领导下,故伎重演。
接下来,12月27日,在首都德黑兰再次发生示威冲突。这一天是当地的传统纪念日阿舒拉节。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反对派与政府支持者发生冲突导致8人死亡。
在信息受到严密封锁的情况下,这场游行引起国外观察者的诸多猜测,改革派的海外支持者甚至开始预言“新伊朗”的诞生。但由于伊朗政府事先采取了相对有效的遏制措施,这场示威规模比库姆的示威要小很多,对德黑兰的直接影响也并不剧烈。反倒是政府以及保守派的支持者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态度。
随后一周,伊朗当局多次严厉谴责示威者的行径,大选期间支持改革派的大佬拉夫桑贾尼这次成了最早跳出来反对这次示威的人之一。政府三大首脑,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议会发言人阿里·拉里贾尼和他的弟弟司法总监萨德格·拉里贾尼则在多个场合称示威者是伊斯兰共和体制的敌人。在上周日三人开会讨论之后,司法总监萨德格·拉里贾尼在周一称将对示威者严惩不贷。1月初,伊朗政府已经将示威者定性为反伊斯兰政权者。
和往常一样,外国势力再次“荣获”示威幕后推手的称号。
伊朗改革派的尴尬境地
保守派的强硬态度势必令改革派的领袖穆萨维、哈塔米等人处于尴尬境地。改革派领袖和保守派人士一样同样是31年前伊斯兰革命的继承者,无论其温和还是激烈的态度,都没有推翻伊斯兰共和体制的政治诉求。面对政府及其支持者的强大压力,不对自己支持者进行声援,则丧失群众基础,在得不到最高领袖和实权派人物支持的情况下,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等于失去了一切。但反过来,声援则面临颠覆政权的指控。随着局势的恶化,改革派领导人越来越面对需要被迫站队的危险。
不过,改革派的命运至今尚未清晰,是分化成革命派和改良派还是集体成为新的革命派犹未可知。更为重要的是,至今尚未有一份能够体现改革派内部共识、成系统的纲领性文件出台。而早在1971年,霍梅尼已经为7年后才爆发的革命制定了革命手册——《伊斯兰法学家的政府》(Government of the Islamic Jurist)。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核心思想之一是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
对于保守派来说,短时的强势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半年以来,反对派的游行越来越多地从大选不公转化为更激烈的对体制的不满。这也正是执政的保守派必须回答的问题——伊斯兰共和体制的合法性依据究竟在哪里。
31年前,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创建了这一政教合一的体制,宗教势力凌驾于世俗的三权分立制度之上。这一体制不仅在波斯人的历史上绝无仅有,就是在几千年人类文明史上也实属罕见。
在伊朗业已建立的现代的国家体系中,宗教系统究竟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承载什么样的功能?社会财富的分配、公共管理、国际关系,这些政治核心机能究竟需要宗教做什么?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不仅仅关系到伊朗若干官僚的饭碗,而且也关系到伊朗整个国家的前途。
30年一动荡的格局不可避免
与诸多媒体报道造成的想象不同,伊朗并不是一个被黑色纱布遮盖起来的封闭国家。德黑兰郊外刚刚建成的霍梅尼国际机场和北京首都机场3号楼不相上下。年轻人手上拿着MP3,放着流行的饶舌音乐,有些还是本土地下乐队自创的。而好莱坞大片也以各种各样的地下渠道渗透到伊朗全境。蜘蛛侠和米老鼠的造型甚至被绣在传统波斯地毯上。
从历史上说,这个国家从来没有过闭关锁国的历史。从大流士时期疆域横跨亚非欧的波斯帝国到陆地、海上丝绸之路的中间掮客,开放一直是伊朗的传统。而石油天然气的经济支柱产业又是造成今天伊朗不得不面对世界的必然。
这意味着整个伊朗近现代过程是在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中进行的。
100年前,伊朗引进西方思潮掀起立宪运动,1920年代礼萨汗在英国人的帮助下创建巴列维王朝,又在1940年代初被盟军驱逐。1960年代巴列维国王发起改革,但经济发展贫富不均进一步造成了社会动荡。到70年代末期,伊斯兰共和国成立,被西方学者称作中东地区的“一次突来洪水”。
在全球化时期,能否长期地维系国内各方的政治共识,为伊朗内部发展、各方利益协调创造出政治“绿坝”,将所谓“不良因素”屏蔽,对于伊斯兰共和体制来说,显然是严峻挑战。
30年前,在冷战与石油危机的背景下,革命者关注的是,民族主义、独立、反殖民主义、反美、国有化、传统、伊斯兰化、反君主制,伊斯兰共和制成了解决问题的实际方案。 而在30年后,自由、私有化、经济增长、通货膨胀、核计划、对外关系、与美国关系甚至政教分离、贫富差异、年轻国家成为解读伊朗政治的关键词,这意味着建国时的理想、理念到政治结构能保持多大的灵活性,能否应对新时代和新命题,将是决定伊朗政治未来动荡程度大小的主要因素。
而能否再次应对国家共识的分裂,将是伊朗领导人逃不掉的宿命,这一点哈梅内伊或者艾哈迈迪内贾德面临的问题,与巴列维国王并无两样。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蒲黄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