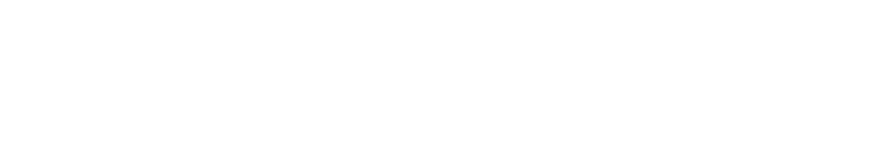|
||||||||||||||||||
简介:
我的名字叫黑 细密画师被杀
在爱情与谋杀的外壳下,《我的名字叫红》包含着沉重的文化内容,反映了东西方两大文明的此消彼长
□李雾

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名著《我的名字叫红》,很罕有地在他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即已引进翻译(译者沈志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06年8月出版。然后,在该年10月帕慕克得奖后热卖。这部小说,通常认为,在爱情和谋杀的外壳之下,包含着沉重的文化内容,东(土耳其)西(威尼斯)方两种观察世界之眼光的冲突,反映了两大文明的此消彼长。
我国古代帝皇继位,有所谓“河图洛书”(简称“图书”)的祥瑞。中亚文化里,苏丹继位,也要为自己编撰一本彪炳功绩的图书。《红》第10章“我是一棵树”里,伊斯坦布尔咖啡馆内讲故事的人,以画中树的口吻,说起从前有位苏丹下令编图书。主事者让鞑靼骑士将书拆开,去各地请大师画装帧。带着这幅画中树的骑士半路被杀,所以这棵树感到很寂寞,因为它不知道自己应该贴哪一张书页,配哪一段文字,隶属于书中哪一个故事。这棵树感到自己失去了生存的意义。这一章很能说明当时奥斯曼宫廷画家的艺术眼光:按他们所奉行的波斯细密画派传统,画是修饰文字的,没有自己的独立意义。书页中央,最吸引观者注意力之处,必须为文字。其实,基督教从前也是这样的。笔者在大英图书馆的珍本室里,见到《圣经》的早期手抄本,也是经文在书页中央,四边画上天使、信徒和飞鸟、花卉等。
但是,西方从14世纪到16世纪经历了文艺复兴运动,人性抬头,人体也抬头,人也可以画在图中央了。帕慕克把故事安排在16世纪末的1591年。《红》末的“大事纪”里———中国人农业民族,不在乎细节,中译本删去了这一附录———帕慕克写道,虽然土耳其海军在1571年的一次关键海战中败北,两年后威尼斯仍然承认了奥斯曼帝国对塞浦路斯岛的主权,这对欧洲的士气有很大冲击,提香、丁托列托和委罗内塞都画过这次事件的画。似乎奥斯曼占了便宜。查威廉·杜兰的煌煌巨著《世界文明史》(英文标题为TheStoryofCivilization,已经由东方出版社在2003年译成38卷出版),却说装备了224条战舰的奥斯曼海军被歼灭,威尼斯史无前例狂欢三天,街上还放着画家们创作的羞辱土耳其人的海战图。
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背景就是土耳其舰队试图攻打当时由威尼斯镇守的塞浦路斯。《红》中的姨夫曾出使威尼斯,而且就是去宣布奥斯曼对塞浦路斯的领土意图。他差点被愤怒的市民打死。这是姨夫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一定印象深刻。如果帕慕克知道威尼斯画家画了痛歼土耳其舰队的画,他笔下的姨夫必然也知道了。姨夫按自己的文化习惯来理解,或许认为这些画将进入西方君主的“功绩书”。姨夫回国后,怂恿苏丹制作图书,送一本给威尼斯。硬实力打不过,就玩软实力,在文化上镇镇西方人。
《红》第20章“我的名字叫黑”里,奥斯曼苏丹让姨夫编图书。苏丹同意仿照威尼斯的西方画法,为自己画像。但这是违反他们宗教传统的,宫廷首席画师奥斯曼大师第一个反对。如果苏丹被画在书页正中,这就涉嫌“偶像崇拜”,为教义所严禁。因此姨夫的编书过程必须严格保密。
男主角黑被姨夫招募,参与图书制作。他接受威尼斯画法,还有私人原因。黑一出场,第2章里,已经说到自己在12年的流浪生活中,逐渐失去了情人脸相的清晰记忆。后来,第22章中,在犹太人废弃的屋子,相隔12年后,黑再次见到情人谢库瑞。他想:要是能精确画下面容就好了,或可缓解相思之苦。
只是新的画风引起内部倾轧,先是一位画师被杀,接着姨夫也遇害。历经曲折,黑终于发现了凶手。凶手最后坦白,他杀人盗画后,试图把自己的肖像画在书页正中,但他连自己都画不像。他警告黑:我们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才能学会西洋画家的技巧,我们这代人改画意大利画,不会有前途。
帕慕克书中没写,不过,西洋画家原来大概也是画不像的。
这牵涉到西方艺术史上一桩公案:欧洲画家到底是如何发展出精细绘脸本事的?近年来,艺术史家提出新假说,他们猜测:某段时期,西洋画家画肖像时,曾利用光学装置,将肖像投影到画布上。
按帕慕克在书末的记录———中国人农业民族,不在乎细节,中译本略去了作者注明的写作时段———《红》是1998年完成的。当时美国报纸可能已在讨论这一假说。2001年美国出版过一本梳理该公案的书,《秘密知识:重新发现散失了的前代大师技巧》。作者戴卫·霍克尼本身也是画家,他将此公案最早回溯到荷兰画家杨·凡·艾克。凡·艾克是西方绘画转折性人物,他创新了逼真描绘真人的技巧。霍克尼认为凡·艾克应用过光学装置。其名作《阿尔诺芬尼夫妇像》(TheArnolfiniMarriage)里,那对夫妻之间的凸镜,可能是画家留下的暗示。凡·艾克是15世纪的画家,而《红》中16世纪的意大利画家,正是受过荷兰影响的。
凡·艾克画中这对夫妻,虽然替代经文站在画中央,却一望可知,他们是简朴的新教徒。即使画俗人像,当时的人都信教,宗教仍然是他们最重要的文化身份。画的四边,遵照以前经文在中央时的习惯,仍会画有一些宗教象征,如十字架和百合花等。《达·芬奇密码》里那位哈佛教授罗伯特·兰登,就是专门研究这类象征的。《阿尔诺芬尼夫妇像》左边的窗沿上有个苹果,即象征人类的原罪。凡·艾克还在妻子脚边画了一条狗,象征对丈夫的忠诚。狗似乎还是画完人之后加上去的。
光线是从眼睛到物体,还是从物体到眼睛,科学史上曾有长期争论。这一争论所体现的我们如何感知客观世界的大问题,几乎就是一部人类思想史。《红》中的画家经常讨论“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奥斯曼大师刺瞎自己的眼睛,固然是不愿遵从苏丹的命令,不愿在姨夫死后接手图书编撰;但他也有观念上的安慰,大师相信目盲之后才能真正见到真主之所见。对他来说,光显然不是从物体来的,也不必反映该物体的某些属性。
有趣的是,正是阿拉伯科学家首先确立了光线从物体到眼睛的观念(文艺复兴之前,阿拉伯的数学和科学研究比西方先进)。这之后,尊重物体固有形象和位置的透视才成为可能。要有这样的观念,凡·艾克才会力求逼真,以至用了光学装置———据某些专家说。《阿尔诺芬尼夫妇像》里的窗框和地板线条,显然符合透视的原理。
奥斯曼大师拒绝透视画法,认为东方人不必学,祖传固有画技更高明;凶手则认为东方人会学成假洋鬼子四不像。用当今时髦说法,这叫作坚持民族文化的自主性,抵制西方的文化侵略。我们甚至可以说,只要抵制到底,东方文化势必单向传至西方。你不愿学西方,多元化的西方却总会有人愿意学你。反正艺多不压身,多一招是一招。英文版《红》的封脊,印有书中提到的一幅画。一对传说中的恋人胡斯莱夫和席琳相对而坐,但他们知道观众在看他们,所以将头扭向正面。这是很不自然的姿势,但毕加索也有这种姿态的画,虽说他的人物很抽象。毕加索是西班牙画家,而西班牙历史上曾被阿拉伯人部分占领,他们的艺术传统里有中东成分。
不学西方透视,大概无所谓,就当是把人画在中央、宣扬个人至上的毒素。只是文化本是整体,其实难分精华糟粕。谁也无法预料,绘画里的透视,会有何种其他用途。
所谓透视,其实是一种投影。是从一个点出发,将三维场景投射到画布平面上。有了这套方法,天地立即宽广。《红》的故事之前30年,欧洲人开始使用墨卡托地图。所谓墨卡托投影,是假设球体外切一个圆柱面,视点在球心,从球心看出去,球面在这个圆柱面上的投影,就是墨卡托地图。绘画里的透视和制图中的墨卡托投影,原理上是一回事。这种图对航海特别方便,球面上两点间的最短距离,在墨卡托地图上就是这两点间的直线。有了好的地图制法,就有了可靠的海图,美洲就能开发,印度就能征服,商业就能发展,世界市场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就能发展,等等———这里可以放入《共产党宣言》中描述地理大发现之后资本全球化的全部段落。
英国印制很多精美地图集。手头有本《新世界:地理大发现时期的地图》。翻看16世纪一百年间的各类地图,投影地图看上去明显地更正规,更像现在的地图。而如今的地图,都是用各种投影法绘制的。
再回想一下,《红》中的苏丹,为什么不惜重金要编那本图书?———苏丹想在书里展示奥斯曼帝国的富裕和先进,用当今时髦说法,这叫作扩大民族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用图书恐吓威尼斯的起因,则是奥斯曼帝国觉得塞浦路斯在去麦加朝拜的海路上,要把这个岛从威尼斯人那里夺过来,结果吃了大败仗。塞浦路斯就在土耳其家门口;而威尼斯人要从地中海西边大老远地坐船过来,他们能打赢,显然有航海优势。较为精确的投影地图,或许就是威尼斯优势的一部分。
在小说之外的真实历史里,姨夫的预言应验了,土耳其人开始被迫向西方看齐;而凶手的预言也应验了,几代人都学不像,他们缺乏在西方萌芽的现代科学观念。蹉跎之间,世界已经是别人的了。
在爱情与谋杀的外壳下,《我的名字叫红》包含着沉重的文化内容,反映了东西方两大文明的此消彼长
□李雾

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名著《我的名字叫红》,很罕有地在他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即已引进翻译(译者沈志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06年8月出版。然后,在该年10月帕慕克得奖后热卖。这部小说,通常认为,在爱情和谋杀的外壳之下,包含着沉重的文化内容,东(土耳其)西(威尼斯)方两种观察世界之眼光的冲突,反映了两大文明的此消彼长。
我国古代帝皇继位,有所谓“河图洛书”(简称“图书”)的祥瑞。中亚文化里,苏丹继位,也要为自己编撰一本彪炳功绩的图书。《红》第10章“我是一棵树”里,伊斯坦布尔咖啡馆内讲故事的人,以画中树的口吻,说起从前有位苏丹下令编图书。主事者让鞑靼骑士将书拆开,去各地请大师画装帧。带着这幅画中树的骑士半路被杀,所以这棵树感到很寂寞,因为它不知道自己应该贴哪一张书页,配哪一段文字,隶属于书中哪一个故事。这棵树感到自己失去了生存的意义。这一章很能说明当时奥斯曼宫廷画家的艺术眼光:按他们所奉行的波斯细密画派传统,画是修饰文字的,没有自己的独立意义。书页中央,最吸引观者注意力之处,必须为文字。其实,基督教从前也是这样的。笔者在大英图书馆的珍本室里,见到《圣经》的早期手抄本,也是经文在书页中央,四边画上天使、信徒和飞鸟、花卉等。
但是,西方从14世纪到16世纪经历了文艺复兴运动,人性抬头,人体也抬头,人也可以画在图中央了。帕慕克把故事安排在16世纪末的1591年。《红》末的“大事纪”里———中国人农业民族,不在乎细节,中译本删去了这一附录———帕慕克写道,虽然土耳其海军在1571年的一次关键海战中败北,两年后威尼斯仍然承认了奥斯曼帝国对塞浦路斯岛的主权,这对欧洲的士气有很大冲击,提香、丁托列托和委罗内塞都画过这次事件的画。似乎奥斯曼占了便宜。查威廉·杜兰的煌煌巨著《世界文明史》(英文标题为TheStoryofCivilization,已经由东方出版社在2003年译成38卷出版),却说装备了224条战舰的奥斯曼海军被歼灭,威尼斯史无前例狂欢三天,街上还放着画家们创作的羞辱土耳其人的海战图。
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背景就是土耳其舰队试图攻打当时由威尼斯镇守的塞浦路斯。《红》中的姨夫曾出使威尼斯,而且就是去宣布奥斯曼对塞浦路斯的领土意图。他差点被愤怒的市民打死。这是姨夫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一定印象深刻。如果帕慕克知道威尼斯画家画了痛歼土耳其舰队的画,他笔下的姨夫必然也知道了。姨夫按自己的文化习惯来理解,或许认为这些画将进入西方君主的“功绩书”。姨夫回国后,怂恿苏丹制作图书,送一本给威尼斯。硬实力打不过,就玩软实力,在文化上镇镇西方人。
《红》第20章“我的名字叫黑”里,奥斯曼苏丹让姨夫编图书。苏丹同意仿照威尼斯的西方画法,为自己画像。但这是违反他们宗教传统的,宫廷首席画师奥斯曼大师第一个反对。如果苏丹被画在书页正中,这就涉嫌“偶像崇拜”,为教义所严禁。因此姨夫的编书过程必须严格保密。
男主角黑被姨夫招募,参与图书制作。他接受威尼斯画法,还有私人原因。黑一出场,第2章里,已经说到自己在12年的流浪生活中,逐渐失去了情人脸相的清晰记忆。后来,第22章中,在犹太人废弃的屋子,相隔12年后,黑再次见到情人谢库瑞。他想:要是能精确画下面容就好了,或可缓解相思之苦。
只是新的画风引起内部倾轧,先是一位画师被杀,接着姨夫也遇害。历经曲折,黑终于发现了凶手。凶手最后坦白,他杀人盗画后,试图把自己的肖像画在书页正中,但他连自己都画不像。他警告黑:我们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才能学会西洋画家的技巧,我们这代人改画意大利画,不会有前途。
帕慕克书中没写,不过,西洋画家原来大概也是画不像的。
这牵涉到西方艺术史上一桩公案:欧洲画家到底是如何发展出精细绘脸本事的?近年来,艺术史家提出新假说,他们猜测:某段时期,西洋画家画肖像时,曾利用光学装置,将肖像投影到画布上。
按帕慕克在书末的记录———中国人农业民族,不在乎细节,中译本略去了作者注明的写作时段———《红》是1998年完成的。当时美国报纸可能已在讨论这一假说。2001年美国出版过一本梳理该公案的书,《秘密知识:重新发现散失了的前代大师技巧》。作者戴卫·霍克尼本身也是画家,他将此公案最早回溯到荷兰画家杨·凡·艾克。凡·艾克是西方绘画转折性人物,他创新了逼真描绘真人的技巧。霍克尼认为凡·艾克应用过光学装置。其名作《阿尔诺芬尼夫妇像》(TheArnolfiniMarriage)里,那对夫妻之间的凸镜,可能是画家留下的暗示。凡·艾克是15世纪的画家,而《红》中16世纪的意大利画家,正是受过荷兰影响的。
凡·艾克画中这对夫妻,虽然替代经文站在画中央,却一望可知,他们是简朴的新教徒。即使画俗人像,当时的人都信教,宗教仍然是他们最重要的文化身份。画的四边,遵照以前经文在中央时的习惯,仍会画有一些宗教象征,如十字架和百合花等。《达·芬奇密码》里那位哈佛教授罗伯特·兰登,就是专门研究这类象征的。《阿尔诺芬尼夫妇像》左边的窗沿上有个苹果,即象征人类的原罪。凡·艾克还在妻子脚边画了一条狗,象征对丈夫的忠诚。狗似乎还是画完人之后加上去的。
光线是从眼睛到物体,还是从物体到眼睛,科学史上曾有长期争论。这一争论所体现的我们如何感知客观世界的大问题,几乎就是一部人类思想史。《红》中的画家经常讨论“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奥斯曼大师刺瞎自己的眼睛,固然是不愿遵从苏丹的命令,不愿在姨夫死后接手图书编撰;但他也有观念上的安慰,大师相信目盲之后才能真正见到真主之所见。对他来说,光显然不是从物体来的,也不必反映该物体的某些属性。
有趣的是,正是阿拉伯科学家首先确立了光线从物体到眼睛的观念(文艺复兴之前,阿拉伯的数学和科学研究比西方先进)。这之后,尊重物体固有形象和位置的透视才成为可能。要有这样的观念,凡·艾克才会力求逼真,以至用了光学装置———据某些专家说。《阿尔诺芬尼夫妇像》里的窗框和地板线条,显然符合透视的原理。
奥斯曼大师拒绝透视画法,认为东方人不必学,祖传固有画技更高明;凶手则认为东方人会学成假洋鬼子四不像。用当今时髦说法,这叫作坚持民族文化的自主性,抵制西方的文化侵略。我们甚至可以说,只要抵制到底,东方文化势必单向传至西方。你不愿学西方,多元化的西方却总会有人愿意学你。反正艺多不压身,多一招是一招。英文版《红》的封脊,印有书中提到的一幅画。一对传说中的恋人胡斯莱夫和席琳相对而坐,但他们知道观众在看他们,所以将头扭向正面。这是很不自然的姿势,但毕加索也有这种姿态的画,虽说他的人物很抽象。毕加索是西班牙画家,而西班牙历史上曾被阿拉伯人部分占领,他们的艺术传统里有中东成分。
不学西方透视,大概无所谓,就当是把人画在中央、宣扬个人至上的毒素。只是文化本是整体,其实难分精华糟粕。谁也无法预料,绘画里的透视,会有何种其他用途。
所谓透视,其实是一种投影。是从一个点出发,将三维场景投射到画布平面上。有了这套方法,天地立即宽广。《红》的故事之前30年,欧洲人开始使用墨卡托地图。所谓墨卡托投影,是假设球体外切一个圆柱面,视点在球心,从球心看出去,球面在这个圆柱面上的投影,就是墨卡托地图。绘画里的透视和制图中的墨卡托投影,原理上是一回事。这种图对航海特别方便,球面上两点间的最短距离,在墨卡托地图上就是这两点间的直线。有了好的地图制法,就有了可靠的海图,美洲就能开发,印度就能征服,商业就能发展,世界市场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就能发展,等等———这里可以放入《共产党宣言》中描述地理大发现之后资本全球化的全部段落。
英国印制很多精美地图集。手头有本《新世界:地理大发现时期的地图》。翻看16世纪一百年间的各类地图,投影地图看上去明显地更正规,更像现在的地图。而如今的地图,都是用各种投影法绘制的。
再回想一下,《红》中的苏丹,为什么不惜重金要编那本图书?———苏丹想在书里展示奥斯曼帝国的富裕和先进,用当今时髦说法,这叫作扩大民族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用图书恐吓威尼斯的起因,则是奥斯曼帝国觉得塞浦路斯在去麦加朝拜的海路上,要把这个岛从威尼斯人那里夺过来,结果吃了大败仗。塞浦路斯就在土耳其家门口;而威尼斯人要从地中海西边大老远地坐船过来,他们能打赢,显然有航海优势。较为精确的投影地图,或许就是威尼斯优势的一部分。
在小说之外的真实历史里,姨夫的预言应验了,土耳其人开始被迫向西方看齐;而凶手的预言也应验了,几代人都学不像,他们缺乏在西方萌芽的现代科学观念。蹉跎之间,世界已经是别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