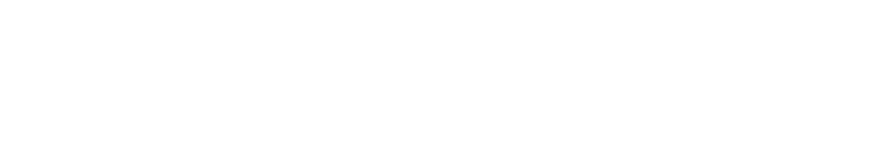浩然,祝福你来生一片艳阳天
|
||||||||||||||||||
简介:
浩然,祝福你来生一片艳阳天
2008年03月08日 19:28南方报业网
●浩然(1932-2008),原名梁金广,1954年起任《河北日报》记者、北京《俄文友好报》记者、《红旗》杂志编辑。1964年到北京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任作协北京分会主席。1956年开始发表小说,1965年出版了代表作、长篇小说《艳阳天》,1972年出版了另一长篇《金光大道》。1974年发表了宣扬“文革”思想的中篇《西沙儿女》和《百花川》。粉碎“四人帮”后,出版了长篇小说《山情》(又名《男婚女嫁》)、《苍生》,自传体长篇小说《乐土》、《活泉》、《圆梦》三部等。

2月20日,“高大全”代表作家浩然辞世。与其用《艳阳天》、《金光大道》所秉持的判断方式评价浩然以及那个时代,不如设身处地扪心自问——换了我又将如何?
“他是矛盾的,有时候坚定,有时候怀疑;有时候认为自己是对的,有时候又认为错了。”“但是外界批评的时候他就会坚持。他的精神很脆弱,有一点打击就受不住。有时候他跟人说话,突然就会眼泪汪汪。”
李青是1981年认识浩然的。作为北京市作协常务副主席,李青与浩然共事二十多年。
最初在北京市文联,浩然参加活动比较少。大多时候他住在北京郊区——通州、延庆、密云以及河北省三河县。第一次见到浩然时,李青感觉他很像小说《艳阳天》中的主人公萧长春:短发,国字脸,很爱笑。如果心结不被触动,浩然的神情总是快乐的。1980年代初期他处于寂寞和抑郁之中,那时候他远离文坛,后来才慢慢地回到集体生活中。
“他是江青看重的作家,但感觉他被动的时候多。‘文革’之后,他还能把自己拉回来。”“他不像文艺界另外几个跟定江青的人,比如钱浩亮、刘庆棠和张永枚,他们陷得很深,最后身败名裂。浩然一直没越过自己的底线,他还能回到一个作家的状态。”
李青最后一次见到浩然,是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浩然在透析,在长达五年的植物状态之后,他已经完全失去知觉。”
2月20日凌晨2时32分,病卧床榻多年的浩然辞世,享年76岁。
“喜鹊登枝”
《新农村的新面貌》是叶圣陶老先生写给浩然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的评论,这本小说集出版于1958年,其时浩然26岁。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的叶圣陶用不无热情的文字评论道:
“光就收进集子里的十一篇短篇看,已经可以从多方面见到,在被革命唤醒的新农村里,人的面貌是怎样的焕然一新,人与人的关系是怎样发生亘古未有的变化。”
浩然在《人民日报》的广告栏中看到了这篇文章的预告,随后急忙骑上自行车赶往东四邮局,买到登载那篇文章的刊物后,急不可待地坐在营业大厅的长椅上阅读起来。
跟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一起来到这个世界的还有浩然的女儿春水。
此时,因为沉迷于作家梦,浩然在单位背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罪名,当女儿在东四一家妇产科医院瓜熟蒂落之时,印刷工人们正在装订那本天蓝色封面的书。几天后的正晌午,女儿正在母亲怀里吃奶,邮递员把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新书送到浩然供职的《俄文友好报》南门口的收发室中。
这是浩然步入文坛的开始,此后他在文学界崭露头角。
《人民文学》杂志社前副主编崔道怡是浩然短篇小说的责任编辑。从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除去《人民文学》被迫停刊的时间,浩然发表在《人民文学》的短篇小说都是经崔道怡编辑发表的。
在浩然辞世之际,头发雪白的崔道怡在他的寓所回忆起往昔的时光:“他的小说文字顺畅,意境优美,结构也很巧妙,拿来就可以发表。他写的乡村都是光明的,美好的。在我接触的作家中,他是一个非常朴实的,真正有乡土气质的作家,待人接物非常诚恳,实际上他已经不是农民了,而是农村干部,但他对土地,对家乡,对农村,对农民是充满感情的,这种感情是真的,不是做出来的。”
“后来我从朋友那儿知道,当时浩然对农村的社会现实也不是没有看法,他说某些农村干部像地痞流氓。他怎么办呢?他越是见到不好的,就越在心里创造一个美好的理想出来。”
浩然出道时,一批作家已先后受到冲击,被划成右派,比如王蒙,刘宾雁,刘绍棠,丛维熙,李国文,邓友梅……文学界从百花齐放变得百花凋残。
浩然的出现恰逢其时,他写新农村、新农民,写农业合作化、农民走集体道路。他的小说都是歌颂性的,充满阳光的,当那些写社会矛盾的作家都成了右派以后,他的小说成了最适合政治潮流的作品。从他登上文坛的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中期,他成了惟一没有问题的作家。
浩然后来出版的三卷本、126万字的《艳阳天》,是崔道怡建议他扩展补充的,最初这部小说只有20万字。崔道怡详细看了手稿,提了具体意见,1962年至1965年,浩然把《艳阳天》改成了三卷本。这部反映19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小说使浩然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也成了那个时代的一面旗帜。
“为什么浩然可以被接受,老舍不可以被接受?因为浩然出身好,所谓根正苗红。我觉得老舍也是矛盾的,他一面要配合现实,另一面要坚持写自己的东西,领导就没把他当自己人看。老舍最后还是被逼死,自沉太平湖”。崔道怡说。
这张极具“文革”美学特征的图片摄于1975年,浩然在京郊密云县下乡,他是那个时代中国文学的一面红旗
“打骡子马也惊”
1932年,浩然出生于河北省开滦赵各庄煤矿。他的家就在矿区的大粪场子,出门就是摊晒着的或堆积着的大粪干儿,到处弥漫着熏人的臭气。曾经一度举家回归祖籍宝坻县单家庄居住,再后来,浩然举家搬到蓟县王吉素村落户,父母双亡,沦为举目无亲的孤儿。
浩然13岁前念过3年小学、半年私塾。他不安心当农民,不情愿在小山村度过窝囊的一生,爱写写画画,爱看书,致使地里的庄稼种不好,棚里的牲口喂得不壮。因此而遭到乡亲们的轻蔑,背后诋毁他是“王吉素最没出息的人”。那时候的浩然想到唐山瓷器厂学手艺,想成为一名身怀绝技、能挣到大钱的画匠师傅。结果因为那个工厂里没有熟人引荐而无门可入,终成泡影。
正当浩然收回野马一样的心,打定主意要苦学农活,不惜出大汗受大累,当一名“合格的庄稼人”的时候,“共产党跟国民党夺取政权的仗打起来。共产党的民主政府曾经出面做主,没有让企图霸占独吞我家财产的舅舅得逞,保住了我的房屋土地,我对共产党感恩,因此在两军生死拼搏的关头,我很自然地站在了共产党的一边。”
浩然打定主意,等到天下太平了,就回到家,种那八亩平川地。意外的是浩然被蓟县县委送到地委党校学习,学习了《社会发展简史》,看了苏联集体农庄的纪录片,听了一位到过苏联、亲眼看到那里的人过上社会主义幸福生活的同志的报告,年轻的心被点燃起火苗子。
1948年11月,16岁的浩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村、区、县青年和党政干部8年。
然而,单纯做农村的基层工作并不能满足浩然的精神需求。自17岁做起文学梦开始,浩然下决心,补充先天不足的文化知识,磨练好笔杆子,效仿古典小说《水浒传》和当代名篇《新儿女英雄传》的样子写农村,写农民。
“我的根子扎在农村的黄土地上,我的血管里流动的是农民的血……农民父老们对我是有恩的,而且恩重如山,终生难报。”
文学上崭露头角,浩然也迎来了工作的变动。1956年他被调到《俄文友好报》。从省报调到中央,从保定调到北京,浩然在自述中这样写道:“这个时候,我们国家历史上有名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哗啦啦地展开了,震天动地的口号是‘超英赶美’、‘向共产主义天堂进军’。那气势真是汹涌澎湃,排山倒海一般。”
浩然得到《北京文艺》的入场券,就是1957年在正义路青年团中央礼堂旁听了一次批判刘绍棠的大会。
他的感觉是“受到了教育”,“灵魂被震撼了”。
万花凋谢,一枝独秀
在1965年出版的《艳阳天》的后记中,浩然写道:“我要永远往高攀登,坚决做一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又红又专的文艺战士”。
小说《艳阳天》及他的写作才能受到江青多次肯定,并在文艺极度萧条时被改编为同名电影(长春电影制片厂1973年出品,导演林农,主演张连文、郭振清、张明子、马精武)。在天桥剧场、钓鱼台、大寨、人民大会堂等地多次得到江青的接见。
学者陈思和在论及浩然作品时写道:“浩然是‘文革’时期有幸可以在新华书店里陈列自己作品的作家……在一片肃杀的文学空间,除了样板戏和一些拙劣图解政治的文字以外,唯一可以当作文学作品看看的合法创作大概就数浩然的小说了。”
“浩然的创作开始于50年代,民间性的自发成份还相当浓厚,他的作品清新活泼,内容多写新人新事,虽然肤浅,但浅得可爱。但从1960年代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来,他的创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标志是长篇小说《艳阳天》的出版。这部作品在‘万花纷谢一时稀’的年代里能够一枝独秀决不是偶然的幸运,而是它能够直接图解出一幅农村阶级斗争的图像:作者用‘两军对阵’的二元对立的模式,写出了一个合作社在麦收以前的15天里发生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敌人’的一方,不但党内外相勾结,而且与城市里的右派挂起钩来;不但思想路线上有分歧,而且还杀人闹事,萧长春之流就在这样虚构的”战争“中成了风口浪尖的英雄人物。这样的生活图像,戏剧性当然很强,但究竟是真实地反映了农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民的精神面貌,还是为了图解错误的政治口号而歪曲了生活真实,在经过了惨痛教训以后的今天,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浩然被军宣队为主的工作组推举为北京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他参加了中共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四届全国人大,1976年9月成为文学界唯一参加毛泽东治丧委员会的代表,常以“文学工作者”、“文化界人士”名义参加外事接待、见诸报端,曾出访日本。
1978年,浩然受到清查,被解除全国人大常委、委员职务。结论是“不是帮派分子,在‘文革’中摔了跤,但没有完全陷进去”。
1979年被流放后重回北京的王蒙成为北京市文联的专业作家,后来在《王蒙自传:大块文章》里忆及当时文联诸公对浩然的态度:“管桦、杨沫都对浩然印象很好,大多一般工作人员与司机也都喜欢浩然,道理之一是浩然对自己的年龄大4岁没有上过什么学的发妻态度极好,这在中国是好人和坏人分野的一个标志。浩然对农民业余写作者的态度也一直比较好,而对作家同行却多了些提防。爱体力劳动者而防脑力劳动者,这大概也算一种阶级感情,也是多年宣传教育引导的结果。另外有几位老作家,对别人在‘文革’中挨整而浩然一花独秀,尤其是浩然当‘文革’头目时的一次红卫兵批斗大会耿耿于怀。此次会后老舍自杀了,那还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前,浩然说他极力保护那些作家,怕闹出人命关天的大事。而另一位老作家坚持说是浩然说过打死也没关系。”
“文革”结束后不久,邵燕祥在林斤澜家见过浩然一面,后又一同参与过一次会见苏联某加盟共和国作家。1979年,林斤澜在家摆了两次“团结宴”。两次都有浩然、王蒙、邵燕祥、邓友梅、丛维熙、刘绍棠。
邵燕祥说:“我听说,即使在‘文革’中,他正所谓当红之时,慑于江青的歇斯底里,浩然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有一次,他去拜望一位高级军官,说起他的烦恼或恐惧,那位军官在室内踱步良久,问:‘你就没有一点什么病吗?’在这样的暗示下,浩然休过病假。这件传闻可以部分地说明当时的政治气氛和浩然在特殊处境下的态度,他在那个非正常时期,不是一个恶人。”
1998年秋,在经历长久的沉默之后复出的浩然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谈到准备写自传,要“说清楚”自己“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受了伤的文艺战士”。
然而,他已经无法说清楚,说清楚的努力使他获得了更强烈的批评。
“失去的感觉能力”
北京市作协副主席刘庆邦是读中学时候知道浩然的,1965年刚读初一时,他就读了《艳阳天》。
参加工作以后到了煤矿,刘庆邦又读了浩然的《金光大道》,读他的小说集《春雨集》,其中收了他的很多短篇,包括《喜鹊登枝》。“他的小说里边爱情挺美好的。他写的农村生活,对一个农村的孩子来说还是很亲切的。”
1989年以后,浩然复出,先是担任《北京文学》主编,后又当选北京市作协主席,北京市文联副主席。
刘庆邦是到了北京以后跟浩然见面认识的。“在认识他之前我已经在《北京文学》发表不少小说,我有一篇小说已经被审定,是写老地主还乡的短篇小说,叫《汉爷》,浩然当了《北京文学》主编以后有人告诉我可能那篇小说发不出来了。大家认为他比较‘左’,而且我的小说正是对阶级斗争观念的反驳,是写一个老地主回乡去找他的情人所遭遇的一系列打击。但那篇小说还是发了,发得位置还不错。这是浩然当了主编以后发表的我的第一篇小说。”
后来刘庆邦跟浩然交往的机会就多了。那时候浩然虽然也在写东西,但跟当时的文学潮流不大融合,说是不大跟得上潮流也好,说是排斥也好,总之,浩然那时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过气的作家。
和诸多对浩然小说的批评不同,刘庆邦以他职业作家的鉴赏力表达了对浩然小说的看法:“他写《艳阳天》,截取的那段生活正是新中国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正是新中国生机勃勃的时候,有种欣欣向荣的感觉。合作化的初期,大家都有对共同富裕的向往,对集体生活的向往,我看他写得确实是热气腾腾,应该说有真实的地方。”
“等我们长大了,有自己的眼睛之后,我们看到的生活跟他写的完全不一样。大跃进,中国农村出现的大面积的饥饿,大面积的浮肿,饿死,自己也饿得吃不饱,那时候再看他的小说就不能认同,很排斥。《艳阳天》还可以接受,《金光大道》就完全不能接受。”
“然而,浩然在晚年也没有反省自己。他表示不后悔,强调他写的都是真实的生活。也许他看生活就是那么看的。很可能他就是那样思考的。我觉得这样一个作家,确实值得深入研究。”
刘庆邦最后一次见浩然是在2002年,参加中国作协全委会议的时候。患脑血栓之后,浩然反应不那么敏捷了。
“他穿件大红毛衣,满头银发。跟他说话,他光笑,笑得很慈祥,但言语表达能力已经跟不上了。后来浩然就因为脑血栓成植物状态,他完全失去了跟人交流的能力。”
2008年03月08日 19:28南方报业网
●浩然(1932-2008),原名梁金广,1954年起任《河北日报》记者、北京《俄文友好报》记者、《红旗》杂志编辑。1964年到北京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任作协北京分会主席。1956年开始发表小说,1965年出版了代表作、长篇小说《艳阳天》,1972年出版了另一长篇《金光大道》。1974年发表了宣扬“文革”思想的中篇《西沙儿女》和《百花川》。粉碎“四人帮”后,出版了长篇小说《山情》(又名《男婚女嫁》)、《苍生》,自传体长篇小说《乐土》、《活泉》、《圆梦》三部等。

2月20日,“高大全”代表作家浩然辞世。与其用《艳阳天》、《金光大道》所秉持的判断方式评价浩然以及那个时代,不如设身处地扪心自问——换了我又将如何?
“他是矛盾的,有时候坚定,有时候怀疑;有时候认为自己是对的,有时候又认为错了。”“但是外界批评的时候他就会坚持。他的精神很脆弱,有一点打击就受不住。有时候他跟人说话,突然就会眼泪汪汪。”
李青是1981年认识浩然的。作为北京市作协常务副主席,李青与浩然共事二十多年。
最初在北京市文联,浩然参加活动比较少。大多时候他住在北京郊区——通州、延庆、密云以及河北省三河县。第一次见到浩然时,李青感觉他很像小说《艳阳天》中的主人公萧长春:短发,国字脸,很爱笑。如果心结不被触动,浩然的神情总是快乐的。1980年代初期他处于寂寞和抑郁之中,那时候他远离文坛,后来才慢慢地回到集体生活中。
“他是江青看重的作家,但感觉他被动的时候多。‘文革’之后,他还能把自己拉回来。”“他不像文艺界另外几个跟定江青的人,比如钱浩亮、刘庆棠和张永枚,他们陷得很深,最后身败名裂。浩然一直没越过自己的底线,他还能回到一个作家的状态。”
李青最后一次见到浩然,是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浩然在透析,在长达五年的植物状态之后,他已经完全失去知觉。”
2月20日凌晨2时32分,病卧床榻多年的浩然辞世,享年76岁。
“喜鹊登枝”
《新农村的新面貌》是叶圣陶老先生写给浩然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的评论,这本小说集出版于1958年,其时浩然26岁。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的叶圣陶用不无热情的文字评论道:
“光就收进集子里的十一篇短篇看,已经可以从多方面见到,在被革命唤醒的新农村里,人的面貌是怎样的焕然一新,人与人的关系是怎样发生亘古未有的变化。”
浩然在《人民日报》的广告栏中看到了这篇文章的预告,随后急忙骑上自行车赶往东四邮局,买到登载那篇文章的刊物后,急不可待地坐在营业大厅的长椅上阅读起来。
跟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一起来到这个世界的还有浩然的女儿春水。
此时,因为沉迷于作家梦,浩然在单位背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罪名,当女儿在东四一家妇产科医院瓜熟蒂落之时,印刷工人们正在装订那本天蓝色封面的书。几天后的正晌午,女儿正在母亲怀里吃奶,邮递员把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新书送到浩然供职的《俄文友好报》南门口的收发室中。
这是浩然步入文坛的开始,此后他在文学界崭露头角。
《人民文学》杂志社前副主编崔道怡是浩然短篇小说的责任编辑。从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除去《人民文学》被迫停刊的时间,浩然发表在《人民文学》的短篇小说都是经崔道怡编辑发表的。
在浩然辞世之际,头发雪白的崔道怡在他的寓所回忆起往昔的时光:“他的小说文字顺畅,意境优美,结构也很巧妙,拿来就可以发表。他写的乡村都是光明的,美好的。在我接触的作家中,他是一个非常朴实的,真正有乡土气质的作家,待人接物非常诚恳,实际上他已经不是农民了,而是农村干部,但他对土地,对家乡,对农村,对农民是充满感情的,这种感情是真的,不是做出来的。”
“后来我从朋友那儿知道,当时浩然对农村的社会现实也不是没有看法,他说某些农村干部像地痞流氓。他怎么办呢?他越是见到不好的,就越在心里创造一个美好的理想出来。”
浩然出道时,一批作家已先后受到冲击,被划成右派,比如王蒙,刘宾雁,刘绍棠,丛维熙,李国文,邓友梅……文学界从百花齐放变得百花凋残。
浩然的出现恰逢其时,他写新农村、新农民,写农业合作化、农民走集体道路。他的小说都是歌颂性的,充满阳光的,当那些写社会矛盾的作家都成了右派以后,他的小说成了最适合政治潮流的作品。从他登上文坛的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中期,他成了惟一没有问题的作家。
浩然后来出版的三卷本、126万字的《艳阳天》,是崔道怡建议他扩展补充的,最初这部小说只有20万字。崔道怡详细看了手稿,提了具体意见,1962年至1965年,浩然把《艳阳天》改成了三卷本。这部反映19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小说使浩然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也成了那个时代的一面旗帜。
“为什么浩然可以被接受,老舍不可以被接受?因为浩然出身好,所谓根正苗红。我觉得老舍也是矛盾的,他一面要配合现实,另一面要坚持写自己的东西,领导就没把他当自己人看。老舍最后还是被逼死,自沉太平湖”。崔道怡说。
这张极具“文革”美学特征的图片摄于1975年,浩然在京郊密云县下乡,他是那个时代中国文学的一面红旗
“打骡子马也惊”
1932年,浩然出生于河北省开滦赵各庄煤矿。他的家就在矿区的大粪场子,出门就是摊晒着的或堆积着的大粪干儿,到处弥漫着熏人的臭气。曾经一度举家回归祖籍宝坻县单家庄居住,再后来,浩然举家搬到蓟县王吉素村落户,父母双亡,沦为举目无亲的孤儿。
浩然13岁前念过3年小学、半年私塾。他不安心当农民,不情愿在小山村度过窝囊的一生,爱写写画画,爱看书,致使地里的庄稼种不好,棚里的牲口喂得不壮。因此而遭到乡亲们的轻蔑,背后诋毁他是“王吉素最没出息的人”。那时候的浩然想到唐山瓷器厂学手艺,想成为一名身怀绝技、能挣到大钱的画匠师傅。结果因为那个工厂里没有熟人引荐而无门可入,终成泡影。
正当浩然收回野马一样的心,打定主意要苦学农活,不惜出大汗受大累,当一名“合格的庄稼人”的时候,“共产党跟国民党夺取政权的仗打起来。共产党的民主政府曾经出面做主,没有让企图霸占独吞我家财产的舅舅得逞,保住了我的房屋土地,我对共产党感恩,因此在两军生死拼搏的关头,我很自然地站在了共产党的一边。”
浩然打定主意,等到天下太平了,就回到家,种那八亩平川地。意外的是浩然被蓟县县委送到地委党校学习,学习了《社会发展简史》,看了苏联集体农庄的纪录片,听了一位到过苏联、亲眼看到那里的人过上社会主义幸福生活的同志的报告,年轻的心被点燃起火苗子。
1948年11月,16岁的浩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村、区、县青年和党政干部8年。
然而,单纯做农村的基层工作并不能满足浩然的精神需求。自17岁做起文学梦开始,浩然下决心,补充先天不足的文化知识,磨练好笔杆子,效仿古典小说《水浒传》和当代名篇《新儿女英雄传》的样子写农村,写农民。
“我的根子扎在农村的黄土地上,我的血管里流动的是农民的血……农民父老们对我是有恩的,而且恩重如山,终生难报。”
文学上崭露头角,浩然也迎来了工作的变动。1956年他被调到《俄文友好报》。从省报调到中央,从保定调到北京,浩然在自述中这样写道:“这个时候,我们国家历史上有名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哗啦啦地展开了,震天动地的口号是‘超英赶美’、‘向共产主义天堂进军’。那气势真是汹涌澎湃,排山倒海一般。”
浩然得到《北京文艺》的入场券,就是1957年在正义路青年团中央礼堂旁听了一次批判刘绍棠的大会。
他的感觉是“受到了教育”,“灵魂被震撼了”。
万花凋谢,一枝独秀
在1965年出版的《艳阳天》的后记中,浩然写道:“我要永远往高攀登,坚决做一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又红又专的文艺战士”。
小说《艳阳天》及他的写作才能受到江青多次肯定,并在文艺极度萧条时被改编为同名电影(长春电影制片厂1973年出品,导演林农,主演张连文、郭振清、张明子、马精武)。在天桥剧场、钓鱼台、大寨、人民大会堂等地多次得到江青的接见。
学者陈思和在论及浩然作品时写道:“浩然是‘文革’时期有幸可以在新华书店里陈列自己作品的作家……在一片肃杀的文学空间,除了样板戏和一些拙劣图解政治的文字以外,唯一可以当作文学作品看看的合法创作大概就数浩然的小说了。”
“浩然的创作开始于50年代,民间性的自发成份还相当浓厚,他的作品清新活泼,内容多写新人新事,虽然肤浅,但浅得可爱。但从1960年代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来,他的创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标志是长篇小说《艳阳天》的出版。这部作品在‘万花纷谢一时稀’的年代里能够一枝独秀决不是偶然的幸运,而是它能够直接图解出一幅农村阶级斗争的图像:作者用‘两军对阵’的二元对立的模式,写出了一个合作社在麦收以前的15天里发生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敌人’的一方,不但党内外相勾结,而且与城市里的右派挂起钩来;不但思想路线上有分歧,而且还杀人闹事,萧长春之流就在这样虚构的”战争“中成了风口浪尖的英雄人物。这样的生活图像,戏剧性当然很强,但究竟是真实地反映了农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民的精神面貌,还是为了图解错误的政治口号而歪曲了生活真实,在经过了惨痛教训以后的今天,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浩然被军宣队为主的工作组推举为北京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他参加了中共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四届全国人大,1976年9月成为文学界唯一参加毛泽东治丧委员会的代表,常以“文学工作者”、“文化界人士”名义参加外事接待、见诸报端,曾出访日本。
1978年,浩然受到清查,被解除全国人大常委、委员职务。结论是“不是帮派分子,在‘文革’中摔了跤,但没有完全陷进去”。
1979年被流放后重回北京的王蒙成为北京市文联的专业作家,后来在《王蒙自传:大块文章》里忆及当时文联诸公对浩然的态度:“管桦、杨沫都对浩然印象很好,大多一般工作人员与司机也都喜欢浩然,道理之一是浩然对自己的年龄大4岁没有上过什么学的发妻态度极好,这在中国是好人和坏人分野的一个标志。浩然对农民业余写作者的态度也一直比较好,而对作家同行却多了些提防。爱体力劳动者而防脑力劳动者,这大概也算一种阶级感情,也是多年宣传教育引导的结果。另外有几位老作家,对别人在‘文革’中挨整而浩然一花独秀,尤其是浩然当‘文革’头目时的一次红卫兵批斗大会耿耿于怀。此次会后老舍自杀了,那还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前,浩然说他极力保护那些作家,怕闹出人命关天的大事。而另一位老作家坚持说是浩然说过打死也没关系。”
“文革”结束后不久,邵燕祥在林斤澜家见过浩然一面,后又一同参与过一次会见苏联某加盟共和国作家。1979年,林斤澜在家摆了两次“团结宴”。两次都有浩然、王蒙、邵燕祥、邓友梅、丛维熙、刘绍棠。
邵燕祥说:“我听说,即使在‘文革’中,他正所谓当红之时,慑于江青的歇斯底里,浩然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有一次,他去拜望一位高级军官,说起他的烦恼或恐惧,那位军官在室内踱步良久,问:‘你就没有一点什么病吗?’在这样的暗示下,浩然休过病假。这件传闻可以部分地说明当时的政治气氛和浩然在特殊处境下的态度,他在那个非正常时期,不是一个恶人。”
1998年秋,在经历长久的沉默之后复出的浩然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谈到准备写自传,要“说清楚”自己“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受了伤的文艺战士”。
然而,他已经无法说清楚,说清楚的努力使他获得了更强烈的批评。
“失去的感觉能力”
北京市作协副主席刘庆邦是读中学时候知道浩然的,1965年刚读初一时,他就读了《艳阳天》。
参加工作以后到了煤矿,刘庆邦又读了浩然的《金光大道》,读他的小说集《春雨集》,其中收了他的很多短篇,包括《喜鹊登枝》。“他的小说里边爱情挺美好的。他写的农村生活,对一个农村的孩子来说还是很亲切的。”
1989年以后,浩然复出,先是担任《北京文学》主编,后又当选北京市作协主席,北京市文联副主席。
刘庆邦是到了北京以后跟浩然见面认识的。“在认识他之前我已经在《北京文学》发表不少小说,我有一篇小说已经被审定,是写老地主还乡的短篇小说,叫《汉爷》,浩然当了《北京文学》主编以后有人告诉我可能那篇小说发不出来了。大家认为他比较‘左’,而且我的小说正是对阶级斗争观念的反驳,是写一个老地主回乡去找他的情人所遭遇的一系列打击。但那篇小说还是发了,发得位置还不错。这是浩然当了主编以后发表的我的第一篇小说。”
后来刘庆邦跟浩然交往的机会就多了。那时候浩然虽然也在写东西,但跟当时的文学潮流不大融合,说是不大跟得上潮流也好,说是排斥也好,总之,浩然那时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过气的作家。
和诸多对浩然小说的批评不同,刘庆邦以他职业作家的鉴赏力表达了对浩然小说的看法:“他写《艳阳天》,截取的那段生活正是新中国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正是新中国生机勃勃的时候,有种欣欣向荣的感觉。合作化的初期,大家都有对共同富裕的向往,对集体生活的向往,我看他写得确实是热气腾腾,应该说有真实的地方。”
“等我们长大了,有自己的眼睛之后,我们看到的生活跟他写的完全不一样。大跃进,中国农村出现的大面积的饥饿,大面积的浮肿,饿死,自己也饿得吃不饱,那时候再看他的小说就不能认同,很排斥。《艳阳天》还可以接受,《金光大道》就完全不能接受。”
“然而,浩然在晚年也没有反省自己。他表示不后悔,强调他写的都是真实的生活。也许他看生活就是那么看的。很可能他就是那样思考的。我觉得这样一个作家,确实值得深入研究。”
刘庆邦最后一次见浩然是在2002年,参加中国作协全委会议的时候。患脑血栓之后,浩然反应不那么敏捷了。
“他穿件大红毛衣,满头银发。跟他说话,他光笑,笑得很慈祥,但言语表达能力已经跟不上了。后来浩然就因为脑血栓成植物状态,他完全失去了跟人交流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