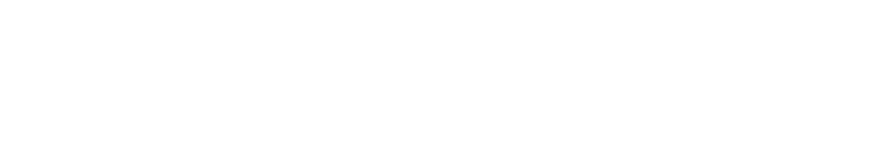朱熹 圣人以无讼为贵
|
||||||||||||||||||
简介:
朱熹 圣人以无讼为贵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在与网友互动时表示:老百姓能不打官司尽量不要打官司,更不要敢于打官司。法院的案件越来越少,是社会越来越和谐的一个表征。

张军的话,其实暗合中国传统社会中官方长期倡导的“息讼”观念。此种观念起自春秋,而至明清为盛。
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朱熹对此解释说:“圣人不以听讼为能,而以无讼为贵”。要到达这一境界,无非是靠道德教化。在儒家泛道德主义的指引下,遂催生“息讼”观念。有意思的是,注重典律的法家,同样支持“息讼”。与儒家不同的是,法家不靠道德教化,而以严刑峻法“使民无讼”,从而“德生于刑”。儒家的道德,法家的严刑,一阴一阳,就构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压制诉讼的基调,所谓“安民之道,首先息讼”。(值得注意的是,“息讼”之“讼”,主要是“词讼”,其与“案件”不同,二者存在“民刑之分”。前者多属民事案件,后者多属刑事案件。不过,二者之间,也常发生由“词讼”到“案件”的转换。)
春秋末期的邓析也许是“息讼”观念最早的打击对象,他因传授法律辩论之术,代民诉讼而被杀。邓析案可说包含了此后数千年讼师行业的全部要素:私家表达法意,与官方权力对峙;授徒研习辩论,培养法学人才;代理诉讼收费,形成业务市场;晓百姓以民权,导向民间健讼;被王权打压,乃至杀身成殉。
抵至清代,“息讼”观念逐步条文化,首要手段是制订“教唆词讼”之例,以打击讼师,达到息讼目的。康熙、雍正皆有相关例文,至乾嘉时管制更猛。乾隆二十九年,根据江苏按察使钱琦所奏《请严积惯讼棍例》,修订了八条例文,规定教唆词讼者与犯人同罪,地方官必须严查讼师,若有失察,将获降级、罚俸等处分。与此同时,清廷也以宣讲法律或禁止民间获得法律知识来息讼。清康熙圣谕16条第8条即是“讲法律以儆愚顽”,雍正《圣谕广训》对此条阐述说:“……见法知惧、观律怀刑……惧法自不犯法,畏刑自可免刑”。乾隆时则相反,规定普通百姓不得藏《大清律例》,更严厉追查禁毁所谓“讼师秘本”。官方宣讲法律,是为了民间畏惧法律,不犯法而息讼;禁止民间获得法律知识,则是釜底抽薪的愚民政策,同样是为了息讼。
在息讼政策之下,清代讼师的地位相当尴尬。
首先,讼师的职业身份,从未得到官方承认。讼师的活动,也多是非公开的。《清稗类钞》中记录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某讼师夜归,身携讼状,被当地官员碰着,索看。讼师担心获谴,将讼状一把吞进肚子,说:文章太烂,不好污大人眼。讼师之狼狈鬼祟,可见一斑。而如果按照嘉庆二十二年的定例,“凡有控告事件者,其呈词俱责令自作,不能自作者,准其口诉……代书之人,照例治罪。其唆讼棍徒……从重究办”,则所有讼师的职业活动均属非法。不过此例并未严格执行,因为不切实际。
其次,讼师的作为空间相对有限。讼师只能在状辞方面下功夫,或者打点官员、胥吏、幕友,搞些小动作,并不能堂而皇之地出庭辩论。周星驰电影中常见的讼师当庭激辩,乃至扳倒父母官的场景,在实际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
更糟糕的是,讼师还常被“恶搞”。嘉庆间就有讼师被以“讼棍”二字刺面,流放边远。乾嘉时期的名幕汪辉祖也曾大谈自己如何羞辱讼师,将后者绑在公堂,大加嘲斥,民众看见其落魄状,对其包讼手段自然失望。不止平日如此,即使遇到大赦,“积惯讼师”也不得优待。譬如嘉庆间江西按察史甄别恩赦人员,有29条不能援免,与讼师直接相关的就有5条。有讼师年过70岁,按例当免,也不得宽大,仍发往边远充军。官方对讼师之恨,可谓入骨。(清代讼师的遭遇,或许不止是讼师或与讼百姓的不幸,也是帝国的不幸。美国学者麦考利发现,16-19世纪的欧洲律师打破社会权力的多样性,确立中央法院的合法性,从而使近代国家成为可能。但在清代中国,讼师并非与法庭对抗的制度性竞争者,当事人在衙门的诉讼,在政治上不能促成政权合法化,在制度上也不能提升司法效率。而缺乏协商与契约的政权,终于无法构建催生近代国家的法律与行政大厦。)
但严治讼师,并不能达到息讼的目的。自明中叶起,关于民间健讼的记载就颇多,其主要地区是江南。而在清代,这范围更扩大至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区。学者黄宗智指出,清代乃是健讼社会,在清后半期,县衙门平均每年要处理150件左右的民事案件。这对“一人政府”的县级政权而言,确是不小负担。
清代民间健讼,究其根源,一是民间重视现实利益,并不为名教道德所阻。二是地方官员效率低下,常拖延不结,而民事案件又无上诉次数限制,遂反复生讼。清人袁枚对此有深刻反思:“今之人不能听讼,先求无讼;不过严状式、诛讼师,诉之而不知,号之而不理,曰吾以息讼云尔。此如防川,怨气不伸,讼必愈多。”三是吏治普遍腐败,断案不公屡有发生,百姓不服,自然再讼。此外,一些地区也确实存在讼师挑唆,借此获利的情况。不过,清代官方妖魔化讼师的记载不可尽信。任何时代,任何职业,都既有无良杂种,也有特出之辈。如《九命奇冤》中的施智伯,就是讼师中的杰士,他不但讼状写作水平极高,而且人格闪亮,“若是拿了钱请教他,他向来不肯做的;要碰着他路见不平,却是分文不受,登时就代人作了”。清人王有孚的议论比较中肯,他认为有教唆词讼、拨弄乡愚、恐吓良善,并在官司中上下其手的讼棍,也有摘伏发奸至冤者得白、有功于世的讼师,结论是“讼棍必当惩而讼师不必禁”。
民间健讼之习既盛,且不可抑,清廷为何不能正视,仍要坚持采取近似于掩耳盗铃的息讼政策呢?首先是因为传统中华帝国的统治者,始终坚持道德主义的国家治理模式,此点在文初即已简述。黄宗智更指出,清代政府对于民事纠纷,最关心的不是权利的保护,而是纠纷的化解。理想的道德社会是和谐共处,互不冲突,因此不应该有纠纷,更不用说诉讼。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民事诉讼被概念化为“细事”,地方政府有权自理,而兴讼也被视作道德低劣者的行为。其次是帝国官僚有难言之隐,就其质量与数量而言,都不能负荷民间之健讼。清代官僚,多出于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本就不具备法律知识,而在官僚从政期间,也没有相关的法律培训,且司法技术也非官员升迁贬谪的评价指标。实际上担任审判任务并草拟判决稿的司法人员是刑名幕友(幕友有时非常强势,譬如汪辉祖做幕友时,就常固执己见,不肯改判词,最终其东家只好沿用其判),操控取证、听讼过程的则还有衙门胥吏文书。对于帝国官僚在法律方面的颟顸无能,晚清薛允升曾感慨说:“今日之大小官员,能讲读律令者,有几人哉?”不止官员的断案本领堪忧,官员的数量也不足。有学者估算,清代全国正式官员大约只有27000名,其中文官约2万名。他们或处于王权的核心周围,或散落在地方省、州、县,被包围在亿万民众的汪洋大海里。技术含量既不够,人手又匮乏,清代地方官要高效听讼,实在不易。
为掩饰无能,地方官员也有对策。官员审案时“往往乐居内衙而不乐升大堂”,因为内衙可以收放自如,在大堂则往往被围观,致有“诸多未便”。 又有官员干脆内衙都不居,将涉案双方带入密室,不许胥吏在旁,独自密审,“恐被知我审案之法,可一不可再矣。”
然而地方官员的无能,终于无法掩盖;地方司法不力,终于扰及中央。嘉庆十二年,都察院左都御史周廷栋就奏称,近来各省民人赴京上控之案日多,乃是因为地方官对民事讼案不重视,懒于听断,旷日持久,挨延不结,遂激上控之端。
进京上访者有时甚至闹出命案。《刑案汇览》“控争坟山,情急赴京,刎颈呈告”一案,记录嘉道间安徽泾县徐、吴两姓因坟山产权而争讼,最终徐氏进京申诉,在都察院署前自刎身死,吴姓也因此获罪。尸体是弱者最绝望的临终呐喊,也成为讼状最惨烈的修辞手段。对此,刑部以为,访民动不动就来京上访,甚至采取过激行为,应予制约,遂议请:“嗣后凡来京控诉案件,如有在刑部、都察院、步军统领各衙门自伤残者即行拿获,严追主使之人,与自伤未死之犯……分别治罪”。后奉旨,俟修例时纂入例册。(时光流转,全国人大代表、广西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刘庆宁在今年两会的“上访时喊口号、静坐、自残、自杀等应判刑”提案,与此异代同音、遥相呼应。)
要之,清代的息讼政策,并不能真正息讼。清人崔述指出,“自有生民以来,莫不有讼”,《左传》也说“饮食必有讼”。即使圣人尧舜都不能消灭诉讼,何况庸官俗吏。高调息讼,往往只是为强者张目,而使弱者更无力。不过,清代的息讼也有其合理一面。学者沈大明指出,清代自州县衙门到乡村民户之间的社会控制,并不全依赖于国家机器,地方士绅与社会共同体不仅是乡村礼俗和秩序控制的承担者,一定程度上也是法律控制的执行者。许多民间纠纷往往服从于宗族调解,而不一定非走司法诉讼的道路。黄宗智则指出,中国传统的社区调解制度具备其独特优点,息讼也有积极的社会秩序维护功能,而不必在争端中白白浪费诸多社会资源。沈、黄二人的发现,也跟文初最高法副院长张军的倡导暗合。
在我看来,今日重提息讼也好,重视调解也好,均只能作为辅助手段。源于西方的明确维护个人权利的对抗性、必分胜负的法律制度,才是主流。如果一味息讼,压制民众利益诉求,只会造成更大的社会冲突,乃至酿成群体纠纷。道光年间湖北崇阳的“钟九闹漕”即是一例,由讼师钟九领导的民间诉讼,最终却演变为大规模的民间暴动。
彼得·斯坦等著《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中说:“冲突实际上会产生许多能使人类生活更具实际意义的东西。没有冲突,社会就会呆滞,就会灭亡。关键在于社会必须对冲突进行适当的调节,使冲突不以将会毁掉整个社会的暴力方式而进行……必须先有社会秩序,才谈得上社会公平。社会秩序要靠一整套普遍性的法律规则来建立。而法律规则又需要整个社会系统地、正式地使用其力量加以维持”。所谓“和谐社会”,其实质或是“冲突社会”。如此看来,在当代中国,与其息讼,不如健讼。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在与网友互动时表示:老百姓能不打官司尽量不要打官司,更不要敢于打官司。法院的案件越来越少,是社会越来越和谐的一个表征。

张军的话,其实暗合中国传统社会中官方长期倡导的“息讼”观念。此种观念起自春秋,而至明清为盛。
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朱熹对此解释说:“圣人不以听讼为能,而以无讼为贵”。要到达这一境界,无非是靠道德教化。在儒家泛道德主义的指引下,遂催生“息讼”观念。有意思的是,注重典律的法家,同样支持“息讼”。与儒家不同的是,法家不靠道德教化,而以严刑峻法“使民无讼”,从而“德生于刑”。儒家的道德,法家的严刑,一阴一阳,就构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压制诉讼的基调,所谓“安民之道,首先息讼”。(值得注意的是,“息讼”之“讼”,主要是“词讼”,其与“案件”不同,二者存在“民刑之分”。前者多属民事案件,后者多属刑事案件。不过,二者之间,也常发生由“词讼”到“案件”的转换。)
春秋末期的邓析也许是“息讼”观念最早的打击对象,他因传授法律辩论之术,代民诉讼而被杀。邓析案可说包含了此后数千年讼师行业的全部要素:私家表达法意,与官方权力对峙;授徒研习辩论,培养法学人才;代理诉讼收费,形成业务市场;晓百姓以民权,导向民间健讼;被王权打压,乃至杀身成殉。
抵至清代,“息讼”观念逐步条文化,首要手段是制订“教唆词讼”之例,以打击讼师,达到息讼目的。康熙、雍正皆有相关例文,至乾嘉时管制更猛。乾隆二十九年,根据江苏按察使钱琦所奏《请严积惯讼棍例》,修订了八条例文,规定教唆词讼者与犯人同罪,地方官必须严查讼师,若有失察,将获降级、罚俸等处分。与此同时,清廷也以宣讲法律或禁止民间获得法律知识来息讼。清康熙圣谕16条第8条即是“讲法律以儆愚顽”,雍正《圣谕广训》对此条阐述说:“……见法知惧、观律怀刑……惧法自不犯法,畏刑自可免刑”。乾隆时则相反,规定普通百姓不得藏《大清律例》,更严厉追查禁毁所谓“讼师秘本”。官方宣讲法律,是为了民间畏惧法律,不犯法而息讼;禁止民间获得法律知识,则是釜底抽薪的愚民政策,同样是为了息讼。
在息讼政策之下,清代讼师的地位相当尴尬。
首先,讼师的职业身份,从未得到官方承认。讼师的活动,也多是非公开的。《清稗类钞》中记录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某讼师夜归,身携讼状,被当地官员碰着,索看。讼师担心获谴,将讼状一把吞进肚子,说:文章太烂,不好污大人眼。讼师之狼狈鬼祟,可见一斑。而如果按照嘉庆二十二年的定例,“凡有控告事件者,其呈词俱责令自作,不能自作者,准其口诉……代书之人,照例治罪。其唆讼棍徒……从重究办”,则所有讼师的职业活动均属非法。不过此例并未严格执行,因为不切实际。
其次,讼师的作为空间相对有限。讼师只能在状辞方面下功夫,或者打点官员、胥吏、幕友,搞些小动作,并不能堂而皇之地出庭辩论。周星驰电影中常见的讼师当庭激辩,乃至扳倒父母官的场景,在实际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
更糟糕的是,讼师还常被“恶搞”。嘉庆间就有讼师被以“讼棍”二字刺面,流放边远。乾嘉时期的名幕汪辉祖也曾大谈自己如何羞辱讼师,将后者绑在公堂,大加嘲斥,民众看见其落魄状,对其包讼手段自然失望。不止平日如此,即使遇到大赦,“积惯讼师”也不得优待。譬如嘉庆间江西按察史甄别恩赦人员,有29条不能援免,与讼师直接相关的就有5条。有讼师年过70岁,按例当免,也不得宽大,仍发往边远充军。官方对讼师之恨,可谓入骨。(清代讼师的遭遇,或许不止是讼师或与讼百姓的不幸,也是帝国的不幸。美国学者麦考利发现,16-19世纪的欧洲律师打破社会权力的多样性,确立中央法院的合法性,从而使近代国家成为可能。但在清代中国,讼师并非与法庭对抗的制度性竞争者,当事人在衙门的诉讼,在政治上不能促成政权合法化,在制度上也不能提升司法效率。而缺乏协商与契约的政权,终于无法构建催生近代国家的法律与行政大厦。)
但严治讼师,并不能达到息讼的目的。自明中叶起,关于民间健讼的记载就颇多,其主要地区是江南。而在清代,这范围更扩大至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区。学者黄宗智指出,清代乃是健讼社会,在清后半期,县衙门平均每年要处理150件左右的民事案件。这对“一人政府”的县级政权而言,确是不小负担。
清代民间健讼,究其根源,一是民间重视现实利益,并不为名教道德所阻。二是地方官员效率低下,常拖延不结,而民事案件又无上诉次数限制,遂反复生讼。清人袁枚对此有深刻反思:“今之人不能听讼,先求无讼;不过严状式、诛讼师,诉之而不知,号之而不理,曰吾以息讼云尔。此如防川,怨气不伸,讼必愈多。”三是吏治普遍腐败,断案不公屡有发生,百姓不服,自然再讼。此外,一些地区也确实存在讼师挑唆,借此获利的情况。不过,清代官方妖魔化讼师的记载不可尽信。任何时代,任何职业,都既有无良杂种,也有特出之辈。如《九命奇冤》中的施智伯,就是讼师中的杰士,他不但讼状写作水平极高,而且人格闪亮,“若是拿了钱请教他,他向来不肯做的;要碰着他路见不平,却是分文不受,登时就代人作了”。清人王有孚的议论比较中肯,他认为有教唆词讼、拨弄乡愚、恐吓良善,并在官司中上下其手的讼棍,也有摘伏发奸至冤者得白、有功于世的讼师,结论是“讼棍必当惩而讼师不必禁”。
民间健讼之习既盛,且不可抑,清廷为何不能正视,仍要坚持采取近似于掩耳盗铃的息讼政策呢?首先是因为传统中华帝国的统治者,始终坚持道德主义的国家治理模式,此点在文初即已简述。黄宗智更指出,清代政府对于民事纠纷,最关心的不是权利的保护,而是纠纷的化解。理想的道德社会是和谐共处,互不冲突,因此不应该有纠纷,更不用说诉讼。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民事诉讼被概念化为“细事”,地方政府有权自理,而兴讼也被视作道德低劣者的行为。其次是帝国官僚有难言之隐,就其质量与数量而言,都不能负荷民间之健讼。清代官僚,多出于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本就不具备法律知识,而在官僚从政期间,也没有相关的法律培训,且司法技术也非官员升迁贬谪的评价指标。实际上担任审判任务并草拟判决稿的司法人员是刑名幕友(幕友有时非常强势,譬如汪辉祖做幕友时,就常固执己见,不肯改判词,最终其东家只好沿用其判),操控取证、听讼过程的则还有衙门胥吏文书。对于帝国官僚在法律方面的颟顸无能,晚清薛允升曾感慨说:“今日之大小官员,能讲读律令者,有几人哉?”不止官员的断案本领堪忧,官员的数量也不足。有学者估算,清代全国正式官员大约只有27000名,其中文官约2万名。他们或处于王权的核心周围,或散落在地方省、州、县,被包围在亿万民众的汪洋大海里。技术含量既不够,人手又匮乏,清代地方官要高效听讼,实在不易。
为掩饰无能,地方官员也有对策。官员审案时“往往乐居内衙而不乐升大堂”,因为内衙可以收放自如,在大堂则往往被围观,致有“诸多未便”。 又有官员干脆内衙都不居,将涉案双方带入密室,不许胥吏在旁,独自密审,“恐被知我审案之法,可一不可再矣。”
然而地方官员的无能,终于无法掩盖;地方司法不力,终于扰及中央。嘉庆十二年,都察院左都御史周廷栋就奏称,近来各省民人赴京上控之案日多,乃是因为地方官对民事讼案不重视,懒于听断,旷日持久,挨延不结,遂激上控之端。
进京上访者有时甚至闹出命案。《刑案汇览》“控争坟山,情急赴京,刎颈呈告”一案,记录嘉道间安徽泾县徐、吴两姓因坟山产权而争讼,最终徐氏进京申诉,在都察院署前自刎身死,吴姓也因此获罪。尸体是弱者最绝望的临终呐喊,也成为讼状最惨烈的修辞手段。对此,刑部以为,访民动不动就来京上访,甚至采取过激行为,应予制约,遂议请:“嗣后凡来京控诉案件,如有在刑部、都察院、步军统领各衙门自伤残者即行拿获,严追主使之人,与自伤未死之犯……分别治罪”。后奉旨,俟修例时纂入例册。(时光流转,全国人大代表、广西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刘庆宁在今年两会的“上访时喊口号、静坐、自残、自杀等应判刑”提案,与此异代同音、遥相呼应。)
要之,清代的息讼政策,并不能真正息讼。清人崔述指出,“自有生民以来,莫不有讼”,《左传》也说“饮食必有讼”。即使圣人尧舜都不能消灭诉讼,何况庸官俗吏。高调息讼,往往只是为强者张目,而使弱者更无力。不过,清代的息讼也有其合理一面。学者沈大明指出,清代自州县衙门到乡村民户之间的社会控制,并不全依赖于国家机器,地方士绅与社会共同体不仅是乡村礼俗和秩序控制的承担者,一定程度上也是法律控制的执行者。许多民间纠纷往往服从于宗族调解,而不一定非走司法诉讼的道路。黄宗智则指出,中国传统的社区调解制度具备其独特优点,息讼也有积极的社会秩序维护功能,而不必在争端中白白浪费诸多社会资源。沈、黄二人的发现,也跟文初最高法副院长张军的倡导暗合。
在我看来,今日重提息讼也好,重视调解也好,均只能作为辅助手段。源于西方的明确维护个人权利的对抗性、必分胜负的法律制度,才是主流。如果一味息讼,压制民众利益诉求,只会造成更大的社会冲突,乃至酿成群体纠纷。道光年间湖北崇阳的“钟九闹漕”即是一例,由讼师钟九领导的民间诉讼,最终却演变为大规模的民间暴动。
彼得·斯坦等著《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中说:“冲突实际上会产生许多能使人类生活更具实际意义的东西。没有冲突,社会就会呆滞,就会灭亡。关键在于社会必须对冲突进行适当的调节,使冲突不以将会毁掉整个社会的暴力方式而进行……必须先有社会秩序,才谈得上社会公平。社会秩序要靠一整套普遍性的法律规则来建立。而法律规则又需要整个社会系统地、正式地使用其力量加以维持”。所谓“和谐社会”,其实质或是“冲突社会”。如此看来,在当代中国,与其息讼,不如健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