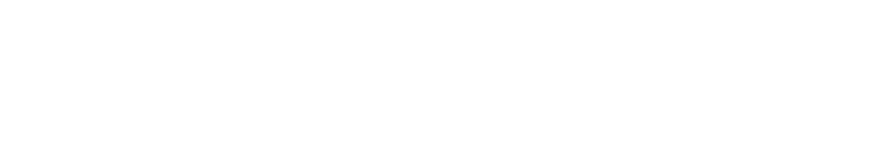吴伟民博士 在那遥远的地方……
| 发布时间: | 2009-05-08 16:49:27 | 点击次数: | 0 |
简述:
接到你已寄发七天的“遗书”,我仿佛失去了我再活下去的一千个理由,因为我已失去睡眠的安逸、饮食的愉悦和说话的气力。我跌跌撞撞,恍恍惚惚,不知是怎样购票上的特快列车的。
简介:
吴伟民博士 在那遥远的地方……
——沙石

引子
接到你已寄发七天的“遗书”,我仿佛失去了我再活下去的一千个理由,因为我已失去睡眠的安逸、饮食的愉悦和说话的气力。我跌跌撞撞,恍恍惚惚,不知是怎样购票上的特快列车的。
你在“遗书”中告诉我,你突然患了绝症,医生只能给你最后一个月的生命的期限。你忍不住给我写出最后一封信,请求我在你死后,把你的骨灰分成三份,一份洒在巴音布鲁克的草原上,一份洒在塔克拉玛干的沙漠上,还有一份洒在阿勒泰的喀纳斯湖中……
“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时。”我几乎是停止了呼吸,读了你临终时生命的话语。我只是一个“悲怆”吗?我只是一个“伤痛”吗?我只是一个“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参戚戚”吗?不!用这些来表述我的心境,那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不仅是学法律的同学,也不仅是做律师的同行。三年前的那个九月,我出差第一次到了新疆,与你相处整整十五天。我们谈律师地位,谈司法独立,谈国家法治,我们对现状是同样的遗憾,我们对未来是同样的理想。那会儿,你我都有一种蓦然回首相遇知音的感觉。分别时,我把全部感激的话语一起压在心底,只说了一句:“希望保持联系!”而你一句话也没说,默默地看着我,轻轻地“嗯”了一声。
特快列车载着我万分焦急的心情,没日没夜地西进——过了洛阳,过了西安,过了兰州,又进入了夜间运行。卧铺车厢的人们似乎都进入了梦乡。只有我,独自坐在窗口,虽然看不见草原风光,看不见“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虽然也听不见康定情歌,听不见“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可我觉得这样更好,我可以静静地与苍天黑夜对话,那是沙漠与绿洲的对话,是悲怆与美丽的对话,是生命与艺术的对话。
在我与苍天黑夜梦幻般的语境中,我忽地忆起那年九月,你我同游敦煌时,一位高僧告诉我,莫高窟藏经洞曾有一本流失的佛陀高徒传下的药书,上面记载着西域一个专治绝症的药方。还依稀记得高僧说,取月牙泉之水,胡杨树之根,再取一朵十年长成的天山雪莲花,熬汤服用,可以返老还童,起死回生。
顿时,我兴奋不已。我要谢谢佛,是佛激励着我的善心;我要谢谢僧人,僧人早有料定你我在世间的情缘;我要谢谢苍天黑夜,是苍天黑夜让我在幽冥中有了清醒的追忆——
-、你属于巴音布鲁克那绿色的草原吗
列车,在呼啸的寒风中西进,载着我无限的思念——我恨不能立即飞到了你的房间。
我知道,你说要把三分之一的骨灰撒在西域的巴音布鲁克大草原,一定是你特别留恋那原本是中国最大的天鹅自然保护区。那年九月,你陪同我到了那个仙境般的世界。我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我只觉得我走过的——东北的镜泊湖没有这儿辽阔,海南三亚的天涯海角没有这儿含蓄,钱塘江的海潮没有这儿宁静,桂林的漓江没有这儿明亮,就是黄山的云海日出也不及这儿平缓与舒展。遍布的湖沼、孤岛和浅水滩上,生活着几十种叫得出名和叫不出名的珍禽。成千上万的大天鹅,还有小天鹅,飞翔于蓝天绿草之间,嬉戏于湖沼碧水当中,恰如李可染、黄宾鸿他们画出的一幅幅绝妙的山水国画。
傍晚黄昏,更激动人心的画面出现了,那九曲十八湾的开都河在落日的逆光中,发出金灿灿的光泽,从我的身前弯曲着向太阳落下的地方飘去。如同敦煌壁画飞天身上的飘带,宛如维族姑娘歌舞时那柔美的舞姿。我想俄国的音乐大师柴可夫斯基一定来过这里,要不,怎么能够创作出举世惊叹的《天鹅湖》呢!
记得在巴音布鲁克天黑之后,我看没地方有酒店,于是担心没地方吃饭。你好像猜出了我的心思,一扬你那充满青春气息的漂亮秀发,笑着拉着我的手随便走进了一家毡房,就像走进你的家一样。你对毡房的主人说了几句我听不懂的蒙语,那主人家随即欢笑着切开哈蜜瓜,端出许多点心,随后还杀了一只全羊招待我们。尽管那时我吃不习惯羊肉,我还是悄悄问你需要花费多少钱,你靠近我说西域的少数民族非常喜欢客人走进他们的毡房,对汉族客人更是以心相待,并且不会收钱的。
呵,你就是这样深深地爱上了巴音布鲁克草原,爱上了草原上的“天鹅湖”,爱上了草原上的蒙族人,于是你要我把你的骨灰洒在那里。难道你要化作一只天鹅,演绎柴可夫斯基《天鹅湖》中的“天鹅之死”吗?你是不是觉得死亡也是一种美丽,是不种凄美呢?你或许有许多注脚,诸如凡•高在画出世界油画名作《向日葵》后选择了死亡,屈原在写出传世诗歌《离骚》后选择了死亡,还有普希金……
可是,我不能答应你,我还要听到你在喀什大巴扎民族市场购物说笑的声音,我还要听到你在库尔勒与维族小伙子弹唱的声音,我还要听到你在和田在哈蜜在达板城一个又一个法庭上辩论的声音。
我一定要再去敦煌的鸣沙山,不是再去莫高窟观赏那边接起来长达25公里的世界最大的壁画艺术画廊,我只是要再去鸣沙山下那无垠沙漠中那口月牙泉。那年九月,你依依不舍送我回内地,一直把我送到敦煌,你说那儿除了莫高窟之外,还有月牙泉。其实,我念中学时不知是读了作家柔石、还是艾青的作品,就知道有个月牙泉了。也就是那个少年时代,月牙泉就使我为之魂牵梦萦了,如同神往朱自清作品中的“荷塘月色”,神往周作人作品中的“乌蓬船”。
那是怎样的一口月牙泉啊!她落在无边的沙漠中而无一粒飞沙落入,宛如下凡仙女那明亮的眼;她落在千年的沙漠中而无一天的干涸,仿若飞天洗浴后悄悄照用的镜面。她在没有生命的地方报告着生命,她在死亡地带传承着永生的魂灵。佛会保佑你的:莫高窟的高僧说过,月牙泉的水,一定会滋润你年轻的清纯的又极有灵气的生命。
二、你属于塔克拉玛干那金色的沙漠吗
列车,在茫茫的雪夜中西进,载着我不尽的忧愁——我恨不能立即飞到了你的床前。
我知道,你说要把三分之一的骨灰撒在西域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一定是你特别留恋那地处塔里木盆地中心的中国第一大沙漠,那也是排列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之后的世界第六大沙漠。那年九月,你开着车子带我上了沙漠公路,那条公路从轮台到民丰全长522公里,穿越塔克拉玛干,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沙漠公路。
坐在你身边的副驾驶位上,我才发现塔克拉玛干是一个真正的“死亡之海”。茫茫沙海,荒无人烟,就是西域其他荒漠中偶尔出现的沙棘、盐桦和芨芨草也没有。你说沙漠空中温度达到40多度,地表温度达到60多度。你还说西部歌王王洛宾把鸡蛋放在沙地上,几分钟就熟了。歌王剥了蛋壳,一半自己吃了,一半递给来到他身边的台湾女作家三毛吃了。我当时多么地想,也那样剥着鸡蛋壳,我们一人吃一口,我有些后悔没带鸡蛋。
我还发现沙漠中那些裸露的高大沙丘,原本是随风流动的。在风中行车,我常常见到车前一个美丽的羽状形态的沙丘,在逆光中张扬着它特有的质感,车过后,回首一望,那沙丘就不见了。当时,我就有一种失落感,恨自己怕热没下车把金色的沙丘拍下来。你说,那沙丘或许又成了另一种美丽的状态呢!
路上,你把车停下,我们一起看着牵着骆驼的人走在干燥而又炎热的沙漠上。你在递给我矿泉水喝时说道:“塔克拉玛干”的正名不叫“死亡之海”,其准确的译名是“曾经有过的家园”。你说沙漠中的罗布泊本是一个巨大的湖泊,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楼兰就在罗布泊的岸边。而今,因为塔里木河上游的大面积的胡杨林遭到破坏,下游近500公里断流,著名的罗布泊消失了,古楼兰也就成了考古人、探险人心中的一个神话般的故事。
在你的声音你的眼神你的举手投足之中,我怎么看不出你对金黄沙漠、对行走在沙漠上的骆驼的热爱呢?你要我把你的骨灰撒在那里,难道你要化作丝绸之路上的罗布泊吗?你是不是觉得生命也是一种演变一种传奇,就像黑暗孕育着光明,光明又孕育着黑暗一样;就像残冬走向春的季节,而春天又慢慢地向冬日走去一般。要不,你就是要化作一个古楼兰的美丽传说,让我像科学家彭家木一样去寻求你的神奇,让我象探险家余纯顺一样去追踪你的神韵……
可是,我做不到啊,我还要读你精彩的辩词,读你美妙的散文,读你深邃的法学评论,这些都是你在那年九月答应过我的。
这回,我会在去了敦煌之后,去塔里木河上游的胡杨林保护区,我会根据佛的旨意,祈求管理人员让我取回几节胡杨树的根枝。那年九月,你告诉过我,胡杨木在干旱炎热的沙地里,甚至常年得不到一滴雨水,竟然能够生长一千年不死,死了一千年不倒,倒了一千年不朽。在你告诉我之前,我曾在中国美术馆看了成都一位摄影师在胡杨林拍摄的人体写真作品展,当时心中就升腾出一种死亡美学的辉煌。胡杨林呵,那不死的是对生命的诠释,那不倒的是对生命的破译,而那不腐的则是对生命的批注和评说。正因为胡杨林的存在,才有了塔里木河那西域人的母亲河。
我是很信佛的,莫高窟的僧人说过,胡杨林的根枝,一定能够救助你那亭亭玉立而又楚楚动人的身子,还有你那维护法律、扶持正义的思想和感情!
三、你属于阿勒泰那蓝色的喀纳斯湖吗?
列车,在微微的晨曦中西进,载着我深深的祝福——我恨不能立即飞到你的身边。
我知道,你说要把三分之一的骨灰撒在阿勒泰的喀纳斯湖。一定是你特别留恋那个被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称作变化莫测的“神秘湖”的。那年九月,你陪同我从乌鲁木齐出发,途经塞外江南的石河子,石油城克拉玛依,千里马的家园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然后到达金子的故乡阿勒泰。在那西域最北端的阿尔泰山山脉,就是闻名于世的“七十二条沟,沟沟产黄金”的地方。你说,“阿尔泰”在突厥语、蒙古语里都是“金子”的意思。在那儿,你把我扶上哈萨克游牧民族最喜欢的伊犁马,然后坐在我的面前,让我紧紧抱住你的腰身,你那随风飘逸的长发拂在我的脸上,给了我从未有过的温馨的感觉。你说你在一次调查取证中,公路被洪水冲毁了,是哈萨克的一位牧马人把你轻盈的身子抱上马背,翻山越岭百余里,送你到了目的地。你说你第一次与一个汉子身贴身在马背上贴得那么近那么紧,很不好意思。
那个夜晚,你却与我同睡在一个牧民的毡房里,至今想起我仍是怦然心跳。开始,我们在一家毡房席毯而坐,吃着牧民烤的羊肉串,还有西域少数民族最爱吃的烤馕。看着你那么放开那么自然那么津津有味地手抓羊肉吃着,我就想着你一个苏州姑娘当初怎么就毅然决然跑到新疆来做律师呢?看来你是与西域的水土有缘啊!后来我们就聊天,聊着聊着你就在我身边睡倒了,还扯来一床被子盖在身上。我忍不住问我睡哪儿呢?你说睡一个毡房呀!这儿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来客都是与主人同住一个毡房呀!哪有内地房屋还有楼上楼下、东房西房呢?你说少数民族很圣洁,他们相信真主,知道真主安拉时刻都在看着他们。就这样,我也睡倒了。可是,我不知是怎么了就是睡不着,看着天窗外面的星星,那是内地看不到的晶晶亮、亮晶晶的星星,那是我孩提时见过的星星——
第二天,你还陪我去看了座落在阿尔泰山森林中部的喀纳斯湖,那湖仿佛是夏日里一个清纯的少女卧睡在山间的绿草地上。湖的北面是紧挨着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奎屯山,耸立山巅的是终年白雪皑皑的友谊峰,那峰如同慈祥和蔼的圣诞老人。湖的四周山峦叠嶂,万木争辉;金黄的,橘红的,墨绿的各呈异彩,宛如节日里城市五光十色的灯,却又比灯光真实,比灯光自然。林间的空地上草甸如茵,山花鲜艳。你说真想在那儿安家在那儿住下来。我说好啊,我也建一座木屋,我们做邻居吧。你要和我拉勾,结果勾没拉,一起笑得都睡在比地毯还舒适的草地上。随后风静波平,湖水恰似一池翡翠,映照着蓝天白云,真是天水一色了。更奇妙的是湖水随着瞬间变化的天气而更换着不同的色调,幻变着奇异的风采。烟云缭绕时,雪峰群山在湖中的倩影似隐似现,我真不知道那是人间仙境,还是天上绝景。
下山的路上,你说可惜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没有走访西域,不知华夏大地还有阿尔泰山和喀纳斯湖,于是只能写道“西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这些都是历历在目,就象昨天发生一样。你又怎么能离得开我们同往的喀纳斯——富饶而神秘(蒙语语意)的湖光山色呢?你做不到的,你让我把你的骨灰撒在阿尔泰山,你是要永远与喀纳斯湖在一起,你是要永远在这湖边的白桦林中蝴蝶沟里还有芳草凄凄的草地上安家了。这样以来,或许你把死看得非常飘渺非常空灵非常自在又非常满足了。你不愿远离自然,你曾经说过,人本属于自然环境中的一个小小的生物,为什么要远离自然,甚至高高凌驾于其他动物植物之上呢?你说过回归自然而熟睡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应该是最最幸福的了。
可是,我还是接受不了啊,因为我活着,我怎么能与你在两个世界里生活呢?我不能看不见你的身影听不见你的声音,我一定要去天山山脉。无论从绵亘千里的天山哪个地方爬上去,无论上面再冷再高再滑再危险,我也要爬上去。我可以请一位药师带我爬山,我要遵从莫高窟高僧的指引,亲手采下雪线以上、生长十年以上的雪莲花。我是绝对相信佛的,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在那没有生命的雪山上,雪莲花竟然能在冰天雪地里生长,在零下几十度的气温中开花——那已不是一般的奇迹,那是对虚无的反证,那是对死亡的抗衡,那是一首生命的颂歌。
——我要把雪莲花慢慢地放入月牙泉的水中,轻轻地放在胡杨树的根上,煎出佛陀高徒传下的、莫高窟僧人所说的汤水,浇灌你无比美丽的生命之花。因为,我还要与你同骑一匹马——行走在帕米尔高原上,去寻觅“冰山上的来客”的足迹;我还要与你沐浴同一片月光——漫步在吐鲁番的葡萄沟里,去欣赏天下最好看的民族歌舞;我还要与你同往北京、上海、哈尔滨,共同去办理案件,维护弱者的正当权利,然后去音乐厅,去东方明珠,去太阳岛上;我还要……
呵,谢谢西进的列车。我终于看见了乌鲁木齐,我真的立即就能到了你的房间,到了你的床前,到了你的身边——
人物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