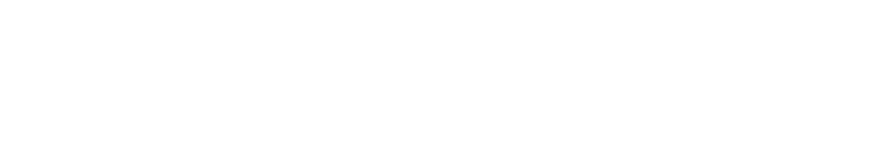吴伟民博士 拨动的是心灵的琴弦
| 发布时间: | 2012-10-27 09:00:35 | 点击次数: | 0 |
简述:
自己的校友们,接受过良好法律教育的法律人,却在这场践踏法治的运动中冲锋陷阵,你可以想见,作为一个对母校有着深厚情感的毕业生,内心是何等的不安和痛楚。
简介:
吴伟民博士 拨动的是心灵的琴弦
——贺卫方纵论时事、宗教、教育(“《律师文摘》沙龙之四”)
2012-10-05 16:15:14| 分类: 沙龙
提问:贺老师,我也姓贺,您对中国这么多学法律的学生,尤其边远学校的学生,对他们有什么寄语吗?
贺卫方:呵呵,谢谢本家啊!说到姓氏,容许我说几句题外话。其实中国许多同音字的姓氏都跟株连有关系。我们有这么多的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古代法律的残酷。遭遇满门抄斩的大祸,能够逃命的就改姓易名,有时就用谐音字,表示不是一个家族的了。像我的妈妈家姓曲,从前他们家姓鞠,后来远祖被逮捕了,要杀头,赶快逃命,自己很委屈,就改姓曲了。中国姓曲的人差不多都是这一支山东人。他们姓氏本身就记录了悲苦家族的历史,到现在还有一个风俗就是生前姓曲,死后姓鞠,死后把姓改回去,所以墓碑上还是刻着鞠某某之墓。
你的问题涉及到这个法律教育。学法律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在校学生,我跟在座的周大伟教授是大学同学,我们那一年全国一共只有700多个法学专业的学生,但是现在好像光学法律的在校学生就有40万以上了。法律当然是一种特别实用的学科,这些年我不断地劝我周边的朋友的孩子说,干脆本科阶段学学历史、人文、外语、考古,多好的专业,然后到研究生阶段喜欢法律的再学法律,但是这类劝说很少成功,大家都愿意学法律。孩子多多少少有点依赖父辈,父辈是在法律界,比方说有人的父亲是法院的院长,觉得自己学法律肯定在资源方面非常丰富,前人栽树,后人可以乘凉。我觉得法律人太多了会导致学历贬值。当代著名作家杨绛教授的父亲杨荫杭是学法律的,他观察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学法律专业,叫“学法之人,如过江之鲫”,终导致“法律文凭贱如粪土”。你们还记得话剧《茶馆》里面有一个二流子,他仿佛很多年不见了,突然在茶馆里出现,常四爷就问他这些年到哪去了?回答是上法政学堂了。学法律去了。所以现在比较麻烦的,随着太多的法律人,整个教育的品质确实是特别容易下降,在这个时候,我想对于学法律的人说,如何去真正地保持一份特别强有力的上进心和培养对法学本身的热爱,去树立法学这门专业本身的尊严,这一点特别重要。
不仅如此,在今天这样的各种思潮纷至沓来的时候,培养自己的鉴别和判断能力也非常重要。我们发现历史上有些人特别容易迷惑,比如说鲁迅,虽然是很伟大的文学家,但是鲁迅对政治问题的判断方面经常是有问题的,例如会突然觉得苏联是一条我们应该追求的道路,这就是迷惑。胡适到莫斯科的时候也突然有一瞬间的迷惑,但是又旅行到了西欧时他才恢复了理性的判断力。我发现倒是徐志摩这个人一点都不迷惑。胡适在一封信里面表达了对苏联这种模式的好感,认为在那里有一种向上的精神,有一种对教育的重视等等,徐志摩看到这个东西就特别的着急,明确地认为这条道路走不通,胡适这样的人绝对不应该再犯这种迷惑。当然罗曼罗兰这些人也都犯过迷糊。
现在法学界也有不少人,像新左派,听起来特别有煽动力,比方说你天天说法律是什么,他就说其实法律就是最肮脏交易的结果;你说这种法律是需要统一的时候,他告诉你法律从来就不是统一;你说这个法律稳定,他说现在法律从来就没有稳定。早晨法官跟太太吵了一架,判刑就多了五年,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后现代解构主义有时候对年轻学子特别有吸引力,对于年轻孩子来说,你能够把权威给推翻,给砸烂,证明你是多么伟大。有些老师会跟你说:书上一切都是错的,回去烧了,听我的,就开始讲,把主流知识全部解构掉。哎呀,这是多么卓尔不群!做教师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你不能标新立异,人云亦云,你所说的是一种常识,你论证常识,这样的话就会觉得你没有什么创造力,这个创造性就往往来自于我们对这个说不,对那个说不,西方人这条制度根本不适合中国,然后说出一番自己的论证。在我们法学界也有一些年轻的学者,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很远,甚至倡言某种国家主义的观念。我觉得虽然说在18-19岁的时候,人容易迷惑,思想跳来跳去。如何有广阔的胸怀接纳各种各样知识和思想的同时又能够保持一份法律人应有的对自由的真诚热爱,一种对真理的追求,这是需要特别重视的。谢谢!
提问:想请问您怎么看现在中国存在很多的家庭教会?有一些学者可能觉得家庭教会意义很重大,作为我个人来讲,我也读《圣经》,我对宗教的态度很开放,但是走在街上就有人跟我传教,我觉得很烦,因为他第一天跟你交朋友,第二天就说你要去受洗,请问您怎么看?
贺卫方:这个事情我的经验倒是很少。也许家庭教会有许多事情让你感觉到不是特别的喜欢或者不是特别的正常,往往是因为他没有得到在地上的健康成长的环境,往往政府打压的结果是使得他们不得不用一种隐秘的方式传教,或者有时候让你觉得不是特别的正当。真正从教义方面的理解,你会发现一些严重的偏差。我认为我们应该跟梵蒂冈建交,无论哪一个国家传教士到中国来,都可以坦坦荡荡地传教。我认为我们应该恢复以前教会办的那些大学,比如说东吴、辅仁,辅仁是法国人办的学校,比如说齐鲁,比如说燕京。当然,燕京恢复有些麻烦,北大要被赶出去,这个事情怎么办?当然是可以另外商量,可以把中南海那个大院腾出来给燕京大学,叫中央机关在一个现代建筑里办公,北大还保留着原来的地方。中南海那样的地方办一所大学其实挺好的,那个院好,我觉得作为对燕京大学被停办60年了,1952年被停办,作为60年一甲子的补偿,让燕京大学在中南海里面成立自己的大学。但是中南海最好把院墙拆了,然后可以通车,让市民可以去燕京大学,市民可以去那边游览参观。
如果有教会学校,然后成立很好的神学院,这是比较正常宗教教育的一种状态,要培养每个人那种平和的心态,然后使得这个国家宗教事业能够得到更好的发育发展,各地教堂应该更自由地修建。我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我有一次夜晚降落首尔机场,晚上降落之前看首尔上空,十字架真多,都是教堂,都亮着。儒家没有宗教式的神学体系,所以很难真正成为信仰,如果汉民族许多人信仰基督教,而基督教经过马丁路德、经过加尔文的改教以后,有很多观念更加的开放,比方说现在通婚,如果你跟穆斯林通婚的话,宗教方面的禁忌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你要和基督徒结婚,基本上没有多少的禁忌,所以更加的理性和开放,我们政府如果明智的话,就应该真正的落实《宪法》中所规定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不能再对宗教自由进行任何的打压,越打压,变态的事情就会越多。谢谢。
张思之:我有问题,请问贺老师,结合某位曾经在北大任教的经济学家最近的指控,你觉得北大是在堕落吗?
贺卫方:我首先要说梦桃源是非常正常的餐馆,一家中档餐馆,但是在我看来价格稍微偏高,如果我个人请客的话,我觉得稍微高了一点,所以我请客愿意在附近价位更低一点的餐馆请朋友吃饭。
北大到底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的,老爷子您可能比我看得更清楚一些。我觉得中国的大学受到同样的体制约束,谁也没有办法逃脱这个整体控制。北京大学有党委,你可以看到北京大学的官方网站是何等的越来越党化,天天网上都在说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学习党的什么文件,本校也会把自己的党代表大会作为大事,开会之后照样要全校学习,贯彻落实相关决议。党委书记和党的官员们变得越来越活跃,越来越主导,官场那一套东西越来越渗透到学界和大学管理的各个环节。
你们看北大内部的电视,北大电视台就是小型版的CCTV……
张思之:为什么不可以抵制?
贺卫方:我观察还是有不少学者在尽可能地坚守,也经常有在内部的批评。比方说有一次元旦,学校举办“中青年教师座谈会”,我发言时非常明确的说,我们必须要在北京大学管理校政各个环节方面全方位的恢复蔡元培校长、胡适校长所开创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样的精神。(张思之先生插话:“哪怕是马寅初也行啊!”)记得现场对此的反响是非常正面的。但是现在的大环境一直在恶化,大学的独立性日渐丧失,堕落的过程似乎是无休止,我自己看不到多少希望。在教育领域当中,还应该关注资源的分配是否公正,北大在北京地区招生、北京市的招生比例已经高到不合理的程度。我有时候给学生们上课,我问你们有多少人是北京籍呢?往往到了1/3,1/3的人是北京的考生。这对于户籍在北京的人当然觉得更好,但是这不公平,这是一所全国性的国立大学,这是面向全国招生的大学。所以当年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说中国政法大学应该严格依据各个省的人口比例来分配招生的名额,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有人研究北京大学招收的学生出生农村的比例,30多年的时间滑落到令人震惊的程度,而且现在官员的孩子也超过了专业人士的孩子,成为第一个高的人群。我觉得这是招生和整个教育的公正问题,它在固化社会的阶层结构。其实我觉得许多人批评北大,北大真的应该非常认真地对待,那是爱之深责之切,大家对北大是有这样的希望,等到大家都不说了那就是太麻烦了。所以北大应当作出应有的检讨,作出决策中的改善,慢慢地去改进。虽然我们很难做到真正的独立,真正独立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我们可以在减少我们堕落方面作出一些努力。
王锦明:现在我们的上层知识分子当中,您觉得在“胆”和“识”当中更缺哪一样?
贺卫方:这有点像是“知”与“行”之间的问题一样不大好回答。“胆”和“识”之间如何取舍?当我们遭遇到某些不公正的事情,比方说贵州这种邪恶审判出现的时候,像重庆的所谓“唱红打黑”发生的时候,我们知识界如果有更多的人站出来说不,甚至有组织化地表达愤怒,比方说李庄事件出现以后,我们律师协会为什么不能够以律师协会的名义发表申明,对这样打压律师剥夺律师独立辩护权的做法作出谴责呢?如果中国法学会刑法学会或刑事诉讼法学会对一些公然践踏法治准则的审判作出谴责,那情况就会非常不一样。这当然需要勇气,也需要在学术界树立一种为正义而抗争的精神。这离不开学者以及学术机构必要的独立性。有很多人其实从“知”的角度说完全看得出来是非,他们私下里往往说我也是这种观点,跟你一样,只是我们不方便说,反正是你说了我们的心里话。如果大多数人是这样的心态,就必然导致邪恶的东西日益猖獗。邪恶不断重演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种勇气站出来齐声怒吼:“不能够这样做!”
“识”问题,我在网上看到一般的匿名网友评论,你可以发现包括对文革的评价,对毛的评价,绝大多数人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个别人也许属于某种可以称之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群”患者,那就是曾经受过专制虐待,却转而喜欢甚至崇拜专制。我不大相信黄宗智教授会有这种问题。他是一个美国历史学家,但是他的文章,对“重庆模式”简直让人肉麻的歌颂,说薄熙来把资本主义的优势和社会主义的优势结合在一起,把毛泽东时代对精神价值的弘扬和邓小平时代对经济的推进结合在一起,重庆模式是这么伟大!我觉得这样的人难道说他们真的是糊涂吗?在我看来其实他们不糊涂,他们也许是受到学术之外的因素的影响。
总体来说我觉得“胆”非常的重要,如果说“识”是一个人明辩是非的能力,那这个东西还是需要我们去勇敢地表达,不受真理之外的因素的影响。我特别喜欢希腊伟大政治家伯里克利的话,他强调没有自由就没有幸福,没有勇敢就没有自由。当然,你首先要认识到自由跟幸福之间的关系,有些人会觉得没有自由我们也很幸福,有许多人说毛泽东时代多幸福,说什么对于贪官污吏,毛泽东一打一个准,一打一个狠,那多好!他们不知道在没有自由的情况下,这种运动带来了对人权的多么严重的侵犯。所以,你首先要有足够的学养和悟性去认识到自由是幸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那部分,然后你还要有足够的勇敢和勇气去捍卫自己的自由。
提问:贺老师你好,我是中国政法大学一名学生,我们学校有很多跟法律有关的学生社团,我本人就是准律师协会的一名会员。我们平时也有做一些普法、法律援助的活动,但是总感觉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请问你们对我们这些社团有什么建议呢?
贺卫方:你们的准律师协会非常的有名,张思之先生多次去你们协会做过演讲,他好像也是你们的顾问吧。其实我对于学生社团的经验几乎是零,因为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没有像样的学术社团。你们准律师协会这样老牌的学生社团,会有许多法律援助之外的活动,包括组织一些讲座,让学生能够接触到这个国家一流的律师,能够让他们在读书的时候能够得到自己职业前辈的某些感染或者是理解法律职业的特色。所谓法律援助,说老实话,我当然希望你们做,但是一个学生最好不要在这方面投入太多。倒不是说对这些苦难的人不应该去帮助,我是说读大学过分地接触这些社会苦难,人就会心灰意冷。所以柏拉图在《理想国》里面说培养统治者的过程,其实应该让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不要太接触那些黑暗肮脏的东西,因为这也是自己心灵受到创伤和污染的过程。我希望你们能够把自己的这类工作控制在一定的比例。固然你们应当关注社会,但是比在本科阶段关注社会更重要的增加自己的学养。我特别赞成学生们在本科阶段能够好好的读圣贤书,因为大学肩负着非常重要的使命,我们要传承人类伟大的文化。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中国先秦诸子的文化,现在同学们应该多去读这些,一页一页、一行一行地认真研读这种经典著作。你怀着一腔救世的心态,就容易使自己还没有非常坚实的知识基础就去介入社会事务。所以有些人判断力老是出问题,可能跟学养方面的匮乏有密切的关系。另外,学生社团的组织活动中非常重要的是让它们本身成为一个训练民主的过程。大学学生社团应当有一种规则,让大家看看我们怎么做一个决策,怎么在决策过程中间真正让每个人都有参与的权利,如何去选举,如何将决策落到实处,这可能是民主的培训过程。
提问:我前两天看您写的东西,让我觉得感慨。去年你发表公开信,现在才一年多一点,重庆发生了这样令人震惊的戏剧性变化。我想问问贺老师,当时在那个环境下,写这个公开信是怎样的心情呢?
贺卫方:我是西南政法的本科毕业,重庆恰好是西南政法所在地。我个人是78级,西南政法复办以后第一届学生,在重庆政法一线上工作的许多人都是西南政法的毕业生,基本上都算是我的师弟师妹,像那两位在“打黑”中表现活跃的女检察官就是西南政法的毕业生,李庄案一审的审判长也是西南政法大学的硕士毕业生。还有法学界的一些学者们,也大多是西南政法大学的教师,他们居然也发表文章,为重庆的这种作为站台打气。自己的校友们,接受过良好法律教育的法律人,却在这场践踏法治的运动中冲锋陷阵,你可以想见,作为一个对母校有着深厚情感的毕业生,内心是何等的不安和痛楚。
不仅如此,在那段时间里,还有些重庆的师妹师弟们给我打电话,小心翼翼地给我打电话,或者是在外地我们遇到了,他们会私下跟我说一些重庆的事情,有很多人说着说着就哭,感叹地说重庆怎么能变成这样恐怖的城市?怎么会一点点的遏制性因素都没有?我们看到前天对王立军的审判,你会发现,这个国家如果政治局委员想做什么事情,无论是杀人还是把企业家的财产没收,还是把官员说撤就撤,把老百姓说抓就抓,完全没有约束。比如,王立军说:因为他向主要领导汇报,主要领导就怒斥他,打了他一个耳光。接着过了两天,手下的人被调查,谁能够下令调查?王立军已经边缘化,下令调查肯定不是王立军嘛!那是谁在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想想这个体制,真是一点约束都没有。所以这种情况下让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是否应该把过去零零碎碎在博客或者是微博上面不是特别系统和正式的批评。除了“打黑”变成“黑打”之外,也包括对于“唱红歌”之类,写成一篇文章。我对于“唱红”也专门写过文章,对于那些“红歌”中所传递和不断再生产的意识形态进行过分析和批评。那篇文章是2011年6月份发表的。
促使我写那封公开信的另一个因素是,在2009到11年期间,越来越多的政界高层人物纷纷到重庆,他们大多要参观“打黑除恶展览”,至少根据重庆的媒体的报道,他们都对于那里的“打黑唱红”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让我忧虑。也许重庆所作所为的意义已经不限于西南一隅,大有代表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趋势。我觉得事情已经变得非常紧迫,怎样才能够让人们认清所谓“重庆模式”开历史倒车的政治意蕴?虽然自己没有太大的号召力,也没有任何的权力,但是作为一个学者,还有一种责任,尤其是西南政法毕业生和一个法学教授的一种责任。所以在压抑了一年左右时间之后,终于把这一年积下来这股郁闷不平之气变成了一封四千字的公开信。当然这样的东西首先来讲不能有任何的调侃,要特别真诚,与此同时要特别的理性。过去我读张思之先生的文章特别受感染和影响,你分析问题十分注意不情绪化,就是把事实和证据一条一条摆出来。当然,其中也有我的情感,还有对死亡的思考。末尾,我引用索福克勒斯的诗,人生年轻的时候大权在握的时候如此猖狂,但是人总有这一天,你会面对衰老病死。而且那些被判死刑的人们只不过比我们一般早走一些时日。无论是枪决还是砍头,都会留下可怕的创伤,但是我说那是一种无须再治疗的创伤。我也想到,这个公开信发出来会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因为重庆“黑打除恶”中的所作所为实在是一种红色恐怖。一些朋友也劝我要注意安全,注意会发生人身危险——后来揭露出来事实真的可以证明他们的确是视人命如草芥的。不过,也不要想那么多了,发了就发了,担心也没有多少用。因为这个缘故,你可以理解为什么今年2月份王捕头潜馆事件发生后我会那么开心,那么高兴,我当时在日本东京,好几个朋友跟我联系,晚上喝酒啊!现在,谷开来已经被判死缓,前天王立军在成都受审,许多人说薄熙来会不会切割出来,只是受到党纪处分。我说绝对不可能,这既是我的判断也是我的期望,你怎么说切割就会不受刑事追究,我预料他一定会受到刑事审判,因为他与前面的几个案件都脱不开干系,甚至此公很可能就是其中的主犯。谢谢!
提问:贺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最近有一个电影叫做《人山人海》,是第二个获得威尼斯奖的作品,你怎么看待这种中国独立电影,他是用一个电影艺术的方式包装了法律事业。
贺卫方:我没有看,等回去查一查。最近有不少纪录片制作人甚至艺术片的制作人越来越关注法律题材,我有机会参与到艺术家独立论坛这样一些活动中间,去接触一些艺术家,包括电影艺术,油画艺术,还有行为艺术、我觉得现在艺术界的人对法律的关注,让我真的感觉到特别的欣慰,他们做艺术家首先特别关心表达自由,尤其是现在这种行为艺术往往都带有政治批判的色彩。如果我们的政治制度不是宽容的对待他们,他们就没有办法生存。我想从历史上电影艺术对法律有些方面的表达往往会起到比好多篇法学论文重要得多的作用。比方说涉及死刑的电影,往往能够在一个国家中促成全民对死刑的反思。我这几年又在鼓吹废除死刑,我多么希望电影界友人能够拍一部电影,展现一个死刑犯临刑前的恐惧。如果能够把这样的恐惧表达出来,那对于我们反思死刑以及人道主义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希望回去看看你所说的《人山人海》,但是现在没有办法去发表评论。另外,你提到这部片子在国际上获奖,我想国际社会的支持也特别重要,尽管国际社会往往一支持,国内不可能上演了。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去努力改变国内法律方面对于艺术自由压制的状况。
谢谢大家!
——贺卫方纵论时事、宗教、教育(“《律师文摘》沙龙之四”)
2012-10-05 16:15:14| 分类: 沙龙
提问:贺老师,我也姓贺,您对中国这么多学法律的学生,尤其边远学校的学生,对他们有什么寄语吗?
贺卫方:呵呵,谢谢本家啊!说到姓氏,容许我说几句题外话。其实中国许多同音字的姓氏都跟株连有关系。我们有这么多的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古代法律的残酷。遭遇满门抄斩的大祸,能够逃命的就改姓易名,有时就用谐音字,表示不是一个家族的了。像我的妈妈家姓曲,从前他们家姓鞠,后来远祖被逮捕了,要杀头,赶快逃命,自己很委屈,就改姓曲了。中国姓曲的人差不多都是这一支山东人。他们姓氏本身就记录了悲苦家族的历史,到现在还有一个风俗就是生前姓曲,死后姓鞠,死后把姓改回去,所以墓碑上还是刻着鞠某某之墓。
你的问题涉及到这个法律教育。学法律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在校学生,我跟在座的周大伟教授是大学同学,我们那一年全国一共只有700多个法学专业的学生,但是现在好像光学法律的在校学生就有40万以上了。法律当然是一种特别实用的学科,这些年我不断地劝我周边的朋友的孩子说,干脆本科阶段学学历史、人文、外语、考古,多好的专业,然后到研究生阶段喜欢法律的再学法律,但是这类劝说很少成功,大家都愿意学法律。孩子多多少少有点依赖父辈,父辈是在法律界,比方说有人的父亲是法院的院长,觉得自己学法律肯定在资源方面非常丰富,前人栽树,后人可以乘凉。我觉得法律人太多了会导致学历贬值。当代著名作家杨绛教授的父亲杨荫杭是学法律的,他观察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学法律专业,叫“学法之人,如过江之鲫”,终导致“法律文凭贱如粪土”。你们还记得话剧《茶馆》里面有一个二流子,他仿佛很多年不见了,突然在茶馆里出现,常四爷就问他这些年到哪去了?回答是上法政学堂了。学法律去了。所以现在比较麻烦的,随着太多的法律人,整个教育的品质确实是特别容易下降,在这个时候,我想对于学法律的人说,如何去真正地保持一份特别强有力的上进心和培养对法学本身的热爱,去树立法学这门专业本身的尊严,这一点特别重要。
不仅如此,在今天这样的各种思潮纷至沓来的时候,培养自己的鉴别和判断能力也非常重要。我们发现历史上有些人特别容易迷惑,比如说鲁迅,虽然是很伟大的文学家,但是鲁迅对政治问题的判断方面经常是有问题的,例如会突然觉得苏联是一条我们应该追求的道路,这就是迷惑。胡适到莫斯科的时候也突然有一瞬间的迷惑,但是又旅行到了西欧时他才恢复了理性的判断力。我发现倒是徐志摩这个人一点都不迷惑。胡适在一封信里面表达了对苏联这种模式的好感,认为在那里有一种向上的精神,有一种对教育的重视等等,徐志摩看到这个东西就特别的着急,明确地认为这条道路走不通,胡适这样的人绝对不应该再犯这种迷惑。当然罗曼罗兰这些人也都犯过迷糊。
现在法学界也有不少人,像新左派,听起来特别有煽动力,比方说你天天说法律是什么,他就说其实法律就是最肮脏交易的结果;你说这种法律是需要统一的时候,他告诉你法律从来就不是统一;你说这个法律稳定,他说现在法律从来就没有稳定。早晨法官跟太太吵了一架,判刑就多了五年,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后现代解构主义有时候对年轻学子特别有吸引力,对于年轻孩子来说,你能够把权威给推翻,给砸烂,证明你是多么伟大。有些老师会跟你说:书上一切都是错的,回去烧了,听我的,就开始讲,把主流知识全部解构掉。哎呀,这是多么卓尔不群!做教师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你不能标新立异,人云亦云,你所说的是一种常识,你论证常识,这样的话就会觉得你没有什么创造力,这个创造性就往往来自于我们对这个说不,对那个说不,西方人这条制度根本不适合中国,然后说出一番自己的论证。在我们法学界也有一些年轻的学者,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很远,甚至倡言某种国家主义的观念。我觉得虽然说在18-19岁的时候,人容易迷惑,思想跳来跳去。如何有广阔的胸怀接纳各种各样知识和思想的同时又能够保持一份法律人应有的对自由的真诚热爱,一种对真理的追求,这是需要特别重视的。谢谢!
提问:想请问您怎么看现在中国存在很多的家庭教会?有一些学者可能觉得家庭教会意义很重大,作为我个人来讲,我也读《圣经》,我对宗教的态度很开放,但是走在街上就有人跟我传教,我觉得很烦,因为他第一天跟你交朋友,第二天就说你要去受洗,请问您怎么看?
贺卫方:这个事情我的经验倒是很少。也许家庭教会有许多事情让你感觉到不是特别的喜欢或者不是特别的正常,往往是因为他没有得到在地上的健康成长的环境,往往政府打压的结果是使得他们不得不用一种隐秘的方式传教,或者有时候让你觉得不是特别的正当。真正从教义方面的理解,你会发现一些严重的偏差。我认为我们应该跟梵蒂冈建交,无论哪一个国家传教士到中国来,都可以坦坦荡荡地传教。我认为我们应该恢复以前教会办的那些大学,比如说东吴、辅仁,辅仁是法国人办的学校,比如说齐鲁,比如说燕京。当然,燕京恢复有些麻烦,北大要被赶出去,这个事情怎么办?当然是可以另外商量,可以把中南海那个大院腾出来给燕京大学,叫中央机关在一个现代建筑里办公,北大还保留着原来的地方。中南海那样的地方办一所大学其实挺好的,那个院好,我觉得作为对燕京大学被停办60年了,1952年被停办,作为60年一甲子的补偿,让燕京大学在中南海里面成立自己的大学。但是中南海最好把院墙拆了,然后可以通车,让市民可以去燕京大学,市民可以去那边游览参观。
如果有教会学校,然后成立很好的神学院,这是比较正常宗教教育的一种状态,要培养每个人那种平和的心态,然后使得这个国家宗教事业能够得到更好的发育发展,各地教堂应该更自由地修建。我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我有一次夜晚降落首尔机场,晚上降落之前看首尔上空,十字架真多,都是教堂,都亮着。儒家没有宗教式的神学体系,所以很难真正成为信仰,如果汉民族许多人信仰基督教,而基督教经过马丁路德、经过加尔文的改教以后,有很多观念更加的开放,比方说现在通婚,如果你跟穆斯林通婚的话,宗教方面的禁忌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你要和基督徒结婚,基本上没有多少的禁忌,所以更加的理性和开放,我们政府如果明智的话,就应该真正的落实《宪法》中所规定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不能再对宗教自由进行任何的打压,越打压,变态的事情就会越多。谢谢。
张思之:我有问题,请问贺老师,结合某位曾经在北大任教的经济学家最近的指控,你觉得北大是在堕落吗?
贺卫方:我首先要说梦桃源是非常正常的餐馆,一家中档餐馆,但是在我看来价格稍微偏高,如果我个人请客的话,我觉得稍微高了一点,所以我请客愿意在附近价位更低一点的餐馆请朋友吃饭。
北大到底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的,老爷子您可能比我看得更清楚一些。我觉得中国的大学受到同样的体制约束,谁也没有办法逃脱这个整体控制。北京大学有党委,你可以看到北京大学的官方网站是何等的越来越党化,天天网上都在说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学习党的什么文件,本校也会把自己的党代表大会作为大事,开会之后照样要全校学习,贯彻落实相关决议。党委书记和党的官员们变得越来越活跃,越来越主导,官场那一套东西越来越渗透到学界和大学管理的各个环节。
你们看北大内部的电视,北大电视台就是小型版的CCTV……
张思之:为什么不可以抵制?
贺卫方:我观察还是有不少学者在尽可能地坚守,也经常有在内部的批评。比方说有一次元旦,学校举办“中青年教师座谈会”,我发言时非常明确的说,我们必须要在北京大学管理校政各个环节方面全方位的恢复蔡元培校长、胡适校长所开创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样的精神。(张思之先生插话:“哪怕是马寅初也行啊!”)记得现场对此的反响是非常正面的。但是现在的大环境一直在恶化,大学的独立性日渐丧失,堕落的过程似乎是无休止,我自己看不到多少希望。在教育领域当中,还应该关注资源的分配是否公正,北大在北京地区招生、北京市的招生比例已经高到不合理的程度。我有时候给学生们上课,我问你们有多少人是北京籍呢?往往到了1/3,1/3的人是北京的考生。这对于户籍在北京的人当然觉得更好,但是这不公平,这是一所全国性的国立大学,这是面向全国招生的大学。所以当年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说中国政法大学应该严格依据各个省的人口比例来分配招生的名额,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有人研究北京大学招收的学生出生农村的比例,30多年的时间滑落到令人震惊的程度,而且现在官员的孩子也超过了专业人士的孩子,成为第一个高的人群。我觉得这是招生和整个教育的公正问题,它在固化社会的阶层结构。其实我觉得许多人批评北大,北大真的应该非常认真地对待,那是爱之深责之切,大家对北大是有这样的希望,等到大家都不说了那就是太麻烦了。所以北大应当作出应有的检讨,作出决策中的改善,慢慢地去改进。虽然我们很难做到真正的独立,真正独立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我们可以在减少我们堕落方面作出一些努力。
王锦明:现在我们的上层知识分子当中,您觉得在“胆”和“识”当中更缺哪一样?
贺卫方:这有点像是“知”与“行”之间的问题一样不大好回答。“胆”和“识”之间如何取舍?当我们遭遇到某些不公正的事情,比方说贵州这种邪恶审判出现的时候,像重庆的所谓“唱红打黑”发生的时候,我们知识界如果有更多的人站出来说不,甚至有组织化地表达愤怒,比方说李庄事件出现以后,我们律师协会为什么不能够以律师协会的名义发表申明,对这样打压律师剥夺律师独立辩护权的做法作出谴责呢?如果中国法学会刑法学会或刑事诉讼法学会对一些公然践踏法治准则的审判作出谴责,那情况就会非常不一样。这当然需要勇气,也需要在学术界树立一种为正义而抗争的精神。这离不开学者以及学术机构必要的独立性。有很多人其实从“知”的角度说完全看得出来是非,他们私下里往往说我也是这种观点,跟你一样,只是我们不方便说,反正是你说了我们的心里话。如果大多数人是这样的心态,就必然导致邪恶的东西日益猖獗。邪恶不断重演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种勇气站出来齐声怒吼:“不能够这样做!”
“识”问题,我在网上看到一般的匿名网友评论,你可以发现包括对文革的评价,对毛的评价,绝大多数人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个别人也许属于某种可以称之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群”患者,那就是曾经受过专制虐待,却转而喜欢甚至崇拜专制。我不大相信黄宗智教授会有这种问题。他是一个美国历史学家,但是他的文章,对“重庆模式”简直让人肉麻的歌颂,说薄熙来把资本主义的优势和社会主义的优势结合在一起,把毛泽东时代对精神价值的弘扬和邓小平时代对经济的推进结合在一起,重庆模式是这么伟大!我觉得这样的人难道说他们真的是糊涂吗?在我看来其实他们不糊涂,他们也许是受到学术之外的因素的影响。
总体来说我觉得“胆”非常的重要,如果说“识”是一个人明辩是非的能力,那这个东西还是需要我们去勇敢地表达,不受真理之外的因素的影响。我特别喜欢希腊伟大政治家伯里克利的话,他强调没有自由就没有幸福,没有勇敢就没有自由。当然,你首先要认识到自由跟幸福之间的关系,有些人会觉得没有自由我们也很幸福,有许多人说毛泽东时代多幸福,说什么对于贪官污吏,毛泽东一打一个准,一打一个狠,那多好!他们不知道在没有自由的情况下,这种运动带来了对人权的多么严重的侵犯。所以,你首先要有足够的学养和悟性去认识到自由是幸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那部分,然后你还要有足够的勇敢和勇气去捍卫自己的自由。
提问:贺老师你好,我是中国政法大学一名学生,我们学校有很多跟法律有关的学生社团,我本人就是准律师协会的一名会员。我们平时也有做一些普法、法律援助的活动,但是总感觉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请问你们对我们这些社团有什么建议呢?
贺卫方:你们的准律师协会非常的有名,张思之先生多次去你们协会做过演讲,他好像也是你们的顾问吧。其实我对于学生社团的经验几乎是零,因为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没有像样的学术社团。你们准律师协会这样老牌的学生社团,会有许多法律援助之外的活动,包括组织一些讲座,让学生能够接触到这个国家一流的律师,能够让他们在读书的时候能够得到自己职业前辈的某些感染或者是理解法律职业的特色。所谓法律援助,说老实话,我当然希望你们做,但是一个学生最好不要在这方面投入太多。倒不是说对这些苦难的人不应该去帮助,我是说读大学过分地接触这些社会苦难,人就会心灰意冷。所以柏拉图在《理想国》里面说培养统治者的过程,其实应该让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不要太接触那些黑暗肮脏的东西,因为这也是自己心灵受到创伤和污染的过程。我希望你们能够把自己的这类工作控制在一定的比例。固然你们应当关注社会,但是比在本科阶段关注社会更重要的增加自己的学养。我特别赞成学生们在本科阶段能够好好的读圣贤书,因为大学肩负着非常重要的使命,我们要传承人类伟大的文化。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中国先秦诸子的文化,现在同学们应该多去读这些,一页一页、一行一行地认真研读这种经典著作。你怀着一腔救世的心态,就容易使自己还没有非常坚实的知识基础就去介入社会事务。所以有些人判断力老是出问题,可能跟学养方面的匮乏有密切的关系。另外,学生社团的组织活动中非常重要的是让它们本身成为一个训练民主的过程。大学学生社团应当有一种规则,让大家看看我们怎么做一个决策,怎么在决策过程中间真正让每个人都有参与的权利,如何去选举,如何将决策落到实处,这可能是民主的培训过程。
提问:我前两天看您写的东西,让我觉得感慨。去年你发表公开信,现在才一年多一点,重庆发生了这样令人震惊的戏剧性变化。我想问问贺老师,当时在那个环境下,写这个公开信是怎样的心情呢?
贺卫方:我是西南政法的本科毕业,重庆恰好是西南政法所在地。我个人是78级,西南政法复办以后第一届学生,在重庆政法一线上工作的许多人都是西南政法的毕业生,基本上都算是我的师弟师妹,像那两位在“打黑”中表现活跃的女检察官就是西南政法的毕业生,李庄案一审的审判长也是西南政法大学的硕士毕业生。还有法学界的一些学者们,也大多是西南政法大学的教师,他们居然也发表文章,为重庆的这种作为站台打气。自己的校友们,接受过良好法律教育的法律人,却在这场践踏法治的运动中冲锋陷阵,你可以想见,作为一个对母校有着深厚情感的毕业生,内心是何等的不安和痛楚。
不仅如此,在那段时间里,还有些重庆的师妹师弟们给我打电话,小心翼翼地给我打电话,或者是在外地我们遇到了,他们会私下跟我说一些重庆的事情,有很多人说着说着就哭,感叹地说重庆怎么能变成这样恐怖的城市?怎么会一点点的遏制性因素都没有?我们看到前天对王立军的审判,你会发现,这个国家如果政治局委员想做什么事情,无论是杀人还是把企业家的财产没收,还是把官员说撤就撤,把老百姓说抓就抓,完全没有约束。比如,王立军说:因为他向主要领导汇报,主要领导就怒斥他,打了他一个耳光。接着过了两天,手下的人被调查,谁能够下令调查?王立军已经边缘化,下令调查肯定不是王立军嘛!那是谁在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想想这个体制,真是一点约束都没有。所以这种情况下让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是否应该把过去零零碎碎在博客或者是微博上面不是特别系统和正式的批评。除了“打黑”变成“黑打”之外,也包括对于“唱红歌”之类,写成一篇文章。我对于“唱红”也专门写过文章,对于那些“红歌”中所传递和不断再生产的意识形态进行过分析和批评。那篇文章是2011年6月份发表的。
促使我写那封公开信的另一个因素是,在2009到11年期间,越来越多的政界高层人物纷纷到重庆,他们大多要参观“打黑除恶展览”,至少根据重庆的媒体的报道,他们都对于那里的“打黑唱红”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让我忧虑。也许重庆所作所为的意义已经不限于西南一隅,大有代表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趋势。我觉得事情已经变得非常紧迫,怎样才能够让人们认清所谓“重庆模式”开历史倒车的政治意蕴?虽然自己没有太大的号召力,也没有任何的权力,但是作为一个学者,还有一种责任,尤其是西南政法毕业生和一个法学教授的一种责任。所以在压抑了一年左右时间之后,终于把这一年积下来这股郁闷不平之气变成了一封四千字的公开信。当然这样的东西首先来讲不能有任何的调侃,要特别真诚,与此同时要特别的理性。过去我读张思之先生的文章特别受感染和影响,你分析问题十分注意不情绪化,就是把事实和证据一条一条摆出来。当然,其中也有我的情感,还有对死亡的思考。末尾,我引用索福克勒斯的诗,人生年轻的时候大权在握的时候如此猖狂,但是人总有这一天,你会面对衰老病死。而且那些被判死刑的人们只不过比我们一般早走一些时日。无论是枪决还是砍头,都会留下可怕的创伤,但是我说那是一种无须再治疗的创伤。我也想到,这个公开信发出来会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因为重庆“黑打除恶”中的所作所为实在是一种红色恐怖。一些朋友也劝我要注意安全,注意会发生人身危险——后来揭露出来事实真的可以证明他们的确是视人命如草芥的。不过,也不要想那么多了,发了就发了,担心也没有多少用。因为这个缘故,你可以理解为什么今年2月份王捕头潜馆事件发生后我会那么开心,那么高兴,我当时在日本东京,好几个朋友跟我联系,晚上喝酒啊!现在,谷开来已经被判死缓,前天王立军在成都受审,许多人说薄熙来会不会切割出来,只是受到党纪处分。我说绝对不可能,这既是我的判断也是我的期望,你怎么说切割就会不受刑事追究,我预料他一定会受到刑事审判,因为他与前面的几个案件都脱不开干系,甚至此公很可能就是其中的主犯。谢谢!
提问:贺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最近有一个电影叫做《人山人海》,是第二个获得威尼斯奖的作品,你怎么看待这种中国独立电影,他是用一个电影艺术的方式包装了法律事业。
贺卫方:我没有看,等回去查一查。最近有不少纪录片制作人甚至艺术片的制作人越来越关注法律题材,我有机会参与到艺术家独立论坛这样一些活动中间,去接触一些艺术家,包括电影艺术,油画艺术,还有行为艺术、我觉得现在艺术界的人对法律的关注,让我真的感觉到特别的欣慰,他们做艺术家首先特别关心表达自由,尤其是现在这种行为艺术往往都带有政治批判的色彩。如果我们的政治制度不是宽容的对待他们,他们就没有办法生存。我想从历史上电影艺术对法律有些方面的表达往往会起到比好多篇法学论文重要得多的作用。比方说涉及死刑的电影,往往能够在一个国家中促成全民对死刑的反思。我这几年又在鼓吹废除死刑,我多么希望电影界友人能够拍一部电影,展现一个死刑犯临刑前的恐惧。如果能够把这样的恐惧表达出来,那对于我们反思死刑以及人道主义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希望回去看看你所说的《人山人海》,但是现在没有办法去发表评论。另外,你提到这部片子在国际上获奖,我想国际社会的支持也特别重要,尽管国际社会往往一支持,国内不可能上演了。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去努力改变国内法律方面对于艺术自由压制的状况。
谢谢大家!
人物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