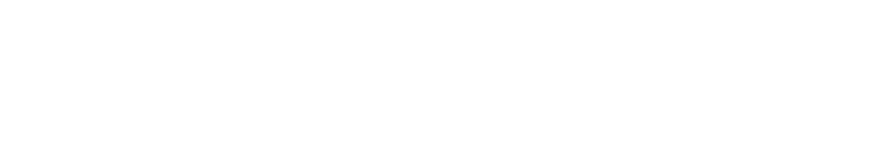奢侈消费 悲剧带给全人类
|
|
|||||||||||||||||
简介:
奢侈消费 悲剧带给全人类
资源是属于整个地球的,属于整个人类的。你奢侈消费,就会使得有限的公共资源急剧减少,使得他人或者后人没有可以消费的资源!
中国的奢侈
2009-11-25 11:39:59 来源: 中国新闻网(北京)
中国奢侈品行业在过去几年一直以20%以上的速度保持增长,在经济危机发生的2008年和2009年也一直如此。英国咨询公司OC&C预计,中国奢侈品市场的规模将在明年增至120亿美元,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位的奢侈品消费大国。
但奢侈品,这个刻上了时光价值的“稀有,无用,昂贵”之物,在中国,已经由权力阶层的专属,一转身变成了中产阶层的消费狂欢。不单是原来的贵族和商业富豪在使用奢侈品,中国的中产们也以穿上或者拥有一个奢侈LOGO为荣。奢侈品在中国走过了什么样的路径?奢侈品在中国的未来是从消费到制造,还是由炫耀变低调?拥有奢侈品,仅仅是身份的区别,还是可以赋予更多的含义?
奢侈中国,是中国另一面的当下。
中国:一步跨进奢侈的门
奢侈品是他们试图证明价值的工具。这些人喜欢购买,但更关注折扣。他们还没有富裕到毫不关注价钱
本刊记者/王家敏(发自北京、上海)
2009年冬天,北京国贸地铁站。人流涌动中,一个年轻女孩挎着Gucci包匆匆坐上地铁。她的背后,是Gucci今年新挂出的巨幅时尚广告。
在中国,年轻女孩挎着Gucci或者LV包坐地铁,不再是罕见的事。穿梭在城市地铁里的上班族,已可以与棕榈泉豪宅里的富太太们拥有同一款奢侈手包。
这个冬天,或许是奢侈品与中国内地消费者最为贴近的一刻。
10月,毕马威《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追上潮流》报告显示,过去两年间,中国消费者对奢侈品牌熟悉度增加,认识的品牌平均达到60多个,北京和上海消费者认识品牌的数目分别是70.5个和73.3个。
与之对应的,是近年来奢侈品消费总额在中国暴涨。2004年,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统计)仅为20亿美元;而至2009年11月,这个数字(据全球战略咨询公司贝恩统计)可望变成96亿美元。
而普华永道则更加乐观。他们预测,到2015年,中国将会成为全球奢侈品的最大买家。
一个奢侈品消费的大国正在诞生。是谁,创造了这些消费数据,社会名流,杜拉拉们,还是大富豪?
洪晃,崇拜工艺与细节
社会名流,看起来是奢侈品理所当然的消费者。
洪晃,章含之的女儿,文人章士钊的外孙女,12岁被外交部送往纽约学习,1984年毕业于美国纽约州瓦萨大学。现在,洪晃是《iLOOk 世界都市》《青春一族》《名牌世界乐》三本时尚杂志的出版人,并经常以社会名流的身份,出席各类时尚晚宴和社会活动。
她对经典奢侈品牌了如指掌,搭配套装的爱马仕丝巾,迪奥的马鞍包,香奈尔的口红,她甚至还能介绍优秀的设计师,比如蒂凡尼的西班牙设计师Elsa Peretti。
但她自己买的不多。洪晃最想拥有的一套衣服,是香奈尔的经典套装。她也关注每年路易威登发布的限量包。和所有女人一样,洪晃对高级珠宝着迷。“但你知道,它太昂贵了。但不买也可以欣赏,去享受它价值的一部分。”
“很多人觉得奢侈品是为了让人看,实际上不过是自己的享受。”洪晃觉得,一件奢侈品最重要的,是需要读懂它的工艺和意识。当她拿“那么薄的骨瓷碗吃饭”时,饭还是一个味儿,碗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功能,但“你的姿态会不一样,感觉会不一样,包括你咬饭的嘴都会不一样”。奢侈品,就是将生活每一个细节品味到极致,用洪晃的语气说,“就是矫情。”
真正的奢侈品之道,在洪晃看来,就是“品味”的内涵。这种东西,可以感觉、触摸,但很难表达。比如,洪晃喜欢的福建肉松、精致旗袍和茉莉花,这都是外婆喜欢的东西。“品位一定和生活相关。我外婆很讲究。我们家的肉松,每次都找福建的一个师傅现做,外婆的旗袍没多少款式,但她非常清楚哪件是哪个裁缝做的,每一件的针脚都要考究。”
最为特别的,是外婆最爱的茉莉花。当时北京有一个张师傅,人们都知道张师傅的茉莉花是最香的。每天一大早,张师傅派徒弟送一筐子茉莉花过来,外婆就先挑一朵别在旗袍上,作为她的香水。
“对于我来说,从小看着外婆的讲究,觉得生活应该是这样的。”洪晃说,“ 当然,这些都是在文革前。”革命的时尚就是实用,洪晃认为这是当下很多人难以理解奢侈感受的原因之一,“文革那时候出的椅子,不可能有曲线、有雕花。绝对就是能够坐人的一个椅子而已。”

接触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奢侈品牌,则是在洪晃大学毕业以后。在上个世纪末的美国,洪晃用800美金买了第一个香奈尔经典棱格包。“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啊,但我太想要了。少女时期遇到文革,心里那种公主劲儿完全没挥发出来,香奈尔就是给我大小姐的感觉。”
洪晃说,那时候不懂工艺,什么都不懂,也不知道什么奢侈品品牌,真正了解还是等到进入时尚行业之后,“越是简单的东西,工艺与设计越是高明”。
她在一些品牌的参观活动中,看到欧洲人所信守的工艺和精致,比如像Birkin Bag的严格工序,陀飞轮腕表的几百个零件等等。
2009年,洪晃到卡地亚参观钻石的切割与镶嵌。这次难得的机会使得洪晃拿着小本子去记录每一个生产的细节。最让洪晃感动的是抛光师。抛光师负责把珠宝的坐件在镶嵌之前抛光,其中一个老师傅干了23年。“他的工作,就是把一根棉线穿进要镶嵌珠宝的眼里面,把镶嵌之后根本看不见的地方也都擦得贼亮。”
“你抛光的部分以后谁也看不见,不觉得浪费时间吗?”洪晃问这位师傅。老头看了她一眼说,“一个东西看不见,不说明不存在。上帝在呢。”
洪晃崇拜这个23年如一日的老头。洪晃告诫现在的奢侈品消费的年轻人,“不用等着谁来告诉你什么是工艺,这个没用的。需要熏陶,需要感受。”
2008年奢侈品消费在中国大行其道之后,《穿Prada的女魔头》也成为风靡话题。有人问洪晃,是否会成为中国的“时尚女魔头”?洪晃说,魔头一定要有自己独特的声音,“以前人家说我是文化人我就高兴,说我是时尚人物我就皱眉头。现在我想开了,我就是时尚人物,但是要做魔头,我还需要更多的行业知识。”
“杜拉拉”阶层的梦想
洪晃买到第一个香奈尔包是在1984年。20多年后,奢侈品在中国内地的消费者已经不再出身名流阶层。2009年初,洪晃在《ILOOK》杂志上说,“世界是平的,我们的符号是名牌。你是爱马仕男,我是香奈尔女,而我们大家,都是路易威登包。”
洪晃三教九流的朋友都有,这些朋友对奢侈品的态度并不一致。洪晃的妈妈章含之,以及洪晃的大部分朋友,特别是文化人,包括张永和、刘索拉对某一种奢侈品都有特定偏好。张永和喜欢山本耀司的服装设计,刘索拉喜欢香奈尔的化妆品,母亲章含之喜欢路易威登鞋。
但这些文化人之外,洪晃还有很多都市中产阶级朋友。这个群体现在已经渐渐成为中国奢侈品消费的中坚力量。
一本叫做《杜拉拉升职记》的书,生动记录了这群都市阶层。他们被包裹在一种叫做生存法则的东西中,生活中除了职场竞争,就是生活压力和人生困惑。他们不停地打拼和追逐,只为了在这个社会上争得一席之地。
奢侈品是他们试图证明价值的工具。这些人喜欢购买,但更关注折扣。他们还没有富裕到毫不关注价钱。洪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我有一个朋友能够告诉你,买ROLEX最好去曼谷,比内地、香港都便宜些。我也不知道她怎么算出来的,但是真的很精。”
Amanda Ma就是那样“精”的一位。她看重某种奢侈品牌的设计与价格,但购物渠道不是大的购物中心,而是机场免税店、托人代购甚至网络购买,更关注直营店铺的打折信息。“你要知道,购物的愉悦感很快就会过去,我必须得确定它物有所值。” Amanda 说。
至于为什么要拥有它, Amanda认为,在高档写字楼工作,无法回避酒会就像无法回避朝九晚五。为礼服配上的鞋,一定要是Manolo Blahnik或Ferragamo,“你没有一件大牌,写字楼的人们会觉得你是不是‘太年轻’?”
Amanda感觉自己“被潮流赶着向前走”,一旦停下来,就会显得与这个繁华都市格格不入。在上海地铁,穿梭着精致衣着的“杜拉拉”们带着路易威登、香奈尔或是古驰,而北京五道口城铁站的安检机,则为女士们准备了塑料袋。一位安检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每天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她们担心安检机的履带弄脏了名牌包。”
Amanda开始想不清楚,“路易威登”算是经典还是随众?
洪晃说,“这是天然的困惑,杜拉拉们与奢侈品有着天然的矛盾。”
奢侈品的概念随时代变化。奢侈品对精致工艺有一种神圣化的追求,这种理想在欧洲从18世纪开始,二战以后逐渐破灭。“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手工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当机器时代来临,人的手工贬值,人们觉得机器比人做得好,针脚也密,产量也高。”
“杜拉拉”们伴随着工业时代与跨国公司而产生。他们与工艺没有联系,也没有感觉。这时候,他们消费的是创新。洪晃认为,“他不只是看这个手工有多好,重要的是看设计,一个新的款式。奢侈品的设计经典,但也随着生活形势而改变。以前女人的包都很小,现在的包越来越大,是因为女人需要的东西越来越多,要放化妆品,甚至一个上网笔记本。”
这是众多奢侈品牌能够在新的环境下持续其魅力的原因。“尽管欣赏工艺不再被人们推崇,但它们确实更为贴切地进入了大众的生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李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奢侈品的大部分消费者是中产阶层,他们不必要都懂工艺,也买不起顶尖奢侈品,可能买个钱夹、一个包或一条丝巾。这些入门产品,满足了普通人想要体验奢侈的梦想。”
Amanda拥有的第一件奢侈品是一瓶No.5香水。她有时候甚至会略微有些骄傲地自嘲,“买不起豪宅,嫁不到精英。但是我能穿着NO.5香水入睡,就像玛丽莲·梦露一样。”
富豪的符号
不管中产对奢侈品有多么钟情,真正消费起奢侈品来,大手笔的始终还是富有的人。胡润“2009富豪消费价格指数”报告中说,中国内地的顶尖奢侈品消费群体中,资产在1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有82.5万人,身价过亿的则有5.1万人。另一份《2009中国千万富豪品牌倾向报告》则显示,豪华车、手表和珠宝等奢侈品,大部分都在富豪的消费名单上,而这些消费,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并不大。
“周围邻居不是开奔驰就是开宝马!你要是开一日本车,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这句曾经的电影台词,如今是大陆富豪的生活写照。但2009年新上映的某部电影却试图告诉大众,“开宝马奔驰那是暴发户,你得有点品”。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奢侈品似乎与暴发户划上了等号。洪晃说,“至少存在一些有钱人,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那样买东西,花起钱来简直让我目瞪口呆。”
这些让洪晃“目瞪口呆“的富豪,消费行为隐含在这些数据中:2005年上海国际顶级私人物品展,7000名大富豪创造了2亿元销售额,部分富豪当场决定购买;2008年国际顶级私人物品展, 1万多名来自京津唐、东北和山西等地的富豪参观, 60家国际顶级品牌参展,展出超过300件稀世珍品,其中超过1/3的展品为首次在中国乃至亚洲地区亮相。为保持高端私密的风格,展会不向公众开放,仅面向受邀VIP。至于成交金额,则至今没有对外公布。
从这些神秘的消费行为中,可以毫无保留地划分出地位和等级。罗·福塞尔在《class(阶层)》一书中说,在西方,欧洲的皇室贵族血统成员是“看得见的顶级阶层”,而各个企业主是“高级阶层”。一般传统奢侈品牌,向来由皇室贵族首先进行引导消费,而“有产阶级”也会“以拥有奢侈品牌而虚荣”。
在中国,这种宽泛的“虚荣”被加倍放大。英国《经济学人》最近说,“日本人曾经被认为是最盲信的消费群体,而现在中国人大有取而代之的趋势。他们接受那些并不十分了解的知名品牌,并以自己的理解去消费它们。”
“我觉得这个理解不是说你非得是什么贵族,你喝了三年的红酒,都喝不出感觉来?”洪晃认为,刚开始,奢侈品消费也许是为了地位、虚荣等因素,但人的品位不可能永远停留在这里,“人都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当你在品味它,你就建立了生活和这个物品的直接关系。”
一些奢侈品公司也希望建立这样的关系。Gucci为中国消费者准备了概念店,公司首席执行官Patrizio di Marco认为,“越来越多的中国高级品牌消费者正在四处寻求时尚权威和‘意大利制造’所代表的工艺品质保证”。
江诗丹顿则在淮海中路的公馆内为顶尖客人打造会所。他们每年会举行为数不多的VIP活动,包括酒会与鉴赏活动,规模不大,每次仅有20多人。
江诗丹顿的店铺布置有书柜,里面放着关于钟表历史与工艺的书籍,还有从瑞士带来的制表工具。会所二楼专设了修表间。Alexandre Kerguen是从瑞士来中国的第一位制表师,每天大概有5位客人找到他。Alexandre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修表的客人,都是半个专家,“一开始他们只是买点什么东西,要这个,或者那个,后来他们开始跟我谈论钟表,谈论时间。”
中国奢侈品的市场路线图
奢侈品在中国市场的起步与盛况,与中国零售业的发展相辅相成
本刊记者/王家敏(发自北京、上海)
2009年11月,全球战略咨询公司贝恩在上海发布《全球奢侈品市场报告》,报告称,2008年中国奢侈品市场规模约为86亿美元,而2009年可望增至96亿美元。普华永道则预测,到2015年,中国将会成为全球奢侈品的最大买家。
笼统而庞大的奢侈品消费人群对面,站着更多清晰的面孔。他们是奢侈品公司、代理商、贸易公司、五星级酒店、百货公司、购物中心和中国商业逐步开放的条款与文件。
“这是消费者和商人们共同创造的市场,”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李飞说,“奢侈品在中国市场的起步与盛况,与中国零售业的发展相辅相成。”
从600元外汇券的领带开始
中国的奢侈新贵们有很多理由记住上世纪70年代末。1979年,皮尔·卡丹(Pierre Cardin)受邀在北京的民族文化宫举办了仅限专业人士参加的服装表演,8个法国模特和4个日本模特,为中国的“美学开放”走了第一场show。
奢侈品牌的震撼由此开始。1980年代,梦特娇、鳄鱼、老人头、花花公子相继到来,人们脑子里开始有了“品牌时装”的概念,它迅速吞没了几十年来的蓝布色调,服装制造厂也开始依葫芦画瓢追逐时尚,各色服装店还挂上了“某某时装”的牌子。
此时的大洋彼岸,伴随着经济繁荣与美国消费主义兴起,原本专为王室与世袭贵族等上流社会服务的奢侈品,有了更为广泛的市场。1985年,世界富豪伯纳德·阿诺特以15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正苦苦挣扎的克里斯汀·迪奥(Christian Dior),成为金融资本介入传统奢侈品家族企业的标志。此后,LVMH,历峰、PPR等大集团逐渐形成,奢侈品消费开始在全球范围蔓延。
当时,奢侈品集团盯准的对象是美国与日本。在中国,只有香港和内地沿海的贸易公司零星经营奢侈品牌,一些品牌甚至通过走私进入中国内地上流社会,真正知道这些品牌的人并不多。从事国际旅游行业的Anne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1989年朋友送了路易威登的包,我看着颜色老气,转手送给了保姆。当知道它价格奇高之后,才从保姆手里要了回来。”
直到1990年代,依托有外资背景的五星级酒店,奢侈品才登堂入室进入中国的主流社会。北京王府半岛酒店依照香港半岛酒店购物廊的模式,将酒店的地下一、二层辟为精品廊,开始出售高档商品。1991年8月8日,杰尼亚在精品廊开设了中国第一家奢侈品直营店,购买的人必须使用外汇券(FEC)。当时从事酒店行业的张朝阳女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候,出入五星级酒店的不是外宾,就是有地位的人。”
开业当天,张朝阳陪同英国朋友买了一条领带,600元的外汇券。“贵,但是很特别。当时的店员告诉我们,杰尼亚的领带必须用自己的系法,这样,别人一看就能辨别出品牌来。”

更具备辨别特征的显然是路易威登的独特LOGO。1992年,路易威登也在“王府地下”开设了中国内地第一家专卖店。1993年,巴宝莉在上海希尔顿酒店出现身影。
不断壮大的市场
“引进路易威登等大牌直营店是一种政策上的试水。”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李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按照当时中国的法律规定,禁止外商在中国设立公司,也不能直营店铺。大多数西方奢侈品牌,在中国都经过了先代理、后合资,再逐渐独资的过程。
1995年之前,由于外资品牌不能在中国合资连锁发展,代理商在奢侈品公司和中国市场之间,扮演了桥梁的角色。这些代理公司多数以地区授权的方式开办新店,或是在百货商店设立专柜。1999年之后,外资持股比例放宽,可以超过51%;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承诺2005年全面开放。
在外资品牌转变的过程中,两个文件扮演了核心角色。
第一个文件诞生在1996年。当年,外经贸部发布《关于设立中外合资对外贸易公司试点暂行办法》,奢侈品公司在中国的注册地逐渐从香港转移到内地,但多数集中在上海。1997年,杰尼亚在上海设立贸易公司,此时张朝阳成为其公关部经理,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主导杰尼亚进入中国市场的,是当时日本公司的CEO木通口一郎,这个精明的日本老头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并不满足于开几个小店面。”
第二个文件在2004年。这一年的6月1日,中国兑现加入WTO承诺,《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实施,外资品牌不再受开设连锁专卖店的限制,“实际上奢侈品公司一直想自己独立做,”李飞说,“他们相继收回代理权,大举铺开直营甚至是旗舰店。”
Gucci公司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显示,其1997年进入北京王府饭店,2001年在上海时代广场又开了一家店铺,而2004年新开店数量增加了3家,2006年为4家,2007年为7家,2009年截至11月新增数量增加9家。
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奢侈品消费增速正在大幅下滑。香奈尔集团因此裁员200人,占员工数1/10;法国高级定制时装品牌Christian Lacroix申请破产保护;英国奢侈陶瓷公司 Waterford Wedgwood申请破产保护,美国私人投资公司KPS收购其全球部分资产,包括香港子公司。
而中国却很快成为奢侈品的避难天堂。2009年11月,Wedgwood第七代传人Thomas Rowland Wedgwood借品牌诞生250周年的机会第二次来到上海,邀请VIP客户在恒隆广场享用英式下午茶,亲自为客户讲解英国陶瓷的历史与工艺。Thomas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中国是个非常重要的市场,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时机。”
零售市场咨询公司Husband Retail Consulting的数据显示,2009年底前,还将有近300家顶级店铺在北京开业。而上海2010年世博会开幕前,至少还有十个顶级奢侈品牌将在淮海路开张旗舰店。
多家机构发布的数据表明,中国奢侈品行业近年来一直保持20%以上的增长速度。李飞认为,“尽管这些都是部分调查数据,没有人能得出准确的统计结果,但至少我们能看到,奢侈品牌对中国市场的热情。”
不仅是数量,奢侈品牌也打起了“面积战”。2008年9月,银泰中心爱马仕(Hermes)店开幕,其全球首席执行官Patrick Thomas到场为新店进行剪彩。这是爱马仕在中国内地面积最大的专卖店,342平方米。2009年6月,Gucci在中国的第28家店面——1600平方米的新旗舰店开幕于上海金鹰国际购物广场。与之隔街的是位于恒隆广场的普拉达(Prada)专卖店,占据了临街两层的位置。
“奢侈品战略的核心就是零售,开旗舰店,争地段,要形象。” 意国时尚总裁严峻涉足奢侈品研究,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开店的地段能说明品牌的实力,也能说明他们对这个市场的重视程度。
从百货到购物中心
与奢侈品市场在中国的发展相伴的,是中国零售业的发展。李飞说,“富有阶层的扩大,奢侈品需求增加,为百货商店提供了发展空间。一方面五星级酒店的专卖网点并不便利,另一方面百货商店由于其他零售业态的挤压,也需要向高档化发展。当时中国高档百货还出现了一种新的经营形式:联营,即并非按照商品品类陈列,而是按照品牌来陈列的。欧美的豪华商店除了对路易威登外,没有这样变通过,而在中国,奢侈品牌有这样的‘特权’。”
1992年,燕莎友谊商城在略显荒凉的京东北落成,天价商品迅速在富人圈中打开名声。1993年,燕莎友谊商城实行合资,成为国内第一家开业的中外合资零售商业企业。新光天地购物中心副总经理庞琨,当时任燕莎商城市场经理。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合资的活力比当时很多国营百货商店强,我们开始引进一些国际品牌。”
“麻烦的是遇到1993年国内经济疲软,我们顶了很大的压力。”庞琨说,“零售业本来就没有接触过多少外国东西,消费环境也不像现在。”
燕莎与当时另一家高档百货赛特还引发了一场媒体大争论。1993年2月,《经济日报》发表《赛特你太离谱了》一文,指责赛特的价格“贵得太离谱”。3个月后,《北京晚报》则以《燕莎、赛特也许不太离谱》回应。刚跨入市场经济门槛的零售业,面临观念之争。
尽管如此,奢侈品牌与代理商仍大手笔租下店面和柜台。1993年6月,上海的伊势丹百货也高调开业,全面引进高端进口化妆品牌,香奈尔就是在这里开设了第一个化妆品专柜,至1998年,迪奥、爱马仕、阿玛尼 Armani、古驰Gucci等品牌相继试水中国市场。
通过零售,消费者最初接触到的,可能是一瓶香奈尔香水,一副迪奥的太阳镜。这些入门产品成为中国市场的热销品,人们进不了五星饭店,总买得起一瓶真正的品牌香水。这就是奢侈品贴近大众的“香水法则”,以此培养出大量潜在消费者。
但奢侈品市场真正的发展,最终依赖于奢侈品旗舰店的诞生。2000年以后,一种新的购物方式在中国兴起,上海的中信泰富、恒隆广场,北京的新光天地、银泰百货陆续开业,淮海路、国贸、大望路等商圈也逐渐形成。这些优良地段大都为奢侈品牌所包揽。
庞琨说,“不是我们要刻意推什么品牌,这是市场的天然选择。无论在燕莎还是在新光天地,我们零售商想的只是让中国的消费者拿到世界一流的商品。”
到每一个城市去
一些奢侈品牌在全球的大秀,一个国家只选择一个城市,在中国,则几乎是上海和北京两个城市同时举行。严峻认为,“更大的趋势是,奢侈品零售店面已经向新发展起来的富裕城市蔓延。”
大城市不再是富裕的代名词。2009年,胡润百富在上海发布《2009中国千万富豪品牌倾向报告》指出,中国52%的富人生活在北京、上海以外的城市,二、三线城市居民对奢侈品的消费能力也越来越高。2007年后,奢侈品在中国发展最快的不是北京、上海,而是成都、哈尔滨、大连、重庆、西安、无锡、温州、宁波等二、三线城市。
与一线城市相比,二、三线城广告、人力、运营成本更低,同类比较更少,中产阶级群体稳定,利润空间也更高。而杰尼亚进入中国之初就没有忽略青岛,江诗丹顿也在宁波开设了旗舰店。欧米茄的旗舰店更是开往了鞍山。GUCCI的30家店面中,有20家在二、三线城市,他们认为,“在三至五年内,中国将形成全新的城市格局。”
“大城市市场的消费者已经很成熟,开始挑剔品牌风格与服务,对价格也更敏感,”庞琨说,“我们已经提供了与欧洲几乎零时差的商品,但因为高关税造成的价格差,一些客人到店里来就是看看价格和款式,然后选择国外或香港代购。”
随着中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很难统计有多少内地人选择海外购买奢侈品。据国家旅游局统计,2007年,中国出境旅游4095万人次,居亚洲第一位;2008年出境总人次数为4584.44万,比2007年增加11.9%。AC尼尔森的调查显示,中国出境游购物消费每年达30多亿美元,且有上升趋势。
LVMH旗下的DFS全球免税店经营众多奢侈品牌,在北京、上海设有办事处,但客户并不受地域限制。张朝阳从杰尼亚公司离开后,成为荷兰GASSAN钻石驻北京首席代表,“我们在内地暂时没有店铺,在荷兰的总部每年接待数量可观的中国游客,他们可能来自中国任何一个城市。”
她们,将“中国制造”刻在奢侈品上
西方的奢侈品工业以家族传承的方式发展,但在中国,多数工艺的创造者,没有被世人提升到其应有的艺术地位和产业地位,也没有形成个人的品牌和家族产业
本刊记者/王家敏
几乎在中国成为奢侈品消费大国的同时,一些咨询机构建议中国企业“选择合适的销售渠道及媒体传播方式,精准的人群定位,打造个性化的奢侈品品牌”。
当奢侈品的消费逐渐成熟,一国的奢侈品消费就会渐渐由模仿到制造。上个世纪的意大利、美国和日本,都曾经有过相似的路径。
中国很少的一些人,正在成为这样的定义者。他们中有的人,坚持要走二十年的设计之路,有的则身居乡野,精细打磨一个现在还不为人知的品牌。他们的名字,并没有淹没在打造品牌的浮光掠影中。有人说,中国第一代的这批人,注定要成为中国奢侈品产业的铺路石。

郭培的梦想
郭培,高级成衣定制商,北京玫瑰坊时装有限责任公司创办人兼总设计师。从1997年5月开始创办玫瑰坊时装有限公司至今,郭培的高级成衣订制之路已经走了整整十二年。在此之前,郭培曾是天马服装公司的设计师。
2009年11月02日,中国国际服装周在北京举办。郭培在服装周上演绎了她的“极繁主义”设计。这场名为“一千零二夜”的服装发布会,以极精细的手工组合饰物与皮草,完全掩盖布料,一反时尚界流行的现代风格。设计的奢华繁复中,郭培对细节的追求几乎到了极致,“发布会上大家看到的所有刺绣,一针一线,都是我们自己做的。中国古代服装的辉煌刺绣让我感动,成为了我做高级时装的坚持。”
郭培迷恋中国手工艺,但她并没有拿着“中国元素”做文章。在她眼里,“中国元素”是中国的成功,但设计师的成功与任何元素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郭培的设计生命始于1980年代。那时候的中国,服装设计还在摸索中成长。郭培向美院的老师学素描、画人体解剖,向技校的老师学裁剪、制版,成为了第一批科班出身的服装设计师。1996年,她首次举办个人时装发布会“走进一九九七”,英国《ELLE》杂志介绍了这位中国设计师的作品。一年后的1997年,她创办了北京玫瑰坊工作室,走进了高级服装定制行业:“工业化带来千篇一律,追求个性化与高品质成为奢侈的梦想,而手工艺术是时装殿堂中最后一片净土。”
高级成衣定制是奢侈品中最能让人直接感受到尊贵礼遇的消费之一。严谨的设计流程,由一对一的专属设计到六次试装的量身剪裁,为满足客户需求不厌其烦的改动,都是高级成衣订制必须遵循的法则。能称得上高级定制的服装,无不是时间与心血、才华与工艺的共同造就。
“但高级定制在中国刚刚起步,它是慢慢成长的市场,因为最初大家把高级定制理解为一种服装加工,我们只能坚持用作品解说两者的差异。”
中国工业化以来,人们将手工制衣普遍视为落后。郭培认为,如今的社会,人应当是越来越受到尊重的,人力也是如此,“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的坐下来一针一线,完全靠生命的付出,靠时间的付出去创造一种价值。”
这种价值感,正是奢侈品的要义之一。吉尔·利波维茨基在《永恒的奢侈》一书中评价,奢侈品更多的是一种“做”或者“让人做”的方式,意味着人们对人力创造的接受与尊重。
慢慢地,人们开始接受高级定制的价值。新世纪以来的近十年,郭培也渐渐成为广受欢迎的高级定制设计。社会名流、企业精英、影视明星成为了郭培的客户,春晚的大部分礼服也由郭培打理。国际星章子怡还曾穿着郭培设计的礼服,参加奥运圣火采集仪式与格莱美颁奖典礼。
“社会名流、明星和老板们,可能更有定制服装的需要。我们的客户大部分是他们,和市场的接合面很小,还没有得到大众的认知。”郭培说。
2009年中国国际时装周上,郭培获得最佳女装设计师奖,李小燕、杨紫明等中国设计师的作品也让人惊艳不已。中国国际时装周则承担了这样的使命:不断传递中国时装的各种符号信息,以及传达中国需要更广泛顾客的信号。中国不仅需要欣赏者,还需要更多理解奢侈品符号的消费者。停留于代工时代的中国服装业,也希望重现当年意大利米兰服装制造的奇迹。
1951年,意大利时装商人Giovanni Battista Georgina举办了意大利第一场时装成衣发布会。这场发布会像一个宣言,预示着意大利的米兰,不再是法国服装业的手工大作坊,而成为自己就是中心的时尚之都。之后20年,意大利诞生了Pucci、Missoni等一大批成衣设计师和Max Mara、Giorgro Armani、Granni Versace、Gucci、Prada、Fendi等著名品牌。
“全球金融危机中最好的消息,莫过于中国设计师也开始抬头了,”洪晃说,但当前的政治与商业环境并非支持他们,“国家对创意产业的资助永远不可能落实到他们头上,国家的钱喜欢给机构。而中国的富人希望雇佣几个设计师,按照他们的指点去设计,这样的合作往往很短暂。中国的时尚媒体也是外国品牌主宰,好不容易介绍一个中国设计师,他们也会问,你觉得你是中国的Marc Jacobs吗?我就是我,我是其他谁啊?”
“每个人的创造都独一无二,”郭培坚持着自己的高级时装定制,“我所做的事情,不过是通过奢华的视角,去叫醒那些忽略了欣赏,对完美视而不见的眼睛。”
沈然的回归
相较于玫瑰坊的盛开,沈然的Manito皮具手工作坊刚刚萌芽。但她并不觉得自己弱小,“西方的大牌,他们最开始不也是一个家庭手工作坊吗?”
出身于设计专业,沈然的皮具没有“翻版”,但最令她最着迷的还是稳定的工序。一张铺着老地图的工作案,记录着每件手工皮具至少要经过的十道工序:设计图样,制版,选皮料,剪裁,粘贴,划线,打孔,缝合,打磨,上胶。沈然追求每一道工序的完美。她会根据款式反复挑选皮料的厚度与颜色,不厌其烦地打孔缝合,就算做出成品后看不到的地方,她也会精细的藏好线头。皮边的打磨,沈然也坚持纯手工,用砂纸一点一点打,不同角度打上三四遍。
现在也有磨边的机器,但沈然不用,她认为把机器掺到任何一道工序里,所有的工序都没有了意义。沈然认为,手工皮具的魅力在于品质的稳定,在于手工艺师所倾注的时间与生命,“一个手工艺人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制作的东西,使用者也能用一生的时间去享受这种稳定。”
沈然当然希望买走皮具的人们能欣赏它。但她并不能控制别人,也不想,所以只把东西卖给喜欢它的人。她也希望顾客知道,他们买走的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商品,总有一个人在背后为它负责。沈然将自己的皮具定义为奢侈品,纯手工制作和一对一服务,“皮具磨损很正常,都可以拿回来保养。每个大包的价格在3000元以上,但我的购买者还不是太有钱,价格再高他们难以接受。还有一些人觉得再添些钱,就能买到国际大牌了。”
在追求效率的社会,这样的手工艺人确实很难养活自己,但她相信这个方向。四年前北京还没有手工皮具的圈子,沈然想找一些书、一些资料非常难,后来日本、欧洲的皮具杂志大陆都有了,北京做手工皮具的人也有了一些,她还认识了宁波等地的朋友,包括进口皮艺工具的老板也跟着他们成长起来。沈然逐渐觉得这是个事业,她想或许还能是一辈子,一直做到敲不动为止。
沈然将爱马仕作为自己的标杆,“我最大的希望是去欧洲,成为爱马仕的工坊学徒,他们的学徒五年内不能独立做一个皮包,只能打杂,但这五年可能相当于我在这里的十年。”
爱马仕对手工的坚守是许多手工艺人的骄傲。1837年,蒂埃利·爱玛仕在巴黎创立了以自己姓氏为名的马具品牌,当时的马具当然是手工艺品。进入20世纪之后,大工业的批量生产席卷了人们的一切生活之时,手工的傲慢与意义,一点点地水落石出,它成了奢侈的必经之途。
沈然执著的同时,全世界都在为寻找这样手工艺人而烦恼,尤其是站在时尚产业尖端的人们。清华大学经管院教授李飞认为,“工艺对于奢侈品的重要,不仅在于传统,还在于皮具需要优秀的工匠,高级时装需要优秀的打版师,高级珠宝也离不开优秀的镶嵌师。”
20世纪20年代,巴黎有大约30万名手工工匠,绣工就有1万人。当高级定制让位于批量成衣,手工作坊工匠数目骤减,到新千年,巴黎的刺绣工只剩下不到200人。2002年香奈尔公司收购了著名的Lesage刺绣坊被,而总计收购了近十家家族式作坊的香奈尔公司也被公认为最聪明的角色。
中国看到了“复兴手工艺”的契机。2008、2009年中国国际时装周中,传统工艺受到多家服装品牌的推崇,NE·TIGER还特别推出“中国传统工艺与现代服饰”结合的主题。在NE·TIGER2009“国色天香华服大典”高级定制华服发布会上,总设计师张志峰携手两位古稀老人微笑出场,一位是曾为皇家制作龙袍的缂丝世家之第五代传人王嘉良,另一位是将几近失传的缂丝工艺再次复兴的缂丝大师王玉祥。
西方的奢侈品工业以家族传承的方式发展,但在中国,多数工艺的创造者,他们的技艺虽然通过师承的方式得到了延续和发展,但他们本人却隐没于“乾隆御制”或“江南织造”之中,没有被世人提升到其应有的艺术地位和产业地位,也没有形成个人的品牌和家族产业。当中国成为奢侈品消费大国,拥有的是沿海大规模的成衣制造工厂,和世界奢侈品品牌高级制造及高档原料采购大国的身份。
起点在1994年,以手制旗袍为卖点,中国第一个奢侈品牌 “上海滩”(Shanghai Tang)招揽了12位自20世纪初就以精湛缝纫手工而闻名的上海裁缝师傅。随着2005年11月上海滩第19家专卖店在日本东京开业,这个在香港出生的服装品牌,已经在全球13个国际大都市开设了专卖店,这其中包括时尚之都纽约、伦敦和巴黎。
2006年跨入成衣行业的玫瑰坊拥有300名绣工,而“东北虎”也拥有缂丝、苏绣、云锦等工艺,张志峰说,“中国的奢侈品牌要走向世界,在创造自我意识的同时,要有工艺,有文化,简单的抄袭和机械的模仿没有出路。”
奢侈品的精神印记
真正的奢侈品,背后一定有它的精神含量,这个精神含量对个人、对社会应该是有价值的
本刊记者/王家敏
一双鞋要结实舒适,一块钱很难达到,但是100块基本都能达到,但是当它卖到100万时跟舒适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在查达哈的《奢侈崇拜症》(The Cult of the Luxury Brand)一书中,这样的奢侈品消费被划分为5个发展阶段:镇压、金钱之始、炫耀、适应、生活方式。当今的日本,被归入“生活方式”一类,中国则被定位在第3个阶段——“炫耀”。
“一个普遍炫耀的奢侈品消费,说明存在一个普遍的、需要被尊重的人群。”复旦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孙时进认为,人们现在要做的,是找到奢侈品的精神价值。

精神的成长
10月,上海财经频道一个商务脱口秀栏目中,两个女孩展示自己创立的连锁酒店,竞争与汉庭酒店连锁创始人、董事长季琦一起午餐的机会。其中一位女孩自称“草根”,创立了求职青年旅舍,而另一位则是“富二代”,镜头不断切向她手上的香奈尔饰品,她开了一家精品酒店。
当主持人问季琦,“你也有女儿,会不会希望你的女儿也创业?”他回答,“不会,除非她愿意,因为创业很辛苦。”
“富二代”的女孩子当场就掉了眼泪。她说,从小到大,她的所有成功在别人眼里,原因都是自己是富二代,还长得漂亮,她想要通过创业证实自己的价值。“酒店都是我一砖一瓦从零到有创立起来的,我不停考察、学习、参加酒店峰会。我知道,我们富二代创业,就会承受更多社会和家里的压力。”
而在节目的最后,季琦问了“草根”女孩一个问题,“如果我给你年薪三十万,买你的创意,你到我的公司来工作如何?”她回答,“那你要让我把团队也带过来。”
季琦问“富二代”女孩,“你的酒店也不怎么赚钱,能不能1500万卖给我?”她回答,“我不愿意,我想把它做成我的事业,未来十年把我们的品牌打造出来。”
一开始倾向于“草根”女孩的评委们,最终选择了“富二代”。他们认为,“她在用心做商业,与人交流。”
“一个是为了生存,而另外一个人,则是希望证明自己的价值,我们对富二代的看法可能需要重新审视。”
“绝大部分人为了生存,很难想到自己的天职是成长。富二代已经不需要在物质这个层面上下功夫,他更多的精力可以放在怎么成长上,这对他来说就是天职。”
他们的精神成长,被通俗地称为附庸风雅,“这样的社会心理与他们的愿望大相径庭,”孙时进说,“实际上富人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与尊重。”
“就像那个富二代女孩一样,很少有人尊重她自身的努力,”孙时进说,或许长久以来,人们得到的尊重都太少了。当人们有了钱,就会花费很高的价格创造一种尊重。香奈尔,高级红酒,豪车豪宅,这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比如说茶叶、红酒,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品出其中滋味,一旦他长期用心品味,解读之后,就可能有助于他的人格成长。”
如果人们还没有钱,则普遍喜欢假冒的奢侈品,“这也说明国民普遍缺少被别人尊重,也并不尊重奢侈品背后的精神价值。”
“收养”工艺
同样,一个尊重奢侈品价值的社会,其背后的价值也能得到延续。一些商人更早发现了这一点。
不愿意透露名字的台北商人丘先生,跟一帮朋友在苏州挑选苏绣时,发现市面上的苏绣很一般。当他们深入了解当地情况后,发现苏绣艺术几乎快死亡了。丘先生很痛心,去探讨为什么?结果,丘先生发现,原因在于绣娘的报酬太低:“比如说一个绣卷,绣娘真正用心绣的话,恐怕要三四年的时间,在中国内地拿去卖,顶多也只卖几千块钱,没有人会用心绣。”
2006年,丘先生在苏州寻找了一批他们认为还有功底的绣娘,把她们的工作买断,“我说一年给你几万块钱的生活费,不要担心生活,你认真地去绣,然后我们再收购绣好的作品。”
丘先生认为,给他们的钱要够多,工艺师首先要有体面的生活。在奢侈品原产地欧洲,手工艺师是受人尊敬的职业。有270年生产历史的瑞士宝柏表(Blancpain),保持了几百年来只生产手工机械表的历史,江诗丹顿(Vacheron Constantin)至今保留着1755年招收手艺学徒的合同。在安特卫普,服装设计师是他们的骄傲,英国的瓷器工艺师则代代相传。
丘先生也得到了想要的工艺价值。他们最初的目的,只是作为一种欣赏品来收藏苏绣。而商人的思维使丘先生很快找到了其他的方式:如果这个东西的价格能在市场上得到承认,在赚钱的同时,还可以使中国的苏绣文化真正地流传下去。
他们将收购的绣品在各地展出,逐渐获得了市场,价格也比以往翻了数倍。“一个品牌绝不只是靠宣传、广告、策略,真正的奢侈品,背后一定有它的精神含量,这个精神含量对个人、对社会应该是有价值的。”孙时进认为,“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把商人看得很低下,那是因为没有真正的商人。商人就是通过市场,把真正好的东西卖出好价钱。幸运的工匠师与真正的商人合作,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理念,如果工匠只是想维持生活,你能想象他的作品理想会是怎么样?”
“但中国这样的商人还没有出来,或者说还不够。”孙时进说,“把工作作为一种理想,与长期的社会积累、经济发展有关,大部分商人还是停留在成为富人的思维上。”
布波族的升起
另一些人,则跳出了“富人-奢侈品”的思维逻辑,“布波族”(Bobos)就是例证。
2000年,美国专栏作家布鲁克斯写出了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布波族:一个社会新阶层的崛起》,“他们富裕却反对物质主义,用健康的法则而非道德的法则规范世俗欲望。遵循这些法则的人过着有纪律和自我节制的生活,但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他们的身体,而不是他们的灵魂。”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认为,布波族只是扔掉了一部分物质炫耀,但至少,一种不以物质为重心的时尚已经进入了精英阶层。

中国的布波族来得晚一些。他们基本由名牌大学制造,如果不是哈佛大学沃顿商学院的MBA,也起码是国内名校的EMBA。他们用实用主义的观点看待享乐,但必须与大众消费严格区分,长期使用同一个品牌,以昭显独特的品位。他们也可能对珠宝历史熟稔于心,或迷恋北京老城的胡同小店。
Ben算是其一。他在上海拥有几千万的豪宅,在北京也买下了昂贵地段的房产,在西南还拥有一套度假房。他的手腕上,始终是一块海鸥手表,他的车也是老牌的国产红旗车。
拼命追赶的人穿金戴银时,早富起来的Ben们则在水果蔬菜。“他们充分认识自己之后,不需要通过外在的物质手段来证实自己的社会地位。”孙时进认为,“他们才不会在乎别人看不出他昂贵衣服的价格,也不介意舒适豪车是不是贴上了晃眼的LOGO。”
如果“圈子”不再以财富来划分
——专访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
好的社会状态的一个特征是,社会中具有抵抗强权的力量,不管那强权是来自政治还是经济、商业、文化
本刊记者/王家敏
奢侈品消费在中国并不是舶来品。与此相反,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代表皇室荣耀的各种物品,无不精雕细刻并且因罕见而稀有昂贵。但奢侈品成为中国中产阶层的消费品,则时间并不长。与有阶层差异的社会相比,如今的商业社会,浸染了多少奢侈品的属性?这种属性在现代具备什么样的特性?《中国新闻周刊》为此专访了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郑也夫从事理论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和知识分子、消费主义问题研究多年。
奢侈品从来都有“区别性”
中国新闻周刊:有观点认为,奢侈品在封建时期,就是贵族的把玩和自我享受,并非“区别性物品”,因为他们无须再度证明自己。当奢侈品成为商品之后,则有了划分阶层的含义。这也是一些人把中国奢侈品消费定位在“炫耀”的原因?
郑也夫:这么说不准确。皇族一直在以种种手段建立与他人的“区别性”,对某种颜色、器物的垄断,住房建制的硬性规定,等等。炫耀是全人类,乃至全体动物的本能。
社会主义革命在上个世纪初期兴起后,人类企图造就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自然那是不可能实现的。反映在消费和奢侈品上,这种区别依然存在,甚至因为垄断而更彻底,社会效益更差。在前苏联,有专供高干消费的“小白桦树”商店,中国也同样。其最坏的负作用,就是“VIP方式”不进入公众消费领域,所以公众消费领域的质量低下得一塌糊涂。文化革命期间,高干子弟先是穿上了军装,别人没有,这就是搞“区别性”,后来索性穿上了“将校呢”,赤裸裸地炫耀。不错,那时因为商品匮乏,炫耀的手段贫乏。但决不是说那时没有了奢侈品和炫耀。那个时代也有人去高级餐馆,莫斯科餐厅,人们叫“老莫”,那种炫耀的得意,甚至高过今天的大吃大喝。
今天,虽然中国人的炫耀甚嚣尘上,但如果认为只有当今的中国人炫耀,那实在是太肤浅了。只能说,中国某些富人的炫耀更张扬、露骨、粗俗、赤裸裸一些。
中国新闻周刊:实际上,正是这些富人们也在引领着奢侈品消费文化?
郑也夫:中国的富人有钱有闲,但不是精神文化的领袖。因为历史原因,中国今天的富人多是暴发户,并且有一些是在极不干净的环境中暴发的,他们摆阔、铺张、不会过艺术化的生活。
要这些富人身心变得和谐一些,需要制度来制约,更需要他们自身慢慢提升。这需要并不短暂的时间,很多人一生都无力完成。如果中国社会能在下一代人中完成这一转换,就是福音。文化的作用还在其次,首先需要的是政治经济层面的公正,这要靠制度来保证。也就是说,首先要杜绝官商勾结,杜绝巧取豪夺。在富人身上,物质与精神的和谐的前提,是对财富的正确的认识:财富不是一切,挣钱不是全部。钱挣到很多的时候,个人的角色就变了,成为社会财富的看守者,成为一个特殊游戏的参与者。如果中国能完成这一转变,将是社会的巨大提升。
雷同在人类社会是乏味的
中国新闻周刊:消费不仅是人们的追逐,也是商人努力的结果。中国人的奢侈品消费热情,看上去更多的是消费社会或者说商人引领力量的来临?
郑也夫:消费社会的第一推动因素当然是商人。但是,商人不是无中生有,只是很好地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在1972年,美国社会学家埃文就说,“在今天谁是意识的领袖?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无冕之王;在今天西方世界中只有一个意识形态,就是消费,而他的领袖就是商人。”
如果把好生活作为人生观来吹捧,商人一定会成为话语权的垄断者。他们可以告诉你吃什么、穿什么、开什么车、住哪里,还能告诉你他们的商品有多少文化价值。他们一方面推动消费,另一方面营造消费为核心的人生观。造就了一个吃饱了饭就面临空虚的社会。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人们的消费与以往大不相同,凭借工业和全球化,大多数人得以温饱,但生存压力反而更大,追求创新与刺激超过了享受细节,这或许是数千年来人类所没有过的生存方式?
郑也夫:这样的生活方式就是时尚,人们全在时尚的笼罩下生活。多数人在不同程度上追逐时尚,人们的生活也被时尚牵着鼻子走,买车、买房、穿衣戴帽,都是如此。人们难以逃脱其外,成了房奴,车奴,不跟着走,好像就成了“等外品”、三等公民。
中国新闻周刊:这样的生存方式对“人”本身提出了挑战?
郑也夫:如果说对“人”有挑战,就是价值观上要彻底改观。但实际上对“人”并没有挑战,人还是追求“牛逼”,追求区别,这种本能是抹不掉的,雷同在人类社会都是乏味的。一些富人圈子是物质时代的产物,社会的进步在于圈子将不再以财富来划分。圈子没有等级是不行的,没有等级就没有文明,水准不等如何交流?只是以后的各种圈子将不再以“物”来划分,不再是通过房子、车子、钱,而是通过人自身的品质,智能、体能、技艺等等,未来的等级也应该是智力上的、技能上的、段位上的。这将是全社会共进的产物,是社会结构与观念共振的结果,不是哪个“精英阶层”可以独自挺进和到达的。
中国新闻周刊:当“物”越来越难以填补人们内心,商品也必然走向非物质化?
郑也夫:此前的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全面解决温饱,在那样的社会中,物质是炫耀的利器。当温饱解决了,空虚是大问题,甚至空虚就是温饱的副产品,如果继续以物质来炫耀,其一自己的身体承受不起,其二因工业带来的巨大复制能力,别人可以迅速拉平和你在某种商品占有上的差距,人们出于无奈,只好在物质之外寻找炫耀手段。
手工可以排除空虚,不是买手工制品,而是自己搞手工。身和心的关系很大,身体忙碌起来,心里就不空虚了。祖先是这样的,我们也只好这样。因为我们的身心和祖先其实没有差距。人们必须身心和祖先处于同一状态才舒适。
商业的民主化我们远远没有完成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确实有一部分人推崇“新手工”的生活方式,这种回归的社会原因是什么?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声音半个世纪不绝于耳,这样的回归恐怕也将经历数百年?
郑也夫:自制月饼、粽子、贺年卡,送给朋友要远比买来的商品恭敬、隆重。自己搞室内装修,既符合自己的要求,也可以实现自己创造潜能。在美国自己搞装修已经成为成年男性的游戏,美国已经兴起多年“Do It Yourself”,原因是耐人寻味的,回归手工的另一个本质原因,是对大规模生产不能造就“区别性”的厌倦。手工制品的个性当然突出,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我相信,手工制品和自制手工会回归得很快,因为后面有多重动力。
中国新闻周刊:无论消费还是文化,有更为广泛的人群共享这个成果才能是成功的。您认为这种商业意义上的民主化在中国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郑也夫:好的社会状态的一个特征是,社会中具有抵抗强权的力量,不管那强权是来自政治还是经济、商业、文化。其实商业的民主化我们远远没有完成,不过是以众多商人的格局代替了计划经济时代国家计委决定一切的格局。真正的经济民主化和商业民主化是,劳工与企业家的均衡,消费者与厂商的均衡,是前者有了充分的发言权。我们现在是后者在支配前者,在支配社会。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
资源是属于整个地球的,属于整个人类的。你奢侈消费,就会使得有限的公共资源急剧减少,使得他人或者后人没有可以消费的资源!
中国的奢侈
2009-11-25 11:39:59 来源: 中国新闻网(北京)
中国奢侈品行业在过去几年一直以20%以上的速度保持增长,在经济危机发生的2008年和2009年也一直如此。英国咨询公司OC&C预计,中国奢侈品市场的规模将在明年增至120亿美元,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位的奢侈品消费大国。
但奢侈品,这个刻上了时光价值的“稀有,无用,昂贵”之物,在中国,已经由权力阶层的专属,一转身变成了中产阶层的消费狂欢。不单是原来的贵族和商业富豪在使用奢侈品,中国的中产们也以穿上或者拥有一个奢侈LOGO为荣。奢侈品在中国走过了什么样的路径?奢侈品在中国的未来是从消费到制造,还是由炫耀变低调?拥有奢侈品,仅仅是身份的区别,还是可以赋予更多的含义?
奢侈中国,是中国另一面的当下。
中国:一步跨进奢侈的门
奢侈品是他们试图证明价值的工具。这些人喜欢购买,但更关注折扣。他们还没有富裕到毫不关注价钱
本刊记者/王家敏(发自北京、上海)
2009年冬天,北京国贸地铁站。人流涌动中,一个年轻女孩挎着Gucci包匆匆坐上地铁。她的背后,是Gucci今年新挂出的巨幅时尚广告。
在中国,年轻女孩挎着Gucci或者LV包坐地铁,不再是罕见的事。穿梭在城市地铁里的上班族,已可以与棕榈泉豪宅里的富太太们拥有同一款奢侈手包。
这个冬天,或许是奢侈品与中国内地消费者最为贴近的一刻。
10月,毕马威《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追上潮流》报告显示,过去两年间,中国消费者对奢侈品牌熟悉度增加,认识的品牌平均达到60多个,北京和上海消费者认识品牌的数目分别是70.5个和73.3个。
与之对应的,是近年来奢侈品消费总额在中国暴涨。2004年,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统计)仅为20亿美元;而至2009年11月,这个数字(据全球战略咨询公司贝恩统计)可望变成96亿美元。
而普华永道则更加乐观。他们预测,到2015年,中国将会成为全球奢侈品的最大买家。
一个奢侈品消费的大国正在诞生。是谁,创造了这些消费数据,社会名流,杜拉拉们,还是大富豪?
洪晃,崇拜工艺与细节
社会名流,看起来是奢侈品理所当然的消费者。
洪晃,章含之的女儿,文人章士钊的外孙女,12岁被外交部送往纽约学习,1984年毕业于美国纽约州瓦萨大学。现在,洪晃是《iLOOk 世界都市》《青春一族》《名牌世界乐》三本时尚杂志的出版人,并经常以社会名流的身份,出席各类时尚晚宴和社会活动。
她对经典奢侈品牌了如指掌,搭配套装的爱马仕丝巾,迪奥的马鞍包,香奈尔的口红,她甚至还能介绍优秀的设计师,比如蒂凡尼的西班牙设计师Elsa Peretti。
但她自己买的不多。洪晃最想拥有的一套衣服,是香奈尔的经典套装。她也关注每年路易威登发布的限量包。和所有女人一样,洪晃对高级珠宝着迷。“但你知道,它太昂贵了。但不买也可以欣赏,去享受它价值的一部分。”
“很多人觉得奢侈品是为了让人看,实际上不过是自己的享受。”洪晃觉得,一件奢侈品最重要的,是需要读懂它的工艺和意识。当她拿“那么薄的骨瓷碗吃饭”时,饭还是一个味儿,碗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功能,但“你的姿态会不一样,感觉会不一样,包括你咬饭的嘴都会不一样”。奢侈品,就是将生活每一个细节品味到极致,用洪晃的语气说,“就是矫情。”
真正的奢侈品之道,在洪晃看来,就是“品味”的内涵。这种东西,可以感觉、触摸,但很难表达。比如,洪晃喜欢的福建肉松、精致旗袍和茉莉花,这都是外婆喜欢的东西。“品位一定和生活相关。我外婆很讲究。我们家的肉松,每次都找福建的一个师傅现做,外婆的旗袍没多少款式,但她非常清楚哪件是哪个裁缝做的,每一件的针脚都要考究。”
最为特别的,是外婆最爱的茉莉花。当时北京有一个张师傅,人们都知道张师傅的茉莉花是最香的。每天一大早,张师傅派徒弟送一筐子茉莉花过来,外婆就先挑一朵别在旗袍上,作为她的香水。
“对于我来说,从小看着外婆的讲究,觉得生活应该是这样的。”洪晃说,“ 当然,这些都是在文革前。”革命的时尚就是实用,洪晃认为这是当下很多人难以理解奢侈感受的原因之一,“文革那时候出的椅子,不可能有曲线、有雕花。绝对就是能够坐人的一个椅子而已。”

接触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奢侈品牌,则是在洪晃大学毕业以后。在上个世纪末的美国,洪晃用800美金买了第一个香奈尔经典棱格包。“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啊,但我太想要了。少女时期遇到文革,心里那种公主劲儿完全没挥发出来,香奈尔就是给我大小姐的感觉。”
洪晃说,那时候不懂工艺,什么都不懂,也不知道什么奢侈品品牌,真正了解还是等到进入时尚行业之后,“越是简单的东西,工艺与设计越是高明”。
她在一些品牌的参观活动中,看到欧洲人所信守的工艺和精致,比如像Birkin Bag的严格工序,陀飞轮腕表的几百个零件等等。
2009年,洪晃到卡地亚参观钻石的切割与镶嵌。这次难得的机会使得洪晃拿着小本子去记录每一个生产的细节。最让洪晃感动的是抛光师。抛光师负责把珠宝的坐件在镶嵌之前抛光,其中一个老师傅干了23年。“他的工作,就是把一根棉线穿进要镶嵌珠宝的眼里面,把镶嵌之后根本看不见的地方也都擦得贼亮。”
“你抛光的部分以后谁也看不见,不觉得浪费时间吗?”洪晃问这位师傅。老头看了她一眼说,“一个东西看不见,不说明不存在。上帝在呢。”
洪晃崇拜这个23年如一日的老头。洪晃告诫现在的奢侈品消费的年轻人,“不用等着谁来告诉你什么是工艺,这个没用的。需要熏陶,需要感受。”
2008年奢侈品消费在中国大行其道之后,《穿Prada的女魔头》也成为风靡话题。有人问洪晃,是否会成为中国的“时尚女魔头”?洪晃说,魔头一定要有自己独特的声音,“以前人家说我是文化人我就高兴,说我是时尚人物我就皱眉头。现在我想开了,我就是时尚人物,但是要做魔头,我还需要更多的行业知识。”
“杜拉拉”阶层的梦想
洪晃买到第一个香奈尔包是在1984年。20多年后,奢侈品在中国内地的消费者已经不再出身名流阶层。2009年初,洪晃在《ILOOK》杂志上说,“世界是平的,我们的符号是名牌。你是爱马仕男,我是香奈尔女,而我们大家,都是路易威登包。”
洪晃三教九流的朋友都有,这些朋友对奢侈品的态度并不一致。洪晃的妈妈章含之,以及洪晃的大部分朋友,特别是文化人,包括张永和、刘索拉对某一种奢侈品都有特定偏好。张永和喜欢山本耀司的服装设计,刘索拉喜欢香奈尔的化妆品,母亲章含之喜欢路易威登鞋。
但这些文化人之外,洪晃还有很多都市中产阶级朋友。这个群体现在已经渐渐成为中国奢侈品消费的中坚力量。
一本叫做《杜拉拉升职记》的书,生动记录了这群都市阶层。他们被包裹在一种叫做生存法则的东西中,生活中除了职场竞争,就是生活压力和人生困惑。他们不停地打拼和追逐,只为了在这个社会上争得一席之地。
奢侈品是他们试图证明价值的工具。这些人喜欢购买,但更关注折扣。他们还没有富裕到毫不关注价钱。洪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我有一个朋友能够告诉你,买ROLEX最好去曼谷,比内地、香港都便宜些。我也不知道她怎么算出来的,但是真的很精。”
Amanda Ma就是那样“精”的一位。她看重某种奢侈品牌的设计与价格,但购物渠道不是大的购物中心,而是机场免税店、托人代购甚至网络购买,更关注直营店铺的打折信息。“你要知道,购物的愉悦感很快就会过去,我必须得确定它物有所值。” Amanda 说。
至于为什么要拥有它, Amanda认为,在高档写字楼工作,无法回避酒会就像无法回避朝九晚五。为礼服配上的鞋,一定要是Manolo Blahnik或Ferragamo,“你没有一件大牌,写字楼的人们会觉得你是不是‘太年轻’?”
Amanda感觉自己“被潮流赶着向前走”,一旦停下来,就会显得与这个繁华都市格格不入。在上海地铁,穿梭着精致衣着的“杜拉拉”们带着路易威登、香奈尔或是古驰,而北京五道口城铁站的安检机,则为女士们准备了塑料袋。一位安检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每天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她们担心安检机的履带弄脏了名牌包。”
Amanda开始想不清楚,“路易威登”算是经典还是随众?
洪晃说,“这是天然的困惑,杜拉拉们与奢侈品有着天然的矛盾。”
奢侈品的概念随时代变化。奢侈品对精致工艺有一种神圣化的追求,这种理想在欧洲从18世纪开始,二战以后逐渐破灭。“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手工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当机器时代来临,人的手工贬值,人们觉得机器比人做得好,针脚也密,产量也高。”
“杜拉拉”们伴随着工业时代与跨国公司而产生。他们与工艺没有联系,也没有感觉。这时候,他们消费的是创新。洪晃认为,“他不只是看这个手工有多好,重要的是看设计,一个新的款式。奢侈品的设计经典,但也随着生活形势而改变。以前女人的包都很小,现在的包越来越大,是因为女人需要的东西越来越多,要放化妆品,甚至一个上网笔记本。”
这是众多奢侈品牌能够在新的环境下持续其魅力的原因。“尽管欣赏工艺不再被人们推崇,但它们确实更为贴切地进入了大众的生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李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奢侈品的大部分消费者是中产阶层,他们不必要都懂工艺,也买不起顶尖奢侈品,可能买个钱夹、一个包或一条丝巾。这些入门产品,满足了普通人想要体验奢侈的梦想。”
Amanda拥有的第一件奢侈品是一瓶No.5香水。她有时候甚至会略微有些骄傲地自嘲,“买不起豪宅,嫁不到精英。但是我能穿着NO.5香水入睡,就像玛丽莲·梦露一样。”
富豪的符号
不管中产对奢侈品有多么钟情,真正消费起奢侈品来,大手笔的始终还是富有的人。胡润“2009富豪消费价格指数”报告中说,中国内地的顶尖奢侈品消费群体中,资产在1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有82.5万人,身价过亿的则有5.1万人。另一份《2009中国千万富豪品牌倾向报告》则显示,豪华车、手表和珠宝等奢侈品,大部分都在富豪的消费名单上,而这些消费,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并不大。
“周围邻居不是开奔驰就是开宝马!你要是开一日本车,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这句曾经的电影台词,如今是大陆富豪的生活写照。但2009年新上映的某部电影却试图告诉大众,“开宝马奔驰那是暴发户,你得有点品”。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奢侈品似乎与暴发户划上了等号。洪晃说,“至少存在一些有钱人,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那样买东西,花起钱来简直让我目瞪口呆。”
这些让洪晃“目瞪口呆“的富豪,消费行为隐含在这些数据中:2005年上海国际顶级私人物品展,7000名大富豪创造了2亿元销售额,部分富豪当场决定购买;2008年国际顶级私人物品展, 1万多名来自京津唐、东北和山西等地的富豪参观, 60家国际顶级品牌参展,展出超过300件稀世珍品,其中超过1/3的展品为首次在中国乃至亚洲地区亮相。为保持高端私密的风格,展会不向公众开放,仅面向受邀VIP。至于成交金额,则至今没有对外公布。
从这些神秘的消费行为中,可以毫无保留地划分出地位和等级。罗·福塞尔在《class(阶层)》一书中说,在西方,欧洲的皇室贵族血统成员是“看得见的顶级阶层”,而各个企业主是“高级阶层”。一般传统奢侈品牌,向来由皇室贵族首先进行引导消费,而“有产阶级”也会“以拥有奢侈品牌而虚荣”。
在中国,这种宽泛的“虚荣”被加倍放大。英国《经济学人》最近说,“日本人曾经被认为是最盲信的消费群体,而现在中国人大有取而代之的趋势。他们接受那些并不十分了解的知名品牌,并以自己的理解去消费它们。”
“我觉得这个理解不是说你非得是什么贵族,你喝了三年的红酒,都喝不出感觉来?”洪晃认为,刚开始,奢侈品消费也许是为了地位、虚荣等因素,但人的品位不可能永远停留在这里,“人都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当你在品味它,你就建立了生活和这个物品的直接关系。”
一些奢侈品公司也希望建立这样的关系。Gucci为中国消费者准备了概念店,公司首席执行官Patrizio di Marco认为,“越来越多的中国高级品牌消费者正在四处寻求时尚权威和‘意大利制造’所代表的工艺品质保证”。
江诗丹顿则在淮海中路的公馆内为顶尖客人打造会所。他们每年会举行为数不多的VIP活动,包括酒会与鉴赏活动,规模不大,每次仅有20多人。
江诗丹顿的店铺布置有书柜,里面放着关于钟表历史与工艺的书籍,还有从瑞士带来的制表工具。会所二楼专设了修表间。Alexandre Kerguen是从瑞士来中国的第一位制表师,每天大概有5位客人找到他。Alexandre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修表的客人,都是半个专家,“一开始他们只是买点什么东西,要这个,或者那个,后来他们开始跟我谈论钟表,谈论时间。”
中国奢侈品的市场路线图
奢侈品在中国市场的起步与盛况,与中国零售业的发展相辅相成
本刊记者/王家敏(发自北京、上海)
2009年11月,全球战略咨询公司贝恩在上海发布《全球奢侈品市场报告》,报告称,2008年中国奢侈品市场规模约为86亿美元,而2009年可望增至96亿美元。普华永道则预测,到2015年,中国将会成为全球奢侈品的最大买家。
笼统而庞大的奢侈品消费人群对面,站着更多清晰的面孔。他们是奢侈品公司、代理商、贸易公司、五星级酒店、百货公司、购物中心和中国商业逐步开放的条款与文件。
“这是消费者和商人们共同创造的市场,”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李飞说,“奢侈品在中国市场的起步与盛况,与中国零售业的发展相辅相成。”
从600元外汇券的领带开始
中国的奢侈新贵们有很多理由记住上世纪70年代末。1979年,皮尔·卡丹(Pierre Cardin)受邀在北京的民族文化宫举办了仅限专业人士参加的服装表演,8个法国模特和4个日本模特,为中国的“美学开放”走了第一场show。
奢侈品牌的震撼由此开始。1980年代,梦特娇、鳄鱼、老人头、花花公子相继到来,人们脑子里开始有了“品牌时装”的概念,它迅速吞没了几十年来的蓝布色调,服装制造厂也开始依葫芦画瓢追逐时尚,各色服装店还挂上了“某某时装”的牌子。
此时的大洋彼岸,伴随着经济繁荣与美国消费主义兴起,原本专为王室与世袭贵族等上流社会服务的奢侈品,有了更为广泛的市场。1985年,世界富豪伯纳德·阿诺特以15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正苦苦挣扎的克里斯汀·迪奥(Christian Dior),成为金融资本介入传统奢侈品家族企业的标志。此后,LVMH,历峰、PPR等大集团逐渐形成,奢侈品消费开始在全球范围蔓延。
当时,奢侈品集团盯准的对象是美国与日本。在中国,只有香港和内地沿海的贸易公司零星经营奢侈品牌,一些品牌甚至通过走私进入中国内地上流社会,真正知道这些品牌的人并不多。从事国际旅游行业的Anne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1989年朋友送了路易威登的包,我看着颜色老气,转手送给了保姆。当知道它价格奇高之后,才从保姆手里要了回来。”
直到1990年代,依托有外资背景的五星级酒店,奢侈品才登堂入室进入中国的主流社会。北京王府半岛酒店依照香港半岛酒店购物廊的模式,将酒店的地下一、二层辟为精品廊,开始出售高档商品。1991年8月8日,杰尼亚在精品廊开设了中国第一家奢侈品直营店,购买的人必须使用外汇券(FEC)。当时从事酒店行业的张朝阳女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候,出入五星级酒店的不是外宾,就是有地位的人。”
开业当天,张朝阳陪同英国朋友买了一条领带,600元的外汇券。“贵,但是很特别。当时的店员告诉我们,杰尼亚的领带必须用自己的系法,这样,别人一看就能辨别出品牌来。”

更具备辨别特征的显然是路易威登的独特LOGO。1992年,路易威登也在“王府地下”开设了中国内地第一家专卖店。1993年,巴宝莉在上海希尔顿酒店出现身影。
不断壮大的市场
“引进路易威登等大牌直营店是一种政策上的试水。”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李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按照当时中国的法律规定,禁止外商在中国设立公司,也不能直营店铺。大多数西方奢侈品牌,在中国都经过了先代理、后合资,再逐渐独资的过程。
1995年之前,由于外资品牌不能在中国合资连锁发展,代理商在奢侈品公司和中国市场之间,扮演了桥梁的角色。这些代理公司多数以地区授权的方式开办新店,或是在百货商店设立专柜。1999年之后,外资持股比例放宽,可以超过51%;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承诺2005年全面开放。
在外资品牌转变的过程中,两个文件扮演了核心角色。
第一个文件诞生在1996年。当年,外经贸部发布《关于设立中外合资对外贸易公司试点暂行办法》,奢侈品公司在中国的注册地逐渐从香港转移到内地,但多数集中在上海。1997年,杰尼亚在上海设立贸易公司,此时张朝阳成为其公关部经理,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主导杰尼亚进入中国市场的,是当时日本公司的CEO木通口一郎,这个精明的日本老头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并不满足于开几个小店面。”
第二个文件在2004年。这一年的6月1日,中国兑现加入WTO承诺,《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实施,外资品牌不再受开设连锁专卖店的限制,“实际上奢侈品公司一直想自己独立做,”李飞说,“他们相继收回代理权,大举铺开直营甚至是旗舰店。”
Gucci公司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显示,其1997年进入北京王府饭店,2001年在上海时代广场又开了一家店铺,而2004年新开店数量增加了3家,2006年为4家,2007年为7家,2009年截至11月新增数量增加9家。
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奢侈品消费增速正在大幅下滑。香奈尔集团因此裁员200人,占员工数1/10;法国高级定制时装品牌Christian Lacroix申请破产保护;英国奢侈陶瓷公司 Waterford Wedgwood申请破产保护,美国私人投资公司KPS收购其全球部分资产,包括香港子公司。
而中国却很快成为奢侈品的避难天堂。2009年11月,Wedgwood第七代传人Thomas Rowland Wedgwood借品牌诞生250周年的机会第二次来到上海,邀请VIP客户在恒隆广场享用英式下午茶,亲自为客户讲解英国陶瓷的历史与工艺。Thomas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中国是个非常重要的市场,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时机。”
零售市场咨询公司Husband Retail Consulting的数据显示,2009年底前,还将有近300家顶级店铺在北京开业。而上海2010年世博会开幕前,至少还有十个顶级奢侈品牌将在淮海路开张旗舰店。
多家机构发布的数据表明,中国奢侈品行业近年来一直保持20%以上的增长速度。李飞认为,“尽管这些都是部分调查数据,没有人能得出准确的统计结果,但至少我们能看到,奢侈品牌对中国市场的热情。”
不仅是数量,奢侈品牌也打起了“面积战”。2008年9月,银泰中心爱马仕(Hermes)店开幕,其全球首席执行官Patrick Thomas到场为新店进行剪彩。这是爱马仕在中国内地面积最大的专卖店,342平方米。2009年6月,Gucci在中国的第28家店面——1600平方米的新旗舰店开幕于上海金鹰国际购物广场。与之隔街的是位于恒隆广场的普拉达(Prada)专卖店,占据了临街两层的位置。
“奢侈品战略的核心就是零售,开旗舰店,争地段,要形象。” 意国时尚总裁严峻涉足奢侈品研究,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开店的地段能说明品牌的实力,也能说明他们对这个市场的重视程度。
从百货到购物中心
与奢侈品市场在中国的发展相伴的,是中国零售业的发展。李飞说,“富有阶层的扩大,奢侈品需求增加,为百货商店提供了发展空间。一方面五星级酒店的专卖网点并不便利,另一方面百货商店由于其他零售业态的挤压,也需要向高档化发展。当时中国高档百货还出现了一种新的经营形式:联营,即并非按照商品品类陈列,而是按照品牌来陈列的。欧美的豪华商店除了对路易威登外,没有这样变通过,而在中国,奢侈品牌有这样的‘特权’。”
1992年,燕莎友谊商城在略显荒凉的京东北落成,天价商品迅速在富人圈中打开名声。1993年,燕莎友谊商城实行合资,成为国内第一家开业的中外合资零售商业企业。新光天地购物中心副总经理庞琨,当时任燕莎商城市场经理。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合资的活力比当时很多国营百货商店强,我们开始引进一些国际品牌。”
“麻烦的是遇到1993年国内经济疲软,我们顶了很大的压力。”庞琨说,“零售业本来就没有接触过多少外国东西,消费环境也不像现在。”
燕莎与当时另一家高档百货赛特还引发了一场媒体大争论。1993年2月,《经济日报》发表《赛特你太离谱了》一文,指责赛特的价格“贵得太离谱”。3个月后,《北京晚报》则以《燕莎、赛特也许不太离谱》回应。刚跨入市场经济门槛的零售业,面临观念之争。
尽管如此,奢侈品牌与代理商仍大手笔租下店面和柜台。1993年6月,上海的伊势丹百货也高调开业,全面引进高端进口化妆品牌,香奈尔就是在这里开设了第一个化妆品专柜,至1998年,迪奥、爱马仕、阿玛尼 Armani、古驰Gucci等品牌相继试水中国市场。
通过零售,消费者最初接触到的,可能是一瓶香奈尔香水,一副迪奥的太阳镜。这些入门产品成为中国市场的热销品,人们进不了五星饭店,总买得起一瓶真正的品牌香水。这就是奢侈品贴近大众的“香水法则”,以此培养出大量潜在消费者。
但奢侈品市场真正的发展,最终依赖于奢侈品旗舰店的诞生。2000年以后,一种新的购物方式在中国兴起,上海的中信泰富、恒隆广场,北京的新光天地、银泰百货陆续开业,淮海路、国贸、大望路等商圈也逐渐形成。这些优良地段大都为奢侈品牌所包揽。
庞琨说,“不是我们要刻意推什么品牌,这是市场的天然选择。无论在燕莎还是在新光天地,我们零售商想的只是让中国的消费者拿到世界一流的商品。”
到每一个城市去
一些奢侈品牌在全球的大秀,一个国家只选择一个城市,在中国,则几乎是上海和北京两个城市同时举行。严峻认为,“更大的趋势是,奢侈品零售店面已经向新发展起来的富裕城市蔓延。”
大城市不再是富裕的代名词。2009年,胡润百富在上海发布《2009中国千万富豪品牌倾向报告》指出,中国52%的富人生活在北京、上海以外的城市,二、三线城市居民对奢侈品的消费能力也越来越高。2007年后,奢侈品在中国发展最快的不是北京、上海,而是成都、哈尔滨、大连、重庆、西安、无锡、温州、宁波等二、三线城市。
与一线城市相比,二、三线城广告、人力、运营成本更低,同类比较更少,中产阶级群体稳定,利润空间也更高。而杰尼亚进入中国之初就没有忽略青岛,江诗丹顿也在宁波开设了旗舰店。欧米茄的旗舰店更是开往了鞍山。GUCCI的30家店面中,有20家在二、三线城市,他们认为,“在三至五年内,中国将形成全新的城市格局。”
“大城市市场的消费者已经很成熟,开始挑剔品牌风格与服务,对价格也更敏感,”庞琨说,“我们已经提供了与欧洲几乎零时差的商品,但因为高关税造成的价格差,一些客人到店里来就是看看价格和款式,然后选择国外或香港代购。”
随着中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很难统计有多少内地人选择海外购买奢侈品。据国家旅游局统计,2007年,中国出境旅游4095万人次,居亚洲第一位;2008年出境总人次数为4584.44万,比2007年增加11.9%。AC尼尔森的调查显示,中国出境游购物消费每年达30多亿美元,且有上升趋势。
LVMH旗下的DFS全球免税店经营众多奢侈品牌,在北京、上海设有办事处,但客户并不受地域限制。张朝阳从杰尼亚公司离开后,成为荷兰GASSAN钻石驻北京首席代表,“我们在内地暂时没有店铺,在荷兰的总部每年接待数量可观的中国游客,他们可能来自中国任何一个城市。”
她们,将“中国制造”刻在奢侈品上
西方的奢侈品工业以家族传承的方式发展,但在中国,多数工艺的创造者,没有被世人提升到其应有的艺术地位和产业地位,也没有形成个人的品牌和家族产业
本刊记者/王家敏
几乎在中国成为奢侈品消费大国的同时,一些咨询机构建议中国企业“选择合适的销售渠道及媒体传播方式,精准的人群定位,打造个性化的奢侈品品牌”。
当奢侈品的消费逐渐成熟,一国的奢侈品消费就会渐渐由模仿到制造。上个世纪的意大利、美国和日本,都曾经有过相似的路径。
中国很少的一些人,正在成为这样的定义者。他们中有的人,坚持要走二十年的设计之路,有的则身居乡野,精细打磨一个现在还不为人知的品牌。他们的名字,并没有淹没在打造品牌的浮光掠影中。有人说,中国第一代的这批人,注定要成为中国奢侈品产业的铺路石。

郭培的梦想
郭培,高级成衣定制商,北京玫瑰坊时装有限责任公司创办人兼总设计师。从1997年5月开始创办玫瑰坊时装有限公司至今,郭培的高级成衣订制之路已经走了整整十二年。在此之前,郭培曾是天马服装公司的设计师。
2009年11月02日,中国国际服装周在北京举办。郭培在服装周上演绎了她的“极繁主义”设计。这场名为“一千零二夜”的服装发布会,以极精细的手工组合饰物与皮草,完全掩盖布料,一反时尚界流行的现代风格。设计的奢华繁复中,郭培对细节的追求几乎到了极致,“发布会上大家看到的所有刺绣,一针一线,都是我们自己做的。中国古代服装的辉煌刺绣让我感动,成为了我做高级时装的坚持。”
郭培迷恋中国手工艺,但她并没有拿着“中国元素”做文章。在她眼里,“中国元素”是中国的成功,但设计师的成功与任何元素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郭培的设计生命始于1980年代。那时候的中国,服装设计还在摸索中成长。郭培向美院的老师学素描、画人体解剖,向技校的老师学裁剪、制版,成为了第一批科班出身的服装设计师。1996年,她首次举办个人时装发布会“走进一九九七”,英国《ELLE》杂志介绍了这位中国设计师的作品。一年后的1997年,她创办了北京玫瑰坊工作室,走进了高级服装定制行业:“工业化带来千篇一律,追求个性化与高品质成为奢侈的梦想,而手工艺术是时装殿堂中最后一片净土。”
高级成衣定制是奢侈品中最能让人直接感受到尊贵礼遇的消费之一。严谨的设计流程,由一对一的专属设计到六次试装的量身剪裁,为满足客户需求不厌其烦的改动,都是高级成衣订制必须遵循的法则。能称得上高级定制的服装,无不是时间与心血、才华与工艺的共同造就。
“但高级定制在中国刚刚起步,它是慢慢成长的市场,因为最初大家把高级定制理解为一种服装加工,我们只能坚持用作品解说两者的差异。”
中国工业化以来,人们将手工制衣普遍视为落后。郭培认为,如今的社会,人应当是越来越受到尊重的,人力也是如此,“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的坐下来一针一线,完全靠生命的付出,靠时间的付出去创造一种价值。”
这种价值感,正是奢侈品的要义之一。吉尔·利波维茨基在《永恒的奢侈》一书中评价,奢侈品更多的是一种“做”或者“让人做”的方式,意味着人们对人力创造的接受与尊重。
慢慢地,人们开始接受高级定制的价值。新世纪以来的近十年,郭培也渐渐成为广受欢迎的高级定制设计。社会名流、企业精英、影视明星成为了郭培的客户,春晚的大部分礼服也由郭培打理。国际星章子怡还曾穿着郭培设计的礼服,参加奥运圣火采集仪式与格莱美颁奖典礼。
“社会名流、明星和老板们,可能更有定制服装的需要。我们的客户大部分是他们,和市场的接合面很小,还没有得到大众的认知。”郭培说。
2009年中国国际时装周上,郭培获得最佳女装设计师奖,李小燕、杨紫明等中国设计师的作品也让人惊艳不已。中国国际时装周则承担了这样的使命:不断传递中国时装的各种符号信息,以及传达中国需要更广泛顾客的信号。中国不仅需要欣赏者,还需要更多理解奢侈品符号的消费者。停留于代工时代的中国服装业,也希望重现当年意大利米兰服装制造的奇迹。
1951年,意大利时装商人Giovanni Battista Georgina举办了意大利第一场时装成衣发布会。这场发布会像一个宣言,预示着意大利的米兰,不再是法国服装业的手工大作坊,而成为自己就是中心的时尚之都。之后20年,意大利诞生了Pucci、Missoni等一大批成衣设计师和Max Mara、Giorgro Armani、Granni Versace、Gucci、Prada、Fendi等著名品牌。
“全球金融危机中最好的消息,莫过于中国设计师也开始抬头了,”洪晃说,但当前的政治与商业环境并非支持他们,“国家对创意产业的资助永远不可能落实到他们头上,国家的钱喜欢给机构。而中国的富人希望雇佣几个设计师,按照他们的指点去设计,这样的合作往往很短暂。中国的时尚媒体也是外国品牌主宰,好不容易介绍一个中国设计师,他们也会问,你觉得你是中国的Marc Jacobs吗?我就是我,我是其他谁啊?”
“每个人的创造都独一无二,”郭培坚持着自己的高级时装定制,“我所做的事情,不过是通过奢华的视角,去叫醒那些忽略了欣赏,对完美视而不见的眼睛。”
沈然的回归
相较于玫瑰坊的盛开,沈然的Manito皮具手工作坊刚刚萌芽。但她并不觉得自己弱小,“西方的大牌,他们最开始不也是一个家庭手工作坊吗?”
出身于设计专业,沈然的皮具没有“翻版”,但最令她最着迷的还是稳定的工序。一张铺着老地图的工作案,记录着每件手工皮具至少要经过的十道工序:设计图样,制版,选皮料,剪裁,粘贴,划线,打孔,缝合,打磨,上胶。沈然追求每一道工序的完美。她会根据款式反复挑选皮料的厚度与颜色,不厌其烦地打孔缝合,就算做出成品后看不到的地方,她也会精细的藏好线头。皮边的打磨,沈然也坚持纯手工,用砂纸一点一点打,不同角度打上三四遍。
现在也有磨边的机器,但沈然不用,她认为把机器掺到任何一道工序里,所有的工序都没有了意义。沈然认为,手工皮具的魅力在于品质的稳定,在于手工艺师所倾注的时间与生命,“一个手工艺人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制作的东西,使用者也能用一生的时间去享受这种稳定。”
沈然当然希望买走皮具的人们能欣赏它。但她并不能控制别人,也不想,所以只把东西卖给喜欢它的人。她也希望顾客知道,他们买走的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商品,总有一个人在背后为它负责。沈然将自己的皮具定义为奢侈品,纯手工制作和一对一服务,“皮具磨损很正常,都可以拿回来保养。每个大包的价格在3000元以上,但我的购买者还不是太有钱,价格再高他们难以接受。还有一些人觉得再添些钱,就能买到国际大牌了。”
在追求效率的社会,这样的手工艺人确实很难养活自己,但她相信这个方向。四年前北京还没有手工皮具的圈子,沈然想找一些书、一些资料非常难,后来日本、欧洲的皮具杂志大陆都有了,北京做手工皮具的人也有了一些,她还认识了宁波等地的朋友,包括进口皮艺工具的老板也跟着他们成长起来。沈然逐渐觉得这是个事业,她想或许还能是一辈子,一直做到敲不动为止。
沈然将爱马仕作为自己的标杆,“我最大的希望是去欧洲,成为爱马仕的工坊学徒,他们的学徒五年内不能独立做一个皮包,只能打杂,但这五年可能相当于我在这里的十年。”
爱马仕对手工的坚守是许多手工艺人的骄傲。1837年,蒂埃利·爱玛仕在巴黎创立了以自己姓氏为名的马具品牌,当时的马具当然是手工艺品。进入20世纪之后,大工业的批量生产席卷了人们的一切生活之时,手工的傲慢与意义,一点点地水落石出,它成了奢侈的必经之途。
沈然执著的同时,全世界都在为寻找这样手工艺人而烦恼,尤其是站在时尚产业尖端的人们。清华大学经管院教授李飞认为,“工艺对于奢侈品的重要,不仅在于传统,还在于皮具需要优秀的工匠,高级时装需要优秀的打版师,高级珠宝也离不开优秀的镶嵌师。”
20世纪20年代,巴黎有大约30万名手工工匠,绣工就有1万人。当高级定制让位于批量成衣,手工作坊工匠数目骤减,到新千年,巴黎的刺绣工只剩下不到200人。2002年香奈尔公司收购了著名的Lesage刺绣坊被,而总计收购了近十家家族式作坊的香奈尔公司也被公认为最聪明的角色。
中国看到了“复兴手工艺”的契机。2008、2009年中国国际时装周中,传统工艺受到多家服装品牌的推崇,NE·TIGER还特别推出“中国传统工艺与现代服饰”结合的主题。在NE·TIGER2009“国色天香华服大典”高级定制华服发布会上,总设计师张志峰携手两位古稀老人微笑出场,一位是曾为皇家制作龙袍的缂丝世家之第五代传人王嘉良,另一位是将几近失传的缂丝工艺再次复兴的缂丝大师王玉祥。
西方的奢侈品工业以家族传承的方式发展,但在中国,多数工艺的创造者,他们的技艺虽然通过师承的方式得到了延续和发展,但他们本人却隐没于“乾隆御制”或“江南织造”之中,没有被世人提升到其应有的艺术地位和产业地位,也没有形成个人的品牌和家族产业。当中国成为奢侈品消费大国,拥有的是沿海大规模的成衣制造工厂,和世界奢侈品品牌高级制造及高档原料采购大国的身份。
起点在1994年,以手制旗袍为卖点,中国第一个奢侈品牌 “上海滩”(Shanghai Tang)招揽了12位自20世纪初就以精湛缝纫手工而闻名的上海裁缝师傅。随着2005年11月上海滩第19家专卖店在日本东京开业,这个在香港出生的服装品牌,已经在全球13个国际大都市开设了专卖店,这其中包括时尚之都纽约、伦敦和巴黎。
2006年跨入成衣行业的玫瑰坊拥有300名绣工,而“东北虎”也拥有缂丝、苏绣、云锦等工艺,张志峰说,“中国的奢侈品牌要走向世界,在创造自我意识的同时,要有工艺,有文化,简单的抄袭和机械的模仿没有出路。”
奢侈品的精神印记
真正的奢侈品,背后一定有它的精神含量,这个精神含量对个人、对社会应该是有价值的
本刊记者/王家敏
一双鞋要结实舒适,一块钱很难达到,但是100块基本都能达到,但是当它卖到100万时跟舒适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在查达哈的《奢侈崇拜症》(The Cult of the Luxury Brand)一书中,这样的奢侈品消费被划分为5个发展阶段:镇压、金钱之始、炫耀、适应、生活方式。当今的日本,被归入“生活方式”一类,中国则被定位在第3个阶段——“炫耀”。
“一个普遍炫耀的奢侈品消费,说明存在一个普遍的、需要被尊重的人群。”复旦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孙时进认为,人们现在要做的,是找到奢侈品的精神价值。

精神的成长
10月,上海财经频道一个商务脱口秀栏目中,两个女孩展示自己创立的连锁酒店,竞争与汉庭酒店连锁创始人、董事长季琦一起午餐的机会。其中一位女孩自称“草根”,创立了求职青年旅舍,而另一位则是“富二代”,镜头不断切向她手上的香奈尔饰品,她开了一家精品酒店。
当主持人问季琦,“你也有女儿,会不会希望你的女儿也创业?”他回答,“不会,除非她愿意,因为创业很辛苦。”
“富二代”的女孩子当场就掉了眼泪。她说,从小到大,她的所有成功在别人眼里,原因都是自己是富二代,还长得漂亮,她想要通过创业证实自己的价值。“酒店都是我一砖一瓦从零到有创立起来的,我不停考察、学习、参加酒店峰会。我知道,我们富二代创业,就会承受更多社会和家里的压力。”
而在节目的最后,季琦问了“草根”女孩一个问题,“如果我给你年薪三十万,买你的创意,你到我的公司来工作如何?”她回答,“那你要让我把团队也带过来。”
季琦问“富二代”女孩,“你的酒店也不怎么赚钱,能不能1500万卖给我?”她回答,“我不愿意,我想把它做成我的事业,未来十年把我们的品牌打造出来。”
一开始倾向于“草根”女孩的评委们,最终选择了“富二代”。他们认为,“她在用心做商业,与人交流。”
“一个是为了生存,而另外一个人,则是希望证明自己的价值,我们对富二代的看法可能需要重新审视。”
“绝大部分人为了生存,很难想到自己的天职是成长。富二代已经不需要在物质这个层面上下功夫,他更多的精力可以放在怎么成长上,这对他来说就是天职。”
他们的精神成长,被通俗地称为附庸风雅,“这样的社会心理与他们的愿望大相径庭,”孙时进说,“实际上富人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与尊重。”
“就像那个富二代女孩一样,很少有人尊重她自身的努力,”孙时进说,或许长久以来,人们得到的尊重都太少了。当人们有了钱,就会花费很高的价格创造一种尊重。香奈尔,高级红酒,豪车豪宅,这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比如说茶叶、红酒,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品出其中滋味,一旦他长期用心品味,解读之后,就可能有助于他的人格成长。”
如果人们还没有钱,则普遍喜欢假冒的奢侈品,“这也说明国民普遍缺少被别人尊重,也并不尊重奢侈品背后的精神价值。”
“收养”工艺
同样,一个尊重奢侈品价值的社会,其背后的价值也能得到延续。一些商人更早发现了这一点。
不愿意透露名字的台北商人丘先生,跟一帮朋友在苏州挑选苏绣时,发现市面上的苏绣很一般。当他们深入了解当地情况后,发现苏绣艺术几乎快死亡了。丘先生很痛心,去探讨为什么?结果,丘先生发现,原因在于绣娘的报酬太低:“比如说一个绣卷,绣娘真正用心绣的话,恐怕要三四年的时间,在中国内地拿去卖,顶多也只卖几千块钱,没有人会用心绣。”
2006年,丘先生在苏州寻找了一批他们认为还有功底的绣娘,把她们的工作买断,“我说一年给你几万块钱的生活费,不要担心生活,你认真地去绣,然后我们再收购绣好的作品。”
丘先生认为,给他们的钱要够多,工艺师首先要有体面的生活。在奢侈品原产地欧洲,手工艺师是受人尊敬的职业。有270年生产历史的瑞士宝柏表(Blancpain),保持了几百年来只生产手工机械表的历史,江诗丹顿(Vacheron Constantin)至今保留着1755年招收手艺学徒的合同。在安特卫普,服装设计师是他们的骄傲,英国的瓷器工艺师则代代相传。
丘先生也得到了想要的工艺价值。他们最初的目的,只是作为一种欣赏品来收藏苏绣。而商人的思维使丘先生很快找到了其他的方式:如果这个东西的价格能在市场上得到承认,在赚钱的同时,还可以使中国的苏绣文化真正地流传下去。
他们将收购的绣品在各地展出,逐渐获得了市场,价格也比以往翻了数倍。“一个品牌绝不只是靠宣传、广告、策略,真正的奢侈品,背后一定有它的精神含量,这个精神含量对个人、对社会应该是有价值的。”孙时进认为,“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把商人看得很低下,那是因为没有真正的商人。商人就是通过市场,把真正好的东西卖出好价钱。幸运的工匠师与真正的商人合作,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理念,如果工匠只是想维持生活,你能想象他的作品理想会是怎么样?”
“但中国这样的商人还没有出来,或者说还不够。”孙时进说,“把工作作为一种理想,与长期的社会积累、经济发展有关,大部分商人还是停留在成为富人的思维上。”
布波族的升起
另一些人,则跳出了“富人-奢侈品”的思维逻辑,“布波族”(Bobos)就是例证。
2000年,美国专栏作家布鲁克斯写出了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布波族:一个社会新阶层的崛起》,“他们富裕却反对物质主义,用健康的法则而非道德的法则规范世俗欲望。遵循这些法则的人过着有纪律和自我节制的生活,但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他们的身体,而不是他们的灵魂。”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认为,布波族只是扔掉了一部分物质炫耀,但至少,一种不以物质为重心的时尚已经进入了精英阶层。

中国的布波族来得晚一些。他们基本由名牌大学制造,如果不是哈佛大学沃顿商学院的MBA,也起码是国内名校的EMBA。他们用实用主义的观点看待享乐,但必须与大众消费严格区分,长期使用同一个品牌,以昭显独特的品位。他们也可能对珠宝历史熟稔于心,或迷恋北京老城的胡同小店。
Ben算是其一。他在上海拥有几千万的豪宅,在北京也买下了昂贵地段的房产,在西南还拥有一套度假房。他的手腕上,始终是一块海鸥手表,他的车也是老牌的国产红旗车。
拼命追赶的人穿金戴银时,早富起来的Ben们则在水果蔬菜。“他们充分认识自己之后,不需要通过外在的物质手段来证实自己的社会地位。”孙时进认为,“他们才不会在乎别人看不出他昂贵衣服的价格,也不介意舒适豪车是不是贴上了晃眼的LOGO。”
如果“圈子”不再以财富来划分
——专访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
好的社会状态的一个特征是,社会中具有抵抗强权的力量,不管那强权是来自政治还是经济、商业、文化
本刊记者/王家敏
奢侈品消费在中国并不是舶来品。与此相反,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代表皇室荣耀的各种物品,无不精雕细刻并且因罕见而稀有昂贵。但奢侈品成为中国中产阶层的消费品,则时间并不长。与有阶层差异的社会相比,如今的商业社会,浸染了多少奢侈品的属性?这种属性在现代具备什么样的特性?《中国新闻周刊》为此专访了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郑也夫从事理论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和知识分子、消费主义问题研究多年。
奢侈品从来都有“区别性”
中国新闻周刊:有观点认为,奢侈品在封建时期,就是贵族的把玩和自我享受,并非“区别性物品”,因为他们无须再度证明自己。当奢侈品成为商品之后,则有了划分阶层的含义。这也是一些人把中国奢侈品消费定位在“炫耀”的原因?
郑也夫:这么说不准确。皇族一直在以种种手段建立与他人的“区别性”,对某种颜色、器物的垄断,住房建制的硬性规定,等等。炫耀是全人类,乃至全体动物的本能。
社会主义革命在上个世纪初期兴起后,人类企图造就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自然那是不可能实现的。反映在消费和奢侈品上,这种区别依然存在,甚至因为垄断而更彻底,社会效益更差。在前苏联,有专供高干消费的“小白桦树”商店,中国也同样。其最坏的负作用,就是“VIP方式”不进入公众消费领域,所以公众消费领域的质量低下得一塌糊涂。文化革命期间,高干子弟先是穿上了军装,别人没有,这就是搞“区别性”,后来索性穿上了“将校呢”,赤裸裸地炫耀。不错,那时因为商品匮乏,炫耀的手段贫乏。但决不是说那时没有了奢侈品和炫耀。那个时代也有人去高级餐馆,莫斯科餐厅,人们叫“老莫”,那种炫耀的得意,甚至高过今天的大吃大喝。
今天,虽然中国人的炫耀甚嚣尘上,但如果认为只有当今的中国人炫耀,那实在是太肤浅了。只能说,中国某些富人的炫耀更张扬、露骨、粗俗、赤裸裸一些。
中国新闻周刊:实际上,正是这些富人们也在引领着奢侈品消费文化?
郑也夫:中国的富人有钱有闲,但不是精神文化的领袖。因为历史原因,中国今天的富人多是暴发户,并且有一些是在极不干净的环境中暴发的,他们摆阔、铺张、不会过艺术化的生活。
要这些富人身心变得和谐一些,需要制度来制约,更需要他们自身慢慢提升。这需要并不短暂的时间,很多人一生都无力完成。如果中国社会能在下一代人中完成这一转换,就是福音。文化的作用还在其次,首先需要的是政治经济层面的公正,这要靠制度来保证。也就是说,首先要杜绝官商勾结,杜绝巧取豪夺。在富人身上,物质与精神的和谐的前提,是对财富的正确的认识:财富不是一切,挣钱不是全部。钱挣到很多的时候,个人的角色就变了,成为社会财富的看守者,成为一个特殊游戏的参与者。如果中国能完成这一转变,将是社会的巨大提升。
雷同在人类社会是乏味的
中国新闻周刊:消费不仅是人们的追逐,也是商人努力的结果。中国人的奢侈品消费热情,看上去更多的是消费社会或者说商人引领力量的来临?
郑也夫:消费社会的第一推动因素当然是商人。但是,商人不是无中生有,只是很好地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在1972年,美国社会学家埃文就说,“在今天谁是意识的领袖?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无冕之王;在今天西方世界中只有一个意识形态,就是消费,而他的领袖就是商人。”
如果把好生活作为人生观来吹捧,商人一定会成为话语权的垄断者。他们可以告诉你吃什么、穿什么、开什么车、住哪里,还能告诉你他们的商品有多少文化价值。他们一方面推动消费,另一方面营造消费为核心的人生观。造就了一个吃饱了饭就面临空虚的社会。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人们的消费与以往大不相同,凭借工业和全球化,大多数人得以温饱,但生存压力反而更大,追求创新与刺激超过了享受细节,这或许是数千年来人类所没有过的生存方式?
郑也夫:这样的生活方式就是时尚,人们全在时尚的笼罩下生活。多数人在不同程度上追逐时尚,人们的生活也被时尚牵着鼻子走,买车、买房、穿衣戴帽,都是如此。人们难以逃脱其外,成了房奴,车奴,不跟着走,好像就成了“等外品”、三等公民。
中国新闻周刊:这样的生存方式对“人”本身提出了挑战?
郑也夫:如果说对“人”有挑战,就是价值观上要彻底改观。但实际上对“人”并没有挑战,人还是追求“牛逼”,追求区别,这种本能是抹不掉的,雷同在人类社会都是乏味的。一些富人圈子是物质时代的产物,社会的进步在于圈子将不再以财富来划分。圈子没有等级是不行的,没有等级就没有文明,水准不等如何交流?只是以后的各种圈子将不再以“物”来划分,不再是通过房子、车子、钱,而是通过人自身的品质,智能、体能、技艺等等,未来的等级也应该是智力上的、技能上的、段位上的。这将是全社会共进的产物,是社会结构与观念共振的结果,不是哪个“精英阶层”可以独自挺进和到达的。
中国新闻周刊:当“物”越来越难以填补人们内心,商品也必然走向非物质化?
郑也夫:此前的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全面解决温饱,在那样的社会中,物质是炫耀的利器。当温饱解决了,空虚是大问题,甚至空虚就是温饱的副产品,如果继续以物质来炫耀,其一自己的身体承受不起,其二因工业带来的巨大复制能力,别人可以迅速拉平和你在某种商品占有上的差距,人们出于无奈,只好在物质之外寻找炫耀手段。
手工可以排除空虚,不是买手工制品,而是自己搞手工。身和心的关系很大,身体忙碌起来,心里就不空虚了。祖先是这样的,我们也只好这样。因为我们的身心和祖先其实没有差距。人们必须身心和祖先处于同一状态才舒适。
商业的民主化我们远远没有完成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确实有一部分人推崇“新手工”的生活方式,这种回归的社会原因是什么?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声音半个世纪不绝于耳,这样的回归恐怕也将经历数百年?
郑也夫:自制月饼、粽子、贺年卡,送给朋友要远比买来的商品恭敬、隆重。自己搞室内装修,既符合自己的要求,也可以实现自己创造潜能。在美国自己搞装修已经成为成年男性的游戏,美国已经兴起多年“Do It Yourself”,原因是耐人寻味的,回归手工的另一个本质原因,是对大规模生产不能造就“区别性”的厌倦。手工制品的个性当然突出,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我相信,手工制品和自制手工会回归得很快,因为后面有多重动力。
中国新闻周刊:无论消费还是文化,有更为广泛的人群共享这个成果才能是成功的。您认为这种商业意义上的民主化在中国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郑也夫:好的社会状态的一个特征是,社会中具有抵抗强权的力量,不管那强权是来自政治还是经济、商业、文化。其实商业的民主化我们远远没有完成,不过是以众多商人的格局代替了计划经济时代国家计委决定一切的格局。真正的经济民主化和商业民主化是,劳工与企业家的均衡,消费者与厂商的均衡,是前者有了充分的发言权。我们现在是后者在支配前者,在支配社会。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