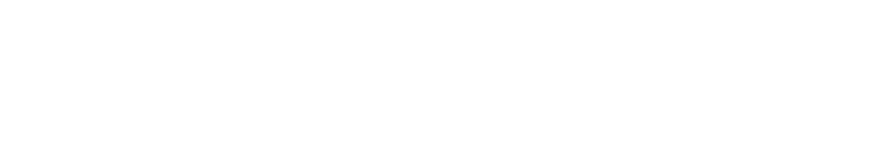|
|
|||||||||||||||||
简介:
 布雷维克 如何让你粉身碎骨
布雷维克 如何让你粉身碎骨2012年5月4日,布雷维克(左三)和律师利普斯德出现在法庭上。他们面前是一个塑胶人偶,用来向法庭展示布雷维克是在何地用何种方式实施他的杀人计划的。 (HEIKO JUNG/东方IC/图)
对于布雷维克,一个罪大恶极、声称代表自己的“文化、宗教和国家行事”,而剥夺了77条鲜活生命的杀人嫌犯,挪威法院表现了足够的冷静与审慎。事隔一年仍未作出终审判决。那么,过去一年中,挪威司法体系、挪威社会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煎熬呢?
身着黑色西装,打着金色领带,布雷维克把一只手插进口袋里,面无表情斜靠在座椅上。没有手铐,没有铁栏,只有两名律师分别坐在这个32岁的挪威男人两边。
这是一场审判。一场已经持续了十个星期的审判。
在这十个星期里,金发碧眼的漂亮女主控官让布雷维克深感困扰。她所代表的控方坚持她们饱受争议的决定:检控布雷维克患有精神疾病,因此他不必为恐怖袭击的罪行负刑事责任。
控方所说的恐怖袭击,被布雷维克自己描述为自己独立策划并完成的“二战以后欧洲最精心策划、规模最大的恐怖袭击”。
2011年7月22日,布雷维克先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的政府办公楼附近引爆炸弹;而后又伪装成警察,对于特岛上参加夏令营的年轻人开枪扫射。那些20岁上下的无辜年轻人,即使是投降、求饶也没让他们躲过子弹。共77人在两起惨案中丧生。
对布雷维克的审判也因此被称为“挪威自二战以来最重要的审判”。2012年4月16日案件开庭,挪威18个地方法院通过视频转播审判,可容纳2500人实时观看。超过1000个世界各地的记者为此赶到奥斯陆。
女主控官让布雷维克感到困扰的还包括她在十个星期中总是保持平和的语气,她总是用这样的开场开始每一次发问:“请问你,布雷维克先生……”
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大卫.布莱尔惊讶地发现,在这个法庭里,“没有严厉质问、揶揄嘲笑,甚至没有高声说话”,法庭外,“没有表达愤怒的集会”。他在自己博客里写道:“挪威的法庭表现了一个有尊严的社会所有的最大的忍耐和克制。”
审判开始当日,全世界的观众都通过电视转播看到了这样的画面:布雷维克一被解下手铐,获得自由的右手立即握拳挥向右上,做了一个“代表极右翼反抗精神”的敬礼。
没有人上前阻止他。在法官和主控官两位女士的带领下,法庭主要成员一一走上前来,用完全解除防备的姿态和他握手。布雷维克有些意外地以微笑回应。
一位法庭的公务人员在当天休庭后向记者表示:“既然他没有认罪,基于无罪假定,我们就应该给予他普通公民应享有的所有尊重”,尽管“将布雷维克当做普通人看待,让所有的法官和检控官都感到备受煎熬”。
“我们只能依法而行,”2012年6月21日,在最后陈词之后,主控官对记者说,“我知道,相对许多国家,挪威适用法律的方式非常仁慈,我们在722年之前就是这样的……也许别的国家觉得我们太过软弱,但这就是我们的选择。”
“如果为了一个人而改变规则,这就动摇了法治的核心”
对于挪威的法律人来说,审判从9个月前就开始了。
2011年7月23日,枪击案发生的次日清晨,律师盖尔.利普斯德接到了警察局打来的电话:这个刚刚自首的恐怖袭击者点名要自己担任辩护律师。
如果有什么可以代表布雷维克所憎恨的一切,那么盖尔恐怕“当之无愧”:他是挪威工党的一员,受过高等教育,信奉自由主义,对移民持宽容态度——这些态度代表了挪威社会的“主流”,却是布雷维克攻击的目标,他宣称自己“正在对欧洲的穆斯林发起战争”。
挪威从约40年以前开始接纳大量的移民。在今天的奥斯陆,30%以上的人口是第一或第二代移民。曾经在挪威访学的法律学者李红勃看来,如果一定要在安宁、富足、自由、文明的“欧洲乡村”挪威找到什么问题,那就是移民问题了,然而它既不构成什么社会矛盾,也远没有达到西欧等国的严重程度。
即便是欧洲的“新纳粹”观察者也承认,“挪威反对移民的极右势力只是一个非常小的社群”。布雷维克正是这边缘中的一员:他在网络论坛上激烈地抨击移民,在网络游戏里训练作战技术,宣称要“独力完成了二战以后欧洲最精心策划、规模最大的恐怖袭击”。
和善耐心的老律师盖尔对要不要接下这个“最艰难的任务”犹豫了几个小时,直到做护士的妻子对他说:“如果他受伤了,医生和护士也会全力救他。不管他是谁,我们都要尽自己的责任。”他终于说服了自己:为这个屠杀者“照看”他应有的权利,正是为了捍卫他所坚信的价值。
他对路透社记者解释自己当时的想法:“我们很容易说,他罪大恶极,不配享有人权。但是如果为了一个人而改变规则,这就动摇了法治的核心。”
在接下来的9个月中,警方对布雷维克进行了31次审讯,233个小时47分钟的录像、1000多页的案卷全部作为呈堂证供交给了法庭。利普斯德律师在整个调查开始前就位,并且由于布雷维克可能患有精神病,他可以比通常情况下“更深入地介入”,以保护被告的权利不受侵害。
警方调查的同时,两个法庭指定的精神病专家团队分别对布雷维克进行了鉴定。2011年11月,一份243页的报告发表,报告认为布雷维克在作案时处于精神错乱状态。基于这份报告的结论,2012年3月,公诉方对他提出“以强制精神病治疗代替为恐怖袭击罪行负责”的控诉。
然而就是距离审判开始不到20天的4月初,另一批法庭指定的精神病学专家在第二份报告中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布雷维克在作案时是理智的,尽管显现出“自恋和反社会的人格异常”。
面对两份相互矛盾的精神病学分析,秉持着“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原则,主控官伊恩没有在开庭时更改控诉,而是继续假定布雷维克患有精神病。这意味着一旦控诉成立,布雷维克将免于21年的牢狱之灾,在医院里度过余生。
同时,根据国家检控官托阿瑟.布什的书面指示,“一旦审判中呈现的完整证据显示布雷维克是理智的,控方保留提出21年监禁的权力”。
令外人有些难以理解的是,盖尔律师并没有接受控方的“疑点利益”,而是坚持称布雷维克在作案时是“完全清醒的”——因为对于布雷维克来说,被判定患有精神病比被判有罪更加耻辱。
盖尔律师充分尊重了他的这一意愿,在开庭时即向法庭提出:在挪威的法律之下,布雷维克有在法庭上做充分的自我陈述的权力,这“是一项基本的人权”,同时也是“证明布雷维克理智与否的最重要证据”。
“程序公正的基石是法官不带任何偏见地走进法庭”
审判一开始,两份相互矛盾的报告和布雷维克的陈述就一起摆在了5位法官面前。
在接下来的10周当中,他们还将一一聆听、质询每一个上台作证的目击者、警察、医生、政治极端主义者和政治领袖……要做出的判断却似乎非常简单:布雷维克到底是不是精神病患者。
这一次的5位法官不仅包括2位职业法官,也包括3位由普通公民担任的非职业法官,5位法官在法庭上的权力完全相同:在法庭上,他们坐在法官席的中央,和职业法官一样可以提问,并在做出判决时享有同样的话语权。
在挪威的法律人看来,犯罪不过是“生活中的非正常现象”。因此,只要司法体系公平地呈现了所有的证据,一个理性的普通公民就应该有能力依据常识判断被告是否有罪。挪威普通刑事案件采1+2式的法官组合,因为是此次“世纪大审判”,拓展到了2+3组合。
在审判的第二天,其中一位非职业法官就遭到了撤换,原因是一位挪威网民发现他2011年在Facebook曾发表过“布雷维克应被处以死刑”的言论。
“程序公正的基石是法官不带任何偏见地走进法庭,即便是公民担任法官也不能例外。”曾在挪威访学的外交学院国际法系李红勃老师这样解释法庭的决定。
在全国瞩目之下,法官们罕见地允许电视台对审判进行部分转播。既要“公开透明的审判”,又要防止法庭成为布雷维克极端政治思想的宣讲台,法庭对媒体报道作出了细致的规定。
国家电视台NRK在法庭的所有关键位置都安装了摄像头,授权录制审判的全部过程。这份完整的录像带将会被保存在国家档案馆,25年不得解封。公众只能通过电视转播,看到开庭、休庭和检控官、律师的全部发言。
挪威本土销量最大的报纸《戴格布拉特》在自己的网站上设置了一个按钮,读者只要一按按钮,所有关于布雷维克审判的报道都会消失。在这个按钮上,简短的文字提醒着:关于审判的报道可能会带来身体不适,也可能包含宣传布雷维克政治思想的内容。
尽管如此,全世界的读者还是通过报纸、新闻网站和记者们的博客读到了法庭上的故事。开庭的第二天,布雷维克向法庭做了长达65分钟的自我陈述。在被超时打断4次之后,法庭还是允许这个男人读完了20页的陈述。布雷维克放下手稿,直直望向法官:“我为保卫我的文化和人民而战,因此请求无罪。”这一陈述的具体内容没有获准发表在媒体上。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由主控官英格.伊恩对布雷维克进行盘问。这个梳着整齐的金色短发的女检控官在法庭上保持着不变的彬彬有礼的态度。
“我对所有的被告都友好地提问,这样他们会愿意说得更多。”伊恩说。奥斯陆公诉办公室的负责人强.曼奴德特别为这场审判挑选了伊恩,因为她不仅能力超群,并且“对于提问有精准的把握”。
这个41岁的女检察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当警察第一次带着伊恩来到枪击案的发生地于特岛,她感到“前所未有的糟糕”。接下来9个月里,每一页审讯记录都让她“难以承受”。然而在审判中,她为自己定下的原则是“距离感”:“我必须不加感情地处理每一个工作环节,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你去伦敦的时候,确实穿了西装和红手套吗?”
——“不,那只是一种夸张。”
——“去除夸张,你刚才的陈述还有哪些部分是真实的?你真的去过伦敦吗?”
咄咄逼人的问题,用几乎不变的温和语气问出,盘问的第二天,伊恩就让布雷维克红了脸,他不得不承认自己之前说的精神领袖不过是幻想出来的斗士,事实上他们只在“网上谈兵”而已。继续问下去,布雷维克更多以“不做评论”回应。
“这至少说明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10周的审判中,属于布雷维克的陈述和接受盘问时间是5天,而在后来的9周里,控方还将传召警方、法医、目击者、幸存者、布雷维克的朋友和亲人一一作供。
审判的第20天,布雷维克在被告席上接受了幸存者英格韦德.斯坦瑞德的直视。这也是他在枪击案之后第一次看到这个聪明的17岁女孩——她一动不动藏在尸体中间,躲过了自己的枪击,而后又用尸体中捡到的电话,招来了警察和救援队伍。
这个女孩在庭上指出了布雷维克拒绝承认的事实:他在用枪扫射时,一直欢呼叫喊,听上去像是“战士的声音”。面对辩方律师利普斯德的质疑,她坚持自己的记忆。
目击者和幸存者们的回忆把人们一次次地再次带回枪击案的当天:一名目击者记得,布雷维克当天穿着警察制服,保安为他找来了渡船,船长看到他带着一口大箱子——箱子里装满了后来杀人的武器;一名幸存者则描述了布雷维克是如何在下船之后“平静地拿出枪开始扫射”。
平静,是这个男人的一张脸。在庭上,他同样面无表情地说:在对头两个受害者开枪之前,“脑子里有100个声音告诉我不要这样做”。但是他依然扣下了扳机。在那天出门前,他吃了自己特别调配的兴奋剂,来“让大脑吸收更多氧气”,从而加倍地疯狂和麻木。
幸存者英格接下来细致地讲述了自己是如何尸体中找到电话,拨通紧急号码:“电话的主人已经死了,我是英格……”没多久,她在颤抖中听到房间里此起彼伏的电话声,随后,警察就来了。
站在法庭上对英格来说绝非易事。直到审判前,她依然不敢待在人群中或是广场上,一旦身处其中就感到“极度的恐惧”。“我只是觉得在法庭上说出一切是我必须要做的事。”英格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对于死难者家属和幸存者来说,这场审判是他们等待已久的煎熬。长达10周的审判中,法庭预留了190个座位给遇难者家属和幸存者,他们有权全程聆听包括布雷维克在内所有证人的证词,观看呈现给法庭的全部证据。
受害者家属唐德.布莱德曼从开庭起就坐在距离布莱维克几米之遥的地方,法庭中“发生的一切都让他难受”,他努力盯着布莱维克的脸看,当他发现这个杀手对死难者“没有流露出一丝同情,却在观看自己制作的(宣传极右思想)视频时掉了泪”,他说:“我不想说这深深刺激了我,但这至少说明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法庭的任务完成后,英格告诉每一个人,自己的生活从此以后再和布雷维克没有任何关系。上庭后的第8天,她和朋友们去野营。在Facebook上发布的照片里,她和人群躺在广场的草坪上,脸上挂着和挪威的阳光一样珍贵的微笑。
法庭之上,进行着残酷的控诉和供述,而在法庭之外,挪威人用独特的方式展现了对审判的态度:2012年4月26日上午,近40000人在细雨中进行了一场音乐游行。人们撑着伞,唱着童谣《彩虹下的孩子》走向法院,手里拿着红色的玫瑰花,歌声中可以听见轻轻的抽泣。
每15个奥斯陆人就有1个参与了4月26日的这场游行,同样的音乐游行在全国的许多其他市镇展开。在枪击案后,童谣中有一句歌词:你难道不知道/杀不完那些不相信的人/通往自由的道路没有捷径。
在法庭上,如果有一个人注定无法逃避面对所有残酷的事实,那这个人就是布雷维克。除了两次应证人要求进入转播室回避,在电视机前观看作证之外,布雷维克一直保持着几乎不变的姿势,面无表情地坐在被告席上,听死难者的名单、看爆炸现场的视频、面对每一个遇难者家属和幸存者的作证,甚至一一面对他们直视的眼睛。
2012年5月24日,在所有的幸存者都完成了证供之后,布雷维克第一次对“不认罪”的立场有了松动:只要法庭承认自己是理智的,他就不会对有罪的判决提出上诉。这个无动于衷的男人甚至第一次说出了心里感受:“在听了这么多的证词之后,我几乎快要精神崩溃了。”
审判还在继续。
“将政治极端主义当做一种病,这是非常危险的”
2012年6月13日,精神病医学专家哈斯比和塞黑姆一起坐上了证人席。他们决定一起作证,并肩接受质询。2011年11月他们做出的精神病学分析报告诊断布雷维克为精神病人,无法为他的屠杀罪行负责。尽管审判同期的民调显示,3/4的挪威人都希望布雷维克被判有罪,在法庭上,哈斯比和塞黑姆坚持自己原先的诊断。
包括他们在内,法庭在审判的最后10天里,共传唤了17位精神病专家对布雷维克的精神状况作出诊断。布雷维克的妈妈也被要求出庭作证。此前,她向法庭请求,不希望在庭上聊儿子的童年。法官驳回了这个请求,但同时要求媒体不得报道关于母亲证词的任何细节。
哈斯比和塞黑姆并肩坐在证人席上,就像他们当初初次面对布雷维克的时候一样,他们选择直接和他交谈,而不是躲在玻璃墙之后。同时,他们也承认“两个人在一起让他们感觉更安全”。布雷维克在早先的自述中说,两位精神病专家在枪击案之后非常短的时间里就见了他,以至于“他们自己都被吓得要死”。
哈斯比和塞黑姆一共对布雷维克进行了13次面对面的长谈,并在枪击案5个月之后做出了一份长达243页的分析报告。这份报告得到了权威的挪威法医协会的认可。在投票表决对报告的意见之前,理事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单独阅读了整份报告。最终,7位成员不但一致认为报告在方法、步骤上正确,并同意诊断布雷维克在作案时“精神错乱”。
理解布雷维克的精神状态,不仅仅关系着他是否被判有罪——如果他是理智的,那么他的想法从何而来?“我们不仅要检验布雷维克是否是一个精神病人,还要让人们了解,他从哪里来,他所相信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在开庭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控方发言人说。
极右翼组织前领袖、右翼刊物主编、工党领袖……这些与案件不直接相关的政治人物也一一出庭,他们的证词帮助法庭更好地理解了布雷维克:他在网络论坛上激烈地辩论移民问题,在网络游戏中练习作战技术。尽管他宣称“独力完成了二战以后欧洲最精心策划、规模最大的恐怖袭击”,他的世界观却并不孤独——前“挪威保卫联盟”领袖罗尼.阿特直言不讳:“现在还有一小群人完全支持布雷维克的所有行为。”
法庭还传召了宗教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哲学家,来解释“人如何能理智地拥有极端思想,做出极端行为”。当被心理学家质疑“你认为是什么使得人越过(理智的)界限,做出法西斯式的行为呢?”宗教历史学家安伯兰德说:“不不不,在历史学家看来,这些行为就是界限本身。”
哲学家欧夫任特承认“能够让一个患有精神病的屠杀者免除罪责是一种巨大的进步”,然而“人是有可能自以为在做好事,却做出了邪恶的行为”。他总结道:“将政治极端主义当做一种病,这是非常危险的。”
2012年6月21日,审判进入结案陈词阶段。在法庭上,布雷维克的精神状态始终无法得出一个定论,然而对于公诉方来说,决定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能确定布雷维克患有精神疾病,但我们对此合理存疑,”公诉人说,“只要无法排除布雷维克在精神错乱状态下犯下罪行的可能性,他就不能被判有罪。”
布雷维克带着一丝嘲讽的微笑听完了检控官的结案陈词,在审判的最后一天,他还获得了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他选择再次阐述自己的政治思想。在他慷慨陈词的同时,死难者的家属静静地走出了法庭。
布雷维克的辩护律师盖尔也在他之后做了一番精彩的发言:“他态度极端,缺乏同情心,但暴力并不是驱使他杀人的动机,他明知不义还要去杀人,为了自以为对的目标不择手段,这就是恐怖主义的价值观。”
这场审判显然也让盖尔这个挪威“最主流的律师”学到了很多,6月22日休庭之后,他对记者说:“我们获得了一个版本的事实,但还有更多的东西没有显现出来:我们还没看到右翼极端主义的本质,我们的记者和社会应该努力挖掘,搞清楚欧洲正在发生什么。”
对于布雷维克的判决,挪威法庭将在2012年8月24日宣布。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