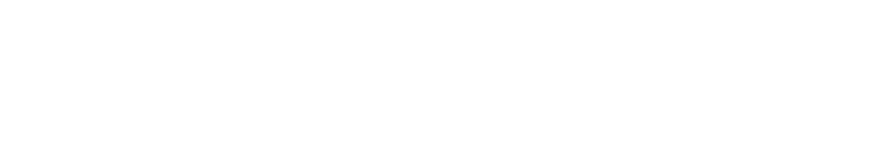李巧钰律师 雨后的彩虹或瞬间即逝
|
|
|||||||||||||||||
简介:
李巧钰律师 雨后的彩虹或瞬间即逝

—— 难以缝合:“保姆偷子案”背后的爱与失
但这份热情没有持续太久,刘金心觉得生母对自己有点“冷”,微信聊天时,有时会不回消息,有时是一个“哦”,还有时她会打电话过来,长篇大论地说教,告诉他“一定要好好工作,过正常的生活。”
新京报记者 王双兴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柳宝庆
刘金心想象中的认亲场景,像电视里演的那样,双方抱头痛哭,涕泪横流。
现实是另一番模样。2018年2月6日,刘金心迈进派出所会议室的门,生母朱晓娟坐在人群里,对视,母子二人都扯出有点尴尬的笑。她说,过来坐,他点头。26年前,刘金心被保姆偷走,杳无音讯;几年后,河南高院出具的一张错误的亲子鉴定为朱晓娟送回一个“假儿子”。两人的生活按照被修改的轨迹向前,又在26年后被再次打乱:保姆将刘金心送了回来。
消失的26年,在母子之间留下了难以缝合的伤口,相认至今的一年半时间里,他们互相靠拢、试探,又掺杂着失望、自卑、敏感和刻意疏远。
母子
刘金心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前不久,他辞掉了南充的工作,来到成都,准备和表哥一起开火锅店。生母朱晓娟不知道这个消息,电话里,儿子轻描淡写:“上一份辞了,现在在成都,餐馆里打工。先不说了,和朋友吃火锅。”
她不信,“真去餐馆打工的话,晚饭时间正是忙的时候,怎么可能有空去和朋友吃火锅呢?你说他是不是在撒谎?”在朱晓娟印象里,光是2018年,刘金心就换过好几份工作,每次都是工作个把月就回家待着,“游手好闲”。在刘金心看来,那段时间是他的调整期,生活的变故接二连三,心态不稳定,经常要靠酒精麻痹自己,“一沾酒就停不下来,必须把自己灌趴了。”随之而来的是胃穿孔和胃出血。
朱晓娟知道他酗酒的习惯,以至于挂掉电话后猜测:他说不定还在南充,辞了职混日子呢。事实上,二百多公里外的成都,刘金心和表哥正在筹备新开的火锅店,在开业前,他们要把同一条商业街上所有竞争对手的店都尝一遍,然后开始打有准备的仗。
在“第一步还没踏出去,能不能成功还说不定”的阶段,他不打算和朱晓娟多说。店铺装修、前期宣传、联系供货商,至少得忙一阵子。6月14日下午,几位股东从广东来成都,看门店,聊规划,刘金心回到住处已经将近凌晨。
他如今很少主动和家人联系,“说实话,我现在很难相信任何人,我生母、我养母、我身边的朋友,都得防着。”28岁的男生从淡蓝色盒子里抽出一根芙蓉王,深吸一口,然后趴在窗台上,一点一点吐出去。
和生母朱晓娟上一次见面还是春节的时候。偶尔两个人会通电话,但往往是母亲说,儿子听。“你不要好高骛远,要好好工作,你是个男人,最起码要养活自己,没有人能养你一辈子。”
“嗯。”
“你不要总是沉浸在过去的阴影里,别人拉你,你要爬。”
“晓得了。”
后来朱晓娟不怎么说了,怕他烦;刘金心坦言,确实烦。和养母何小平的联系也不多。来成都前,他和养母都生活在南充,住所只相距五六公里,但他严格把控频率,每隔一两个月回去一次。“时间长了不回去不太好,太频繁了也不合适。”刘金心说,成长环境甚至整个人生都被改变了,不恨是不可能的。
何小平的家,在南充市区一个菜市场旁,老式居民楼的护栏上挂着尚未晾干的衣服,窗台上的盆景长得茂盛。邻居说,她如今在一家茶馆工作,每天早出晚归,很少和其他居民打交道;小女儿已经结婚了,第二次婚姻遇到的丈夫比她年纪大,如今已经退休,而刘金心的身影,只是偶尔会出现在这里。
朱晓娟说,何小平如今处于“居住监视”期。去年认亲时,刘金心考虑到养母对他二十多年的养育,请求生母朱晓娟签了“免责书”。据媒体报道,如今重庆警方未立案。6月13日,记者见到了何小平,西南闷热,她穿了一条浅色连衣裙,撑着遮阳伞。说话时嗓门大,操着一口浓郁的南充方言。前不久,因为一句“毕竟我们两个人(她和朱晓娟)一个儿子,就当走亲戚吧”,她很快被卷入舆论浪潮,愤愤不平,于是表示“什么都不可能再说了”。
在刘金心的回忆中,他和养母“合不来,从小到大说的话都很少”,何小平脾气大,一言不合就会骂人、贬低人,很长一段时间里,刘金心甚至怀疑自己真的会像她说的那样,一事无成,这辈子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失而复得
明知道假设毫无意义,朱晓娟还是常常忍不住想:要是当年刘金心没有被偷走,两个人的生活都不至于是如今的境况。1992年,趁朱晓娟夫妇不在,家里的保姆偷走了一岁多的婴儿,在那之前,保姆的两个孩子都接连夭折,按照村里的迷信说法,她需要抱一个孩子回来“镇命”,才能在日后养活自己的孩子。她带着捡来的身份证去了劳务市场,应聘成为保姆,然后抱回了刘金心。
出事时,朱晓娟在上班,丈夫在出差。他责备她“没把孩子看好”,她反击他“还不是你找回来的保姆”,夫妻关系开始有了裂痕,它像炸弹一样埋在生活中,随时爆发。唯一容易达成共识的是找儿子。此后三年,朱晓娟夫妇四处奔走,打听孩子的下落,哪有线索就往哪去,前后跑了二十多个省份。
1995年,他们生下了小儿子,同一年冬天,在河南寻亲时得到消息,兰考县解救的一批被拐儿童中,有一个名叫盼盼的孩子,年龄和长相与朱晓娟夫妇丢失的儿子相近。朱晓娟夫妇通过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了亲子鉴定,如今那份两页纸的鉴定书已经变得破旧,在1996年1月15日的落款上方,一排小字写着结论:盼盼与朱晓娟夫妇有生物学亲子关系。
这个日后被证明并非亲生的儿子结束了朱晓娟夫妇的寻子行动。歉疚,加上失而复得的喜悦,让他们尽最大努力弥补盼盼。再也不敢请保姆,于是把小儿子送到奶奶家,夫妻俩全心照顾盼盼。
盼盼性格调皮,上课坐不住,下课爱惹事,朱晓娟就每天亲自接送,监督他写作业,课余时间让他学书法,磨合性子。七八岁的时候,盼盼开始喜欢唱歌,朱晓娟就带他到两路口的少年宫,报名了音乐培训班。后来觉得画画挺稀奇,于是在素描班和水彩班也报了名。十多岁的时候,盼盼看到班上有人学跆拳道,回家和妈妈说也想学,能锻炼身体也不错,朱晓娟同意了。
在月薪几百块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朱晓娟给盼盼买了一千多块的圆号和将近四千块的萨克斯,一对一的老师,课时费要50到80块,“就想着那几年他在外面受了很多罪,那些缺失能不能在其他方面给补上,所以他想学什么就支持他去学。”而送去奶奶家直到小学毕业才接回来的小儿子,从来没培养过什么业余爱好。
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如火如荼,迎接盼盼回家后,这个二孩家庭不得不承担几百元的罚款,盼盼爸爸原本在警备区担任干部,后来也被调任到地方,成了银行里的小职员。
小孩成长步履不停,家里开销越来越多,经济压力越来越重。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年代,盼盼爸爸借助在银行工作的便利,很早接触到了计算机,并且开始炒期货。
夫妻关系的裂痕越来越大,僵持几年后,以离婚告终,两个读中学的儿子由朱晓娟抚养。朱晓娟一边在医院工作,一边兼职卖保险赚外快,加上家人的接济,生活得以周转。两个儿子陆续大学毕业,一个在金融行业工作,一个在汽车公司做销售,朱晓娟觉得,自己“熬出来了”。
被偷走的26年
“假儿子”盼盼在还算优渥的环境里长大时,“真儿子”刘金心正在经历那段日后不太愿意回想的童年。被保姆偷走后,刘金心到了南充农村,保姆很快外出打工,把他交由养父照料。印象里,养父是一个脾气暴躁的男人,“打得啊……”刘金心皱着眉回忆,不再继续说了。
他向我演示了一个六七岁男孩的恐惧。挺直腰板,并拢双腿,垂着眼睛,手放在膝盖上,“只要听到他摩托车的声音,我就规规矩矩坐在客厅门边,不敢动。”那些年他被四处寄养,有时在姑姑家,有时在外婆家,也有时在舅公家,飘来飘去,但生活“还可以”,温饱能得到基本保障,亲戚在监督自家小孩写作业时“顺便管一下”刘金心,也是在那段时间,他学会了逃学、抽烟、上网吧、打游戏。
初二那年,刘金心打算辍学到长沙去找当时网恋的女朋友。“考虑清楚了,以后别后悔,也别怪我就行。”养母说。刘金心拿到了一张火车票和一张银行卡,开始打工。
女生在洗脚城工作,到长沙后,刘金心也开始学习足疗、保健。可能是缺少母爱的缘故,他在恋爱时尤其喜欢比自己年纪大的女孩子,“特别是十多岁的时候,找女朋友就要找小姐姐那种,说不清道不明,喜欢比自己大的、姐弟恋,觉得挺安全的。”刘金心说。
后来的日子里,刘金心去过江西,也回过四川;卖过眼镜,也在涂料店做过接待。在他右侧的锁骨上,蜿蜒着一条几厘米长的疤痕,那是在广西打工时留下的。当时,刘金心在下班回宿舍的路上,途经贩鱼的摊位,脚下一滑摔倒了。十几岁的男孩子没当回事,回宿舍躺到床上休息,没多久发现自己起不来了,伸手摸摔伤的锁骨,摔成两截的骨头已经错位了。
同事给老板打电话,刘金心被拉到医院做手术。再后来,工作黄了,他拿到一笔补偿金,打算回南充。临走前一晚,刘金心和朋友去网吧打游戏,困了蜷在沙发上睡觉,醒后发现钱不见了,连放在旁边的鞋也不见了。报警,警察建议去救助站;又打着赤脚到了救助站,和孤儿、流浪汉、智力残疾的人等等挤在一起,从柳州到武汉,再到贵阳、重庆,一站一站,二十多天后回到了南充。
许多年后,刘金心回重庆认亲,生母朱晓娟陪他逛解放碑、朝天门、七星岗。在刘金心离开的日子里,这座城市飞速发展,轻轨网络不断扩张,曾经的城郊、农村,也都立起了钢铁森林。小时候住过的警备区家属楼早就被拆迁,新的大厦笔直,那里成了整个重庆最繁华的地段。
“这些年来过重庆吗?”朱晓娟问。
“没。”想起曾经的落魄,刘金心没说。“旧的伤疤被撕开”按照既定的轨迹,刘金心会像许多人一样,打工、结婚、生子。转折发生在2017年。他和当时的女朋友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因为双方家长没有提前沟通充足,在定亲当天,许多琐碎的细节让女方家长不满,最终,8万元的彩礼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年7月,刘金心想着“长痛不如短痛”,和女朋友分了手。
那段时间,工作的地方换了“掌权的”,也不怎么顺心。刘金心干脆辞了职,待在家里酗酒。脑袋里胡思乱想,又不知道在想什么。时而后悔做出了分手的决定,过后又觉得那是必要的;时而担心自己的处境,过后又觉得想也没用。喝酒,睡觉,无所事事。没过多长时间,刘金心意识到自己“精神上面出现问题了”。
夜晚猫和老鼠发出声音,刘金心觉得是来害自己的;耳朵里出现幻听,经常有歌声,并且不受控制地自言自语;抱着酒瓶子躺在沙发上,越来越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时间久了,也觉得别人在戴着有色眼镜看自己,邻居是不是觉得我不行?继父是不是也看不起我?养母在客厅里和舅舅打电话,是不是在说我这也不好、那也不好?
刘金心崩溃了,去看精神科医生,抱回一堆治疗焦虑和抑郁的药。那段时间,刘金心很快从110多斤长胖到了130多斤,肚囊鼓起来,头发和胡须也无心打理,生活一片狼藉。
低谷期尚未走出来,第二重打击又紧接着来了。
养母瞒着他去了重庆,通过媒体寻找刘金心的亲生父母。起初的说法是“看了一档寻亲节目受了感动,想要赎罪”,后来的说法是以为过了二十年的刑事诉讼期不再受法律追究,再后来也曾在一档节目中如此阐述:“他没有事每天就睡在床上边耍电脑边喝酒,喝醉了就睡,大瓶子小瓶子到处都是……现在你肯定婚也没法结了,我也没法管你了,算了,我还是去给你找亲生父母。”
新闻当事人刘金心是通过看新闻得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新闻。朋友发来一个链接,里面讲述了一个曾经偷走小孩的保姆打算把小孩“还”给亲生父母,个人信息和照片翔实,刘金心就是那个曾经被偷走、现在被还回来的小孩。“找到亲生父母是好事,但是至少等我生活、心理各方面都好起来了,现在这种状态下……”他重新抱起酒瓶子,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瓶接一瓶。
没过多久,亲生母亲朱晓娟被找到了。不似其他寻亲成功的母亲一样激动,朱晓娟蒙了,和刘金心一样,难以接受。很久以前,朱晓娟成长在一个殷实的家庭中,她人长得漂亮,成绩好,被父母师长宠爱。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千军万马中过了独木桥,考上重庆医科大学,并且在毕业后进入医院,“是中级职称晋升最早的,领导很看重”。
但之后的日子,经历了结婚,丢子寻子;离婚,养子育子,从此和“母亲”这个身份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生活的重心,全都落在培养儿子身上;自我价值的实现,也全都寄托在儿子的成功上。“虽然放弃了我的事业,但是把两个小孩养大了,小孩也是我的成就;而且他们两个有出息了,实际上对我今后的生活来说也好。”于是放弃过出国的机会,经历过经济上的困窘,早早长出白发,用十多年的时间,将两个儿子送进大学,又送进职场。朱晓娟觉得,“终于熬出来了。”
没想到就在这时被告知,她付出很大精力和情感培养的儿子是“假”的,而“真儿子”,正在落魄不堪地过活。在采访中,朱晓娟讲起以前的生活,弯着眼睛,笑容可掬。小儿子打小聪慧,但偶尔贪玩调皮;大儿子憨一些,也更黏人,十几岁时还会跑去母亲房间睡,朱晓娟调侃:“你好不好意思,这么大的孩子了。”儿子撒娇:“睡一下嘛,我是你的取暖器。”
就像那间三居室里没有属于刘金心的房间一样,朱晓娟对孩子的称呼也被另外两个男孩子占满。和刘金心在一起,她叫他“心心”,和旁人提起,则是“那个刘金心”,同时出现的表情,往往是蹙眉。
如今,朱晓娟的大部分精力用在诉讼上。去年7月,她正式起诉河南高院,今年5月底,案件进入“证据交换及庭前调解”阶段。“旧的伤疤被撕开了,再撒一把盐。不对,应该说是再洒上酒精,疼得要命的。”这位曾经的医务工作者说,她希望河南高院为这些伤害负责,诉求是290余万元经济赔偿。
心有芥蒂
母子之间隔着消失的26年,血缘之亲也掺杂了尴尬和各怀心事的疏离。不过,认亲伊始,刘金心对亲生母亲还是存有期待,“不管是怎么样,这么多年没得过母爱什么之类的,对吧?有时候还是有点渴望的那种。对吧?平时不会表达出来,但是有时候还是心里会想。”
2018年2月,母子聚在一起过春节、逛街、买衣服。和生母走在一起,刘金心会主动挽着她的手,这是以前二十多年里,和养母从未有过的。聊天,多数时候是刘金心在说,讲自己这些年经历过的事、吃过的苦,“倾诉,像机关枪一样,啪啦啪啦地,全都扔出去了。”
回到南充后,两个人保持微信联系,每隔一段时间,朱晓娟的微信里就会收到刘金心发来的消息,字不多,常常是:妈,想你了。但这份热情没有持续太久,刘金心觉得生母对自己有点“冷”,微信聊天时,有时会不回消息,有时是一个“哦”,还有时她会打电话过来,长篇大论地说教,告诉他“一定要好好工作,过正常的生活”。
在生母的家中,刘金心见过“另一个自己”——曾经被错误亲子鉴定送回的男孩盼盼,他个子高,人长得帅气,“说一点都不自卑是不可能的,文化程度、从小受到的教育和培训,各方面综合起来,肯定是有差距的。”刘金心说。那次见面,朱晓娟的小儿子、刘金心的亲弟弟也在,三个男孩聚在一起,话不多,有一搭没一搭地随便聊聊,刘金心觉得尴尬。
寻亲目的,也一度是这段关系中的敏感词。在一次家庭聚餐时,外婆对三个男孩子说,你们都是我的外孙,以后结婚的时候,我都会表示表示。刘金心当场急了,为了这件事,还和朱晓娟吵了一架。朱晓娟觉得他不懂事,他觉得生母一家对他心有芥蒂:“好像我来认亲有什么别的目的似的。”事后又反思,可能那段时间自己确实太敏感了。
和房子相关的事也让刘金心头大。养母试图卖掉刘金心名下的房子。养母撺掇刘金心去打探生母的房产。生母因为这件事怀疑刘金心寻亲的初衷。生母嘱咐刘金心一定要守住养母买给他的那套房……
朱晓娟觉得,刘金心被保姆“养废了”,不爱工作,经常辞职,还酗酒、打游戏。“我们家没有像这样的人,两个小孩,包括孩子父亲,都是很勤快的人,但是他怎么回事?我感觉是保姆从小没有给他一个正常的家,像流浪汉一样在外面飘,飘到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就养成了那种不自律、游手好闲的性格。”
刘金心早就得知了生母的此类想法,他甚至有些后悔,不该在刚刚认亲时倾诉那么多,在他看来,如果当时少说一点,生母对他的轻视可能也少一点。后来,刘金心开始刻意与生母疏远。不再手牵手走路,很少发“想你了”,也尽量不去无所顾忌地倾诉,2018年,每到节假日会去重庆和家人团聚,但2019年以来,他开始主动降低联系的频率,上一次见面,还是春节的时候。
6月15日,记者和刘金心坐在成都东郊的咖啡馆里闲聊,电话响了,是生母那边的外婆。“晓得了,晓得了,我能上啥子当了?要得要得,好好。”挂掉电话,他表情夸张地说,这是今天打来的第三个电话了。
如今,不管是养母那边的家人,还是生母这边的亲戚,外婆是唯一和刘金心联系最多的。他回忆,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如今糖尿病、高血压,眼睛也不怎么看得见,本来身上就没有太多钱,春节时还是掏出了一千块交给刘金心。那次,他在外婆家看到她保留着他出生时医院给的小铜板,刻着1991年3月7日,是他的生辰。
“想到这些心里会舒服一点,至少还有人关心我。”刘金心说。去年,刘金心还会控制不住地酗酒,如今,他说自己“慢慢醒了”。“为自己也好,证明给别人看也好,先让工作有些起色。”
更长远的规划,可能还是会回到南充,“只有那栋房子是属于我的,其他什么都不是,属于自己的才是最真实的。”

—— 难以缝合:“保姆偷子案”背后的爱与失
但这份热情没有持续太久,刘金心觉得生母对自己有点“冷”,微信聊天时,有时会不回消息,有时是一个“哦”,还有时她会打电话过来,长篇大论地说教,告诉他“一定要好好工作,过正常的生活。”
新京报记者 王双兴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柳宝庆
刘金心想象中的认亲场景,像电视里演的那样,双方抱头痛哭,涕泪横流。
现实是另一番模样。2018年2月6日,刘金心迈进派出所会议室的门,生母朱晓娟坐在人群里,对视,母子二人都扯出有点尴尬的笑。她说,过来坐,他点头。26年前,刘金心被保姆偷走,杳无音讯;几年后,河南高院出具的一张错误的亲子鉴定为朱晓娟送回一个“假儿子”。两人的生活按照被修改的轨迹向前,又在26年后被再次打乱:保姆将刘金心送了回来。
消失的26年,在母子之间留下了难以缝合的伤口,相认至今的一年半时间里,他们互相靠拢、试探,又掺杂着失望、自卑、敏感和刻意疏远。
母子
刘金心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前不久,他辞掉了南充的工作,来到成都,准备和表哥一起开火锅店。生母朱晓娟不知道这个消息,电话里,儿子轻描淡写:“上一份辞了,现在在成都,餐馆里打工。先不说了,和朋友吃火锅。”
她不信,“真去餐馆打工的话,晚饭时间正是忙的时候,怎么可能有空去和朋友吃火锅呢?你说他是不是在撒谎?”在朱晓娟印象里,光是2018年,刘金心就换过好几份工作,每次都是工作个把月就回家待着,“游手好闲”。在刘金心看来,那段时间是他的调整期,生活的变故接二连三,心态不稳定,经常要靠酒精麻痹自己,“一沾酒就停不下来,必须把自己灌趴了。”随之而来的是胃穿孔和胃出血。
朱晓娟知道他酗酒的习惯,以至于挂掉电话后猜测:他说不定还在南充,辞了职混日子呢。事实上,二百多公里外的成都,刘金心和表哥正在筹备新开的火锅店,在开业前,他们要把同一条商业街上所有竞争对手的店都尝一遍,然后开始打有准备的仗。
在“第一步还没踏出去,能不能成功还说不定”的阶段,他不打算和朱晓娟多说。店铺装修、前期宣传、联系供货商,至少得忙一阵子。6月14日下午,几位股东从广东来成都,看门店,聊规划,刘金心回到住处已经将近凌晨。
他如今很少主动和家人联系,“说实话,我现在很难相信任何人,我生母、我养母、我身边的朋友,都得防着。”28岁的男生从淡蓝色盒子里抽出一根芙蓉王,深吸一口,然后趴在窗台上,一点一点吐出去。
和生母朱晓娟上一次见面还是春节的时候。偶尔两个人会通电话,但往往是母亲说,儿子听。“你不要好高骛远,要好好工作,你是个男人,最起码要养活自己,没有人能养你一辈子。”
“嗯。”
“你不要总是沉浸在过去的阴影里,别人拉你,你要爬。”
“晓得了。”
后来朱晓娟不怎么说了,怕他烦;刘金心坦言,确实烦。和养母何小平的联系也不多。来成都前,他和养母都生活在南充,住所只相距五六公里,但他严格把控频率,每隔一两个月回去一次。“时间长了不回去不太好,太频繁了也不合适。”刘金心说,成长环境甚至整个人生都被改变了,不恨是不可能的。
何小平的家,在南充市区一个菜市场旁,老式居民楼的护栏上挂着尚未晾干的衣服,窗台上的盆景长得茂盛。邻居说,她如今在一家茶馆工作,每天早出晚归,很少和其他居民打交道;小女儿已经结婚了,第二次婚姻遇到的丈夫比她年纪大,如今已经退休,而刘金心的身影,只是偶尔会出现在这里。
朱晓娟说,何小平如今处于“居住监视”期。去年认亲时,刘金心考虑到养母对他二十多年的养育,请求生母朱晓娟签了“免责书”。据媒体报道,如今重庆警方未立案。6月13日,记者见到了何小平,西南闷热,她穿了一条浅色连衣裙,撑着遮阳伞。说话时嗓门大,操着一口浓郁的南充方言。前不久,因为一句“毕竟我们两个人(她和朱晓娟)一个儿子,就当走亲戚吧”,她很快被卷入舆论浪潮,愤愤不平,于是表示“什么都不可能再说了”。
在刘金心的回忆中,他和养母“合不来,从小到大说的话都很少”,何小平脾气大,一言不合就会骂人、贬低人,很长一段时间里,刘金心甚至怀疑自己真的会像她说的那样,一事无成,这辈子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失而复得
明知道假设毫无意义,朱晓娟还是常常忍不住想:要是当年刘金心没有被偷走,两个人的生活都不至于是如今的境况。1992年,趁朱晓娟夫妇不在,家里的保姆偷走了一岁多的婴儿,在那之前,保姆的两个孩子都接连夭折,按照村里的迷信说法,她需要抱一个孩子回来“镇命”,才能在日后养活自己的孩子。她带着捡来的身份证去了劳务市场,应聘成为保姆,然后抱回了刘金心。
出事时,朱晓娟在上班,丈夫在出差。他责备她“没把孩子看好”,她反击他“还不是你找回来的保姆”,夫妻关系开始有了裂痕,它像炸弹一样埋在生活中,随时爆发。唯一容易达成共识的是找儿子。此后三年,朱晓娟夫妇四处奔走,打听孩子的下落,哪有线索就往哪去,前后跑了二十多个省份。
1995年,他们生下了小儿子,同一年冬天,在河南寻亲时得到消息,兰考县解救的一批被拐儿童中,有一个名叫盼盼的孩子,年龄和长相与朱晓娟夫妇丢失的儿子相近。朱晓娟夫妇通过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了亲子鉴定,如今那份两页纸的鉴定书已经变得破旧,在1996年1月15日的落款上方,一排小字写着结论:盼盼与朱晓娟夫妇有生物学亲子关系。
这个日后被证明并非亲生的儿子结束了朱晓娟夫妇的寻子行动。歉疚,加上失而复得的喜悦,让他们尽最大努力弥补盼盼。再也不敢请保姆,于是把小儿子送到奶奶家,夫妻俩全心照顾盼盼。
盼盼性格调皮,上课坐不住,下课爱惹事,朱晓娟就每天亲自接送,监督他写作业,课余时间让他学书法,磨合性子。七八岁的时候,盼盼开始喜欢唱歌,朱晓娟就带他到两路口的少年宫,报名了音乐培训班。后来觉得画画挺稀奇,于是在素描班和水彩班也报了名。十多岁的时候,盼盼看到班上有人学跆拳道,回家和妈妈说也想学,能锻炼身体也不错,朱晓娟同意了。
在月薪几百块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朱晓娟给盼盼买了一千多块的圆号和将近四千块的萨克斯,一对一的老师,课时费要50到80块,“就想着那几年他在外面受了很多罪,那些缺失能不能在其他方面给补上,所以他想学什么就支持他去学。”而送去奶奶家直到小学毕业才接回来的小儿子,从来没培养过什么业余爱好。
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如火如荼,迎接盼盼回家后,这个二孩家庭不得不承担几百元的罚款,盼盼爸爸原本在警备区担任干部,后来也被调任到地方,成了银行里的小职员。
小孩成长步履不停,家里开销越来越多,经济压力越来越重。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年代,盼盼爸爸借助在银行工作的便利,很早接触到了计算机,并且开始炒期货。
夫妻关系的裂痕越来越大,僵持几年后,以离婚告终,两个读中学的儿子由朱晓娟抚养。朱晓娟一边在医院工作,一边兼职卖保险赚外快,加上家人的接济,生活得以周转。两个儿子陆续大学毕业,一个在金融行业工作,一个在汽车公司做销售,朱晓娟觉得,自己“熬出来了”。
被偷走的26年
“假儿子”盼盼在还算优渥的环境里长大时,“真儿子”刘金心正在经历那段日后不太愿意回想的童年。被保姆偷走后,刘金心到了南充农村,保姆很快外出打工,把他交由养父照料。印象里,养父是一个脾气暴躁的男人,“打得啊……”刘金心皱着眉回忆,不再继续说了。
他向我演示了一个六七岁男孩的恐惧。挺直腰板,并拢双腿,垂着眼睛,手放在膝盖上,“只要听到他摩托车的声音,我就规规矩矩坐在客厅门边,不敢动。”那些年他被四处寄养,有时在姑姑家,有时在外婆家,也有时在舅公家,飘来飘去,但生活“还可以”,温饱能得到基本保障,亲戚在监督自家小孩写作业时“顺便管一下”刘金心,也是在那段时间,他学会了逃学、抽烟、上网吧、打游戏。
初二那年,刘金心打算辍学到长沙去找当时网恋的女朋友。“考虑清楚了,以后别后悔,也别怪我就行。”养母说。刘金心拿到了一张火车票和一张银行卡,开始打工。
女生在洗脚城工作,到长沙后,刘金心也开始学习足疗、保健。可能是缺少母爱的缘故,他在恋爱时尤其喜欢比自己年纪大的女孩子,“特别是十多岁的时候,找女朋友就要找小姐姐那种,说不清道不明,喜欢比自己大的、姐弟恋,觉得挺安全的。”刘金心说。
后来的日子里,刘金心去过江西,也回过四川;卖过眼镜,也在涂料店做过接待。在他右侧的锁骨上,蜿蜒着一条几厘米长的疤痕,那是在广西打工时留下的。当时,刘金心在下班回宿舍的路上,途经贩鱼的摊位,脚下一滑摔倒了。十几岁的男孩子没当回事,回宿舍躺到床上休息,没多久发现自己起不来了,伸手摸摔伤的锁骨,摔成两截的骨头已经错位了。
同事给老板打电话,刘金心被拉到医院做手术。再后来,工作黄了,他拿到一笔补偿金,打算回南充。临走前一晚,刘金心和朋友去网吧打游戏,困了蜷在沙发上睡觉,醒后发现钱不见了,连放在旁边的鞋也不见了。报警,警察建议去救助站;又打着赤脚到了救助站,和孤儿、流浪汉、智力残疾的人等等挤在一起,从柳州到武汉,再到贵阳、重庆,一站一站,二十多天后回到了南充。
许多年后,刘金心回重庆认亲,生母朱晓娟陪他逛解放碑、朝天门、七星岗。在刘金心离开的日子里,这座城市飞速发展,轻轨网络不断扩张,曾经的城郊、农村,也都立起了钢铁森林。小时候住过的警备区家属楼早就被拆迁,新的大厦笔直,那里成了整个重庆最繁华的地段。
“这些年来过重庆吗?”朱晓娟问。
“没。”想起曾经的落魄,刘金心没说。“旧的伤疤被撕开”按照既定的轨迹,刘金心会像许多人一样,打工、结婚、生子。转折发生在2017年。他和当时的女朋友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因为双方家长没有提前沟通充足,在定亲当天,许多琐碎的细节让女方家长不满,最终,8万元的彩礼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年7月,刘金心想着“长痛不如短痛”,和女朋友分了手。
那段时间,工作的地方换了“掌权的”,也不怎么顺心。刘金心干脆辞了职,待在家里酗酒。脑袋里胡思乱想,又不知道在想什么。时而后悔做出了分手的决定,过后又觉得那是必要的;时而担心自己的处境,过后又觉得想也没用。喝酒,睡觉,无所事事。没过多长时间,刘金心意识到自己“精神上面出现问题了”。
夜晚猫和老鼠发出声音,刘金心觉得是来害自己的;耳朵里出现幻听,经常有歌声,并且不受控制地自言自语;抱着酒瓶子躺在沙发上,越来越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时间久了,也觉得别人在戴着有色眼镜看自己,邻居是不是觉得我不行?继父是不是也看不起我?养母在客厅里和舅舅打电话,是不是在说我这也不好、那也不好?
刘金心崩溃了,去看精神科医生,抱回一堆治疗焦虑和抑郁的药。那段时间,刘金心很快从110多斤长胖到了130多斤,肚囊鼓起来,头发和胡须也无心打理,生活一片狼藉。
低谷期尚未走出来,第二重打击又紧接着来了。
养母瞒着他去了重庆,通过媒体寻找刘金心的亲生父母。起初的说法是“看了一档寻亲节目受了感动,想要赎罪”,后来的说法是以为过了二十年的刑事诉讼期不再受法律追究,再后来也曾在一档节目中如此阐述:“他没有事每天就睡在床上边耍电脑边喝酒,喝醉了就睡,大瓶子小瓶子到处都是……现在你肯定婚也没法结了,我也没法管你了,算了,我还是去给你找亲生父母。”
新闻当事人刘金心是通过看新闻得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新闻。朋友发来一个链接,里面讲述了一个曾经偷走小孩的保姆打算把小孩“还”给亲生父母,个人信息和照片翔实,刘金心就是那个曾经被偷走、现在被还回来的小孩。“找到亲生父母是好事,但是至少等我生活、心理各方面都好起来了,现在这种状态下……”他重新抱起酒瓶子,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瓶接一瓶。
没过多久,亲生母亲朱晓娟被找到了。不似其他寻亲成功的母亲一样激动,朱晓娟蒙了,和刘金心一样,难以接受。很久以前,朱晓娟成长在一个殷实的家庭中,她人长得漂亮,成绩好,被父母师长宠爱。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千军万马中过了独木桥,考上重庆医科大学,并且在毕业后进入医院,“是中级职称晋升最早的,领导很看重”。
但之后的日子,经历了结婚,丢子寻子;离婚,养子育子,从此和“母亲”这个身份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生活的重心,全都落在培养儿子身上;自我价值的实现,也全都寄托在儿子的成功上。“虽然放弃了我的事业,但是把两个小孩养大了,小孩也是我的成就;而且他们两个有出息了,实际上对我今后的生活来说也好。”于是放弃过出国的机会,经历过经济上的困窘,早早长出白发,用十多年的时间,将两个儿子送进大学,又送进职场。朱晓娟觉得,“终于熬出来了。”
没想到就在这时被告知,她付出很大精力和情感培养的儿子是“假”的,而“真儿子”,正在落魄不堪地过活。在采访中,朱晓娟讲起以前的生活,弯着眼睛,笑容可掬。小儿子打小聪慧,但偶尔贪玩调皮;大儿子憨一些,也更黏人,十几岁时还会跑去母亲房间睡,朱晓娟调侃:“你好不好意思,这么大的孩子了。”儿子撒娇:“睡一下嘛,我是你的取暖器。”
就像那间三居室里没有属于刘金心的房间一样,朱晓娟对孩子的称呼也被另外两个男孩子占满。和刘金心在一起,她叫他“心心”,和旁人提起,则是“那个刘金心”,同时出现的表情,往往是蹙眉。
如今,朱晓娟的大部分精力用在诉讼上。去年7月,她正式起诉河南高院,今年5月底,案件进入“证据交换及庭前调解”阶段。“旧的伤疤被撕开了,再撒一把盐。不对,应该说是再洒上酒精,疼得要命的。”这位曾经的医务工作者说,她希望河南高院为这些伤害负责,诉求是290余万元经济赔偿。
心有芥蒂
母子之间隔着消失的26年,血缘之亲也掺杂了尴尬和各怀心事的疏离。不过,认亲伊始,刘金心对亲生母亲还是存有期待,“不管是怎么样,这么多年没得过母爱什么之类的,对吧?有时候还是有点渴望的那种。对吧?平时不会表达出来,但是有时候还是心里会想。”
2018年2月,母子聚在一起过春节、逛街、买衣服。和生母走在一起,刘金心会主动挽着她的手,这是以前二十多年里,和养母从未有过的。聊天,多数时候是刘金心在说,讲自己这些年经历过的事、吃过的苦,“倾诉,像机关枪一样,啪啦啪啦地,全都扔出去了。”
回到南充后,两个人保持微信联系,每隔一段时间,朱晓娟的微信里就会收到刘金心发来的消息,字不多,常常是:妈,想你了。但这份热情没有持续太久,刘金心觉得生母对自己有点“冷”,微信聊天时,有时会不回消息,有时是一个“哦”,还有时她会打电话过来,长篇大论地说教,告诉他“一定要好好工作,过正常的生活”。
在生母的家中,刘金心见过“另一个自己”——曾经被错误亲子鉴定送回的男孩盼盼,他个子高,人长得帅气,“说一点都不自卑是不可能的,文化程度、从小受到的教育和培训,各方面综合起来,肯定是有差距的。”刘金心说。那次见面,朱晓娟的小儿子、刘金心的亲弟弟也在,三个男孩聚在一起,话不多,有一搭没一搭地随便聊聊,刘金心觉得尴尬。
寻亲目的,也一度是这段关系中的敏感词。在一次家庭聚餐时,外婆对三个男孩子说,你们都是我的外孙,以后结婚的时候,我都会表示表示。刘金心当场急了,为了这件事,还和朱晓娟吵了一架。朱晓娟觉得他不懂事,他觉得生母一家对他心有芥蒂:“好像我来认亲有什么别的目的似的。”事后又反思,可能那段时间自己确实太敏感了。
和房子相关的事也让刘金心头大。养母试图卖掉刘金心名下的房子。养母撺掇刘金心去打探生母的房产。生母因为这件事怀疑刘金心寻亲的初衷。生母嘱咐刘金心一定要守住养母买给他的那套房……
朱晓娟觉得,刘金心被保姆“养废了”,不爱工作,经常辞职,还酗酒、打游戏。“我们家没有像这样的人,两个小孩,包括孩子父亲,都是很勤快的人,但是他怎么回事?我感觉是保姆从小没有给他一个正常的家,像流浪汉一样在外面飘,飘到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就养成了那种不自律、游手好闲的性格。”
刘金心早就得知了生母的此类想法,他甚至有些后悔,不该在刚刚认亲时倾诉那么多,在他看来,如果当时少说一点,生母对他的轻视可能也少一点。后来,刘金心开始刻意与生母疏远。不再手牵手走路,很少发“想你了”,也尽量不去无所顾忌地倾诉,2018年,每到节假日会去重庆和家人团聚,但2019年以来,他开始主动降低联系的频率,上一次见面,还是春节的时候。
6月15日,记者和刘金心坐在成都东郊的咖啡馆里闲聊,电话响了,是生母那边的外婆。“晓得了,晓得了,我能上啥子当了?要得要得,好好。”挂掉电话,他表情夸张地说,这是今天打来的第三个电话了。
如今,不管是养母那边的家人,还是生母这边的亲戚,外婆是唯一和刘金心联系最多的。他回忆,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如今糖尿病、高血压,眼睛也不怎么看得见,本来身上就没有太多钱,春节时还是掏出了一千块交给刘金心。那次,他在外婆家看到她保留着他出生时医院给的小铜板,刻着1991年3月7日,是他的生辰。
“想到这些心里会舒服一点,至少还有人关心我。”刘金心说。去年,刘金心还会控制不住地酗酒,如今,他说自己“慢慢醒了”。“为自己也好,证明给别人看也好,先让工作有些起色。”
更长远的规划,可能还是会回到南充,“只有那栋房子是属于我的,其他什么都不是,属于自己的才是最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