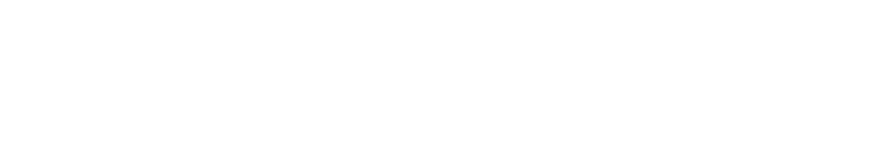记住:那个年代的杨沫与青春之歌
|
|
|||||||||||||||||
简介:
记住:那个年代的杨沫与青春之歌
1958年1月1日,《北京日报》的“新书介绍”栏内,登出了《青春之歌》即将出版的消息,并于1月3日起开始连载《青春之歌》,这是这部小说第一次在媒体上露脸。
这一年杨沫已经44岁了,是北影厂的一名编剧,《青春之歌》却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鬼在《母亲杨沫》一书中曾经回忆,因为这部小说,杨沫还在厂里挨了批评,在1月31日的动员大会上,厂领导点名说:杨沫同志几年没有写成一个剧本,可是却写了一部40万字的小说……

这样的批评让杨沫觉得很是冤枉,她还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在北影厂,以正视听。她强调小说是在1951和1952年两年写就,自己是1952年11月17日才来到剧本创作所工作,此后也不过只用了养病期间的3个月对小说进行修改。
事实上,这部小说的草稿的确在1954年已经交到出版社,却一直在中青和作家两个出版社“滚”了3年多,其出版过程可谓一波三折。著名编辑家、文学评论家江晓天在2007年接受的一次采访中,也提到了很多这部小说出版的细节,他说,最早注意到这部小说的人是中青社的编辑萧也牧,他在一次与柳溪的交谈中得知杨沫刚写完一部叫《烧不尽的野火》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描写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道静如何走上革命道路,并成为无产阶级战士的曲折过程。在看过稿子后,萧也牧建议杨沫把小说名字改为《青春之歌》。
但是这部稿子在中青社却一直没能成书,1956年1月26日,“左联”时期的老作家欧阳凡海把帮忙审读稿子后的意见反馈给了出版社,他一共列出了33条意见,仅有3条是优点,其余30条都是缺点,而最大的缺点就是:“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林道静作为书中最重的主人公、中心人物和小说的中心线索。而对于林道静却缺乏足够的批判和分析。”

1958年塔什干亚非作家会议,途经莫斯科胖一点的是杨沫
杨沫起初还是很尊重欧阳凡海的意见的,她在日记中表示,要下决心改好小说,想多酝酿一下,准备好再执笔。但其实从中青社的编辑到杨沫本人都明白,若是按照欧阳凡海的意见修改,几乎就是另写一部作品。
1956年春,杨沫又把稿子给了时任《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的秦兆阳。过了些天,秦兆阳来了电话,说稿子看过了,挺好,没什么大毛病,他已经把稿子转给了作家出版社。5月底,责任编辑任大心告诉杨沫,只需对个别的一两处地方做些修改即可出版,因为要落实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杨沫心里也很清楚,出版社此时之所以对《青春之歌》大放绿灯,其主要的原因是赶上了政治气候的“清朗”时期。正如她在6月28日的日记中所说:“看起来,什么都是一阵风。现在是赶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机上了,否则这小说的命运还不知如何呢?”
在小说正式出版后的1958年3月,杨沫开始收到一些群众来信。4月1日,文化部电影局局长王阑西托人带信给杨沫,称写40万字的小说,并不比写剧本容易,也是对党的贡献,以此安抚她,不要介意北影厂的批评。4月23日,海默写信给杨沫称,周扬在几天前召开的文学评论工作会上说,最近有三部好作品出现,分别是《林海雪原》、《红旗谱》和《青春之歌》。
读者的来信越来越多,询问最多的是林道静、卢嘉川这些书中人物是否还活着。到6月份,《青春之歌》已经出版了39万册。
杨沫开始忙活起来,电话和拜访者络绎不绝。1958年10月4日,杨沫随中国作家代表团来到塔什干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团长茅盾,副团长是周扬和巴金,季羡林、刘白羽等人为团员,其中女作家只有许广平、谢冰心和杨沫三人。
然而,批评声也再次袭来,1959年《中国青年》的第2期发表了北京电子管厂工人郭开的《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一文,文中批评《青春之歌》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没有很好的描写工农群众,没有认真地实际地描写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这是第一篇尖锐批评这部小说的长篇文章,并由此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大讨论。
杨沫和她最后一个老伴李蕴昌,两位老人在晚年相濡以沫,对杨沫的精神状况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
此后,郭开又发表了《就<青春之歌>谈文艺创作和批评中的几个原则问题》一文,再次表示,林道静不是共产党员的典型。从当时的文章还有读者来信来看,批评意见还是少数,多数人并不赞成郭开的观点。在此背景下,茅盾在《中国青年》上撰文,肯定了《青春之歌》是一部有一定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
不过郭开的部分意见后来也被杨沫采纳,她又花了3个月的时间对《青春之歌》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增加了林道静身上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批判。这样的修改被一些人认为是有迎合政治口号的嫌疑。
在1991年6月新版《青春之歌》出版的后记中,杨沫再次回忆了作品引起的各种争议,她说“他们的看法都各有道理,我呢,也有我的道理。我推崇现实主义创作法则,我的生活经历,我的信仰决定了我的爱与憎,也决定了我喜欢写什么,不喜欢写什么。”
回顾《青春之歌》最受关注的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几乎是当时革命历史教育的准教材,有口皆碑的是“三红一创”和“山青保林”八部,前四部是《红日》、《红旗谱》、《红岩》、《创业史》,后四部是《山乡巨变》、《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在毛泽东提倡文艺“为工农兵而创作和利用”的年代,这八部长篇小说中,唯有《青春之歌》的主人公是知识分子。
但这并不表示《青春之歌》不是一本革命历史小说,毕竟书中从一个侧面反映“九·一八”事变后,“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来龙去脉,而她在当年一纸风行的主要原因,大概也是因为唤起了整整一代人的浪漫情操。不可否认的是,《青春之歌》的影响是空前的,截至1990年,本书累计发行500万册,被翻译成18种文字,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反映革命题材的共和国经典长篇小说。
伴随着《青春之歌》一起流行起来的还有这样两句话:“人在痛苦的时候,是最容易回忆往事的。”以及“迷人的爱情幻成的绚丽虹彩,随着时间渐渐褪去了它美丽的颜色。”直到今天,很多人在写作时仍然喜欢引用之。
我们还有必要再回过头看一看当初杨沫创作《青春之歌》时的背景,50年代杨沫的身体很不好,尽管很多朋友都说杨沫心宽坦荡,想得开,但实际上翻开那时她的日记,大都是再写她患病的感受和对疾病的忧虑。在日记里,她多次提到了自己的痛苦,包括了病休不能工作的痛苦;被丈夫冷落的痛苦;睡不好觉的痛苦;三十多岁就大把掉发的痛苦;怀疑自己得了肝癌的痛苦……
在疾病缠身时,当年在冀中的抗日生活碎片和不少牺牲老战友的影像再次浮现,1951年6月9日,杨沫在日记中写道“我有时忽然想,身体总是不好,干脆来个灯尽油干,尽所有力量写出那长篇小说来,然后死了就死了……”9月25日,她草拟了全书提纲,最初的名字叫《千锤百炼》,后改为《烧不尽的野火》。
多年后,儿子老鬼在《母亲杨沫》一书中写道:“如果她身体健康,正常上班工作,终日快快乐乐,仕途顺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958年1月1日,《北京日报》的“新书介绍”栏内,登出了《青春之歌》即将出版的消息,并于1月3日起开始连载《青春之歌》,这是这部小说第一次在媒体上露脸。
这一年杨沫已经44岁了,是北影厂的一名编剧,《青春之歌》却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鬼在《母亲杨沫》一书中曾经回忆,因为这部小说,杨沫还在厂里挨了批评,在1月31日的动员大会上,厂领导点名说:杨沫同志几年没有写成一个剧本,可是却写了一部40万字的小说……

这样的批评让杨沫觉得很是冤枉,她还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在北影厂,以正视听。她强调小说是在1951和1952年两年写就,自己是1952年11月17日才来到剧本创作所工作,此后也不过只用了养病期间的3个月对小说进行修改。
事实上,这部小说的草稿的确在1954年已经交到出版社,却一直在中青和作家两个出版社“滚”了3年多,其出版过程可谓一波三折。著名编辑家、文学评论家江晓天在2007年接受的一次采访中,也提到了很多这部小说出版的细节,他说,最早注意到这部小说的人是中青社的编辑萧也牧,他在一次与柳溪的交谈中得知杨沫刚写完一部叫《烧不尽的野火》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描写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道静如何走上革命道路,并成为无产阶级战士的曲折过程。在看过稿子后,萧也牧建议杨沫把小说名字改为《青春之歌》。
但是这部稿子在中青社却一直没能成书,1956年1月26日,“左联”时期的老作家欧阳凡海把帮忙审读稿子后的意见反馈给了出版社,他一共列出了33条意见,仅有3条是优点,其余30条都是缺点,而最大的缺点就是:“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林道静作为书中最重的主人公、中心人物和小说的中心线索。而对于林道静却缺乏足够的批判和分析。”

1958年塔什干亚非作家会议,途经莫斯科胖一点的是杨沫
杨沫起初还是很尊重欧阳凡海的意见的,她在日记中表示,要下决心改好小说,想多酝酿一下,准备好再执笔。但其实从中青社的编辑到杨沫本人都明白,若是按照欧阳凡海的意见修改,几乎就是另写一部作品。
1956年春,杨沫又把稿子给了时任《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的秦兆阳。过了些天,秦兆阳来了电话,说稿子看过了,挺好,没什么大毛病,他已经把稿子转给了作家出版社。5月底,责任编辑任大心告诉杨沫,只需对个别的一两处地方做些修改即可出版,因为要落实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杨沫心里也很清楚,出版社此时之所以对《青春之歌》大放绿灯,其主要的原因是赶上了政治气候的“清朗”时期。正如她在6月28日的日记中所说:“看起来,什么都是一阵风。现在是赶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机上了,否则这小说的命运还不知如何呢?”
在小说正式出版后的1958年3月,杨沫开始收到一些群众来信。4月1日,文化部电影局局长王阑西托人带信给杨沫,称写40万字的小说,并不比写剧本容易,也是对党的贡献,以此安抚她,不要介意北影厂的批评。4月23日,海默写信给杨沫称,周扬在几天前召开的文学评论工作会上说,最近有三部好作品出现,分别是《林海雪原》、《红旗谱》和《青春之歌》。
读者的来信越来越多,询问最多的是林道静、卢嘉川这些书中人物是否还活着。到6月份,《青春之歌》已经出版了39万册。
杨沫开始忙活起来,电话和拜访者络绎不绝。1958年10月4日,杨沫随中国作家代表团来到塔什干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团长茅盾,副团长是周扬和巴金,季羡林、刘白羽等人为团员,其中女作家只有许广平、谢冰心和杨沫三人。
然而,批评声也再次袭来,1959年《中国青年》的第2期发表了北京电子管厂工人郭开的《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一文,文中批评《青春之歌》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没有很好的描写工农群众,没有认真地实际地描写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这是第一篇尖锐批评这部小说的长篇文章,并由此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大讨论。
杨沫和她最后一个老伴李蕴昌,两位老人在晚年相濡以沫,对杨沫的精神状况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
此后,郭开又发表了《就<青春之歌>谈文艺创作和批评中的几个原则问题》一文,再次表示,林道静不是共产党员的典型。从当时的文章还有读者来信来看,批评意见还是少数,多数人并不赞成郭开的观点。在此背景下,茅盾在《中国青年》上撰文,肯定了《青春之歌》是一部有一定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
不过郭开的部分意见后来也被杨沫采纳,她又花了3个月的时间对《青春之歌》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增加了林道静身上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批判。这样的修改被一些人认为是有迎合政治口号的嫌疑。
在1991年6月新版《青春之歌》出版的后记中,杨沫再次回忆了作品引起的各种争议,她说“他们的看法都各有道理,我呢,也有我的道理。我推崇现实主义创作法则,我的生活经历,我的信仰决定了我的爱与憎,也决定了我喜欢写什么,不喜欢写什么。”
回顾《青春之歌》最受关注的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几乎是当时革命历史教育的准教材,有口皆碑的是“三红一创”和“山青保林”八部,前四部是《红日》、《红旗谱》、《红岩》、《创业史》,后四部是《山乡巨变》、《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在毛泽东提倡文艺“为工农兵而创作和利用”的年代,这八部长篇小说中,唯有《青春之歌》的主人公是知识分子。
但这并不表示《青春之歌》不是一本革命历史小说,毕竟书中从一个侧面反映“九·一八”事变后,“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来龙去脉,而她在当年一纸风行的主要原因,大概也是因为唤起了整整一代人的浪漫情操。不可否认的是,《青春之歌》的影响是空前的,截至1990年,本书累计发行500万册,被翻译成18种文字,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反映革命题材的共和国经典长篇小说。
伴随着《青春之歌》一起流行起来的还有这样两句话:“人在痛苦的时候,是最容易回忆往事的。”以及“迷人的爱情幻成的绚丽虹彩,随着时间渐渐褪去了它美丽的颜色。”直到今天,很多人在写作时仍然喜欢引用之。
我们还有必要再回过头看一看当初杨沫创作《青春之歌》时的背景,50年代杨沫的身体很不好,尽管很多朋友都说杨沫心宽坦荡,想得开,但实际上翻开那时她的日记,大都是再写她患病的感受和对疾病的忧虑。在日记里,她多次提到了自己的痛苦,包括了病休不能工作的痛苦;被丈夫冷落的痛苦;睡不好觉的痛苦;三十多岁就大把掉发的痛苦;怀疑自己得了肝癌的痛苦……
在疾病缠身时,当年在冀中的抗日生活碎片和不少牺牲老战友的影像再次浮现,1951年6月9日,杨沫在日记中写道“我有时忽然想,身体总是不好,干脆来个灯尽油干,尽所有力量写出那长篇小说来,然后死了就死了……”9月25日,她草拟了全书提纲,最初的名字叫《千锤百炼》,后改为《烧不尽的野火》。
多年后,儿子老鬼在《母亲杨沫》一书中写道:“如果她身体健康,正常上班工作,终日快快乐乐,仕途顺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