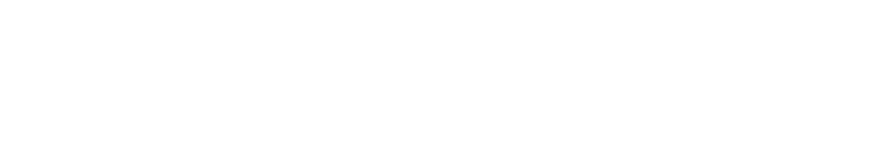阿米娜 飘忽不定的吸毒婚恋
|
|
|||||||||||||||||
简介:
阿米娜 飘忽不定的吸毒婚恋
——青年艾克的城南之恋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杨继斌 实习生 肖克来提
2011-07-14 13:59:59
两个社会边缘人爱情的背后,是一个边缘人群对北京的恋情。

十年或者二十年前,他们为了更美好的生活来到北京。但在美好生活来临之前,其中一部分选择了波德莱尔所描绘的、毒品营造的“人造天堂”。
接纳和善待这个流离于城市边缘的人群,或可帮助他们走出噩运。
连结婚的日子都不记得了
2000年后北京唯一的一桩维汉婚姻快满5年了。两个爱人,也是两个艾滋病毒携带者兼“资深”吸毒者,生活在北京南五环外的大兴工业区。
2006年年底结婚后,艾克和他的新疆老乡——这个群体最多的时候有一千多人——像他们过着游牧生活的祖先一样,在拆迁以及房租的驱使下一次次寻找新的聚居地。从甘家口到北京西站南广场,2008年底,他们搬到了大兴工业区。这里是京城繁华的边缘,是北京生活成本最低的地区之一。
结婚才5年,年轻的妻子柳风便忘记了自己和丈夫艾克一生中最重要的那个日子。这是因为长期吸食海洛因所导致的健忘。
因为遗忘,他们经常在租住的那套一百余平米的房子里,就过往的一些生活细节争论。大到两个人认识的时间地点、第一次带对方回家是什么时候,小到家里的那个红色杯子是妻子送给丈夫的,还是丈夫送给妻子的。但有一个细节,夫妻俩这么多年都没有忘记:对方无论什么时候吸毒,自己都必须守在旁边。
“这是最危险的时候,”柳风说,“一般是先把针管往下推三分之二,但有时毒瘾来得急,手不听使唤,一下子就全推进去,便会非常危险。”
柳风清楚地记得8年前的5月14日,她的前男友兼毒友、台湾人吴杰华,因为吸食海洛因过量死亡。于是,同艾克结婚后,每一次丈夫将海洛因注入胳膊时,柳风都坚持要守在身边。
这便是他们的爱情细节。圈子里的人,都明白旁边有没有人意味着什么。
55岁的阿米娜1991年便从乌鲁木齐到北京谋生。她声称“在北京的维吾尔人,百分之九十我都认识”。她说,从2003年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多个人因为海洛因吸食过量死亡。
搬来大兴工业区之前,艾克夫妇的毒品供应,依赖于增光路那边的“云南街”(并无此街道名,因为此处为北京毒品重要交易点,所以被唤作“云南街”)买粉。北京奥运会之前,警方剔除了这一贩毒渠道。
认识艾克夫妇的人,大多羡慕他们感情好。这在吸毒者群体中属于异类。多数吸毒女嫁人,只是为了寻找一个经济依靠或者稳定的毒品渠道,一旦丈夫被抓,渠道废弃了,女性往往会迅速换人——毒瘾在后面逼着呢。
但艾克几次被抓了以后,柳风都到处找人“捞人”。她说上一次为了“捞”艾克花了一万多块钱。尽管是北京姑娘,但吸毒以后,她在京的社会关系几乎全断了,没有朋友愿意帮忙。最后柳风辗转找到一个给艾滋病患者提供帮助的志愿者,通过后者的人脉,才打通关系,从派出所把艾克带回了家。
柳风体型壮硕,祖上是满族正蓝旗的,谈吐间流露着旗里姑娘的豪气。如果不是胳膊上密密麻麻的针孔,没人会相信她已经有20年的毒史。“四号(海洛因)如果纯度高,对体型影响不是太大,溜冰(冰毒)一星期就能让人变成骷髅。”柳风解释。
黄金年代
1972年出生的柳风,18岁开始吸毒。她的朋友说,柳父是高级干部,柳风1990年从北京外事职高毕业以后,便开始经商。三年后,身家百万。1992年前后,柳风认识了台湾人吴杰华,吴是她资金和毒品的来源。
也就是从1991年前后开始,新疆人蜂拥至内地。新疆真正的改革开放是从1991年开始,随着边境贸易量增加,维吾尔人的金钱意识开始提高,他们渴望体验都市生活。
1995年,23岁的艾克从乌鲁木齐来到北京,在甘家口住下。当时甘家口有近1000维吾尔人。这是阿米娜记忆中的黄金年代。“当时街道两边都是新疆餐馆,北京人都把这里叫新疆村。”当时双方相处融洽,在宰牲节、开斋节等节日里,当地派出所还特地封闭道路,让新疆民众尽情歌舞。孩子们也可以在就近的学校上学读书,成年人可以去牛街那边的清真寺做礼拜。
“当时来北京的,大多是南疆喀什、阿克苏的人,那里比较穷,都想着来北京赚钱。”在北京呆了20年,阿米娜的普通话已经非常纯正。“那时,从新疆来的人,大多有正当工作。”
艾克是带着一个发财的美梦来到北京的。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便有新疆人进京闯荡,这些人衣锦返乡后,具有难以拒绝的示范效应。京疆两地的经济、文化发展落差,让大批新疆人进京寻梦。这和同一时期北京人到纽约寻梦,有同样的内在动因。
但艾克在北京的发展,比柳风要困难得多。语言不通,并且他只读过小学,找不到工作。即使是今天,这也是大多数新疆青年来北京谋生面临的最大障碍。
1995年是在京新疆人境遇的一个分水岭。1995年之前,阿米娜几乎没有见到过有人吸毒,但这一年开始,她经常在路边的垃圾桶看到注射完毒品的针管。
后来维持艾克毒资的主业——贼头——也是在那个时期出现。艾克手下带过几个小孩,小孩去偷钱包,然后提成给艾克。
阿米娜目睹了故乡的孩子慢慢在街头多起来的过程。1997年,她认识了来自伊宁市的图尔斯娜依,一个拥有两个孩子的母亲。来北京半年没有找到工作,却染上了毒瘾。于是,逼着七八岁的儿女,去街上偷毒资。
毒品、小偷几乎是不可遏制地在新疆村蔓延。因为熟悉维汉两种语言,阿米娜隔三差五地被派出所请去当翻译。“很多孩子都是被骗到北京的,骗子跟父母说,带孩子去北京做生意,一年赚一万。结果来了以后,都当了小偷。”
派出所曾解救过多批孩子送回新疆。但凡是已经在北京染上毒瘾的,很快,便又出现在了新疆村。
2002年,北京市开始整治甘家口一带的治安状况。一些新疆人回到了故乡,另一些则搬到了北京西站南广场一带。
2003年,柳风和艾克邂逅。柳风已经不记得她和艾克第一次见面的具体日子。“应该是吴杰华死后不久。”每当柳风开始回顾往事,她都似乎是在同自己的记忆力玩“砸金蛋”游戏,连她自己都不能肯定,哪一些是真相,哪一些是自己的想象,“吴杰华死后,我的天就塌了,买粉的渠道就断了”。
按照柳风的说法,她当时在亚运村经营的一家民族风情酒楼需要维族歌手,艾克来应聘。“我一见面就知道他也是‘跟四哥’(海洛因)的。”柳风的一个好朋友却提供了另一个版本。当时艾克的手下偷了柳风的钱包。柳风托人找到了艾克。两个人一见如故。
但两种说法对于二人后来的发展过程是一致的:过了几天,柳风找艾克买白粉,于是成了好朋友。
那时,两个人的“事业”都处于“上升期”。彼此的朋友没人看好这段感情。“艾克的朋友说我是为了白粉找艾克,我的朋友说艾克是为了我的钱找我。”
从戒毒所出来便结婚
但柳风第一次找艾克买白粉,就被后者骗了。
当时柳风开着一辆白色丰田。艾克说,你下车,我来开,带你去取货。柳风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但艾克把车开到了他朋友开的一个小旅馆。
艾克把柳风带进房间,说在这里等着,我去取白粉。但出门就把门从外面给锁上了。
“他当时以为我吸毒时间不长,忍一下就戒掉了。”柳风回忆。在小旅馆里住了一个星期,毒瘾自然没有戒掉,但出来后,柳风就带着艾克回家了。“我觉得他是真心对我好。”
在随后的两年里,艾克“逃”过很多次。他说他是艾滋病毒携带者,不能和柳风在一起。2005年夏,再一次从乌鲁木齐找回艾克后,柳风拿艾克刚用过的针头刺了一下胳膊。“我跟艾克说,如果我也染上了艾滋病,我们就能在一起了。”
这期间,柳风的生意一落千丈,一则是吴杰华死后,柳的资金链断了;二则是2006年夏,柳风因吸毒被警方抓获,送进了强制戒毒所强制戒毒半年。
柳风进戒毒所后的半年里,艾克主动投案。“我以为进去就能见到她。”艾克笑着回忆他们最终订婚的缘由,“但没想到,里面男女是分开的,我们半年都没有见一面。”
两人从戒毒所出来,已经是2006年底。两个人到乌鲁木齐领了结婚证。研究维族社区的学者及阿米娜均向记者证实,在2000年之后,这是唯一一对在京的维汉通婚的案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曾有过7对,其中6对离婚;1990年代的时候,曾有过3对,其中两对离婚。”伊力哈木说。
此后,他们在北京西站南广场一带的维族聚居区住过一段时间。艾克重操就业,供养着两个人的毒资。但境况已经大不如前。以前有钱的时候,两人都是吸食,即把海洛因放在锡纸上,烘烤,通过呼吸道进入体内,这样相对安全,但是浪费;现在没钱了,两个人开始注射。
新生者和悄然故去者
2008年,36岁的柳风突然想当母亲。“我和艾克商量,如果生下来不健康,孩子活三年,我就养他三年,反正要当一次妈妈。”
2009年,儿子出生了。去地坛医院检查了三次,检查结果都显示,孩子不是艾滋病毒携带者。
为了做到母婴隔断,儿子出生后不久,就送到了乌鲁木齐的婆婆家由小姑子养。柳风决定戒毒。她定期去医院领取海洛因的替代品美沙酮。
儿子健健康康地出生后,艾克曾尝试着收手。他遣散了手下的几个小孩,和柳风一块去找工作,但因为两个人都有案底,且是艾滋病毒携带者,除了艾克做过一段短暂的修车工外,一无所获。
这几乎是目前北京整个吸毒者、艾滋病携带者人群普遍的窘境。
2008年底他们刚迁来的时候,近百名维族人甚至连房子都租不到。他们在网吧、澡堂里度过了多个夜晚。
“其实,房东的想法也可以理解。”拜尔,某NGO的志愿者,他所在的组织每星期免费向艾克他们发放清洁的针头并宣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房东一看这些人吸毒的吸毒偷东西的偷东西,谁敢租房子给他们?”
在拜尔的帮助下,最终租房的问题,勉强解决了。
但毒品和艾滋病,已经开始裁剪这个本就不断缩小的人群。就在2008年底,那个逼着自己儿女去偷窃的图尔斯娜依,因为艾滋病,孤零零地在一街附近的一家小旅馆去世。当地的新疆人集资请阿訇给她办了葬礼。两个孩子已经成年,听说在南方打工。
2010年冬,二十岁的哑巴因为吸毒过量去世了。哑巴是阿克苏人。1995年到北京后,就一直以偷养毒。大家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只知道他是孤儿。
“现在在大兴的这一批维族人,其中60%是吸毒成瘾者,这60%当中约有30%患有艾滋病或者是艾滋病毒携带者。”拜尔说,他所服务的NGO已经关注这个人群近4年。“剩下的多是乙肝或者丙肝患者。”
阿米娜已经盘算着退休回乌鲁木齐了。她不时提起鼎盛时期的甘家口。在她的叙述里,1990年代初
的甘家口新疆村就像史前的马孔多小镇,但毒品就像失眠症,几乎一夜之间就来了。
“我很爱北京。”她说,这些年,她的饭店从甘家口到鼓楼东再到大兴工业区。“越来越偏远了,生意越来越难做了。”
北京市政府已在努力解决在京新疆人的生存发展问题。2010年8月16日,北京新发地市场新疆名特优农产品展销大厅开业。共有两百多个商铺,建筑面积达六千多平方米,专门批发销售新疆特色农产品。“已经有几十户新疆人搬到新发地去了。”阿米娜说。
也许是因为毒品,在大多数时候,柳风看上去都要比普通人更乐观。但她还是难免会在某些时候盘点自己的余生:“我不知道我和艾克什么时候会死,也许10年也许20年。”她想起艾克第一次带她去乌鲁木齐见婆婆。婆婆颤颤巍巍地亲着她的脸颊。婆婆知道她携带有艾滋病毒。
老太太摸着柳风的脸:“希望你和艾克在北京生活快乐。”
——青年艾克的城南之恋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杨继斌 实习生 肖克来提
2011-07-14 13:59:59
两个社会边缘人爱情的背后,是一个边缘人群对北京的恋情。

十年或者二十年前,他们为了更美好的生活来到北京。但在美好生活来临之前,其中一部分选择了波德莱尔所描绘的、毒品营造的“人造天堂”。
接纳和善待这个流离于城市边缘的人群,或可帮助他们走出噩运。
连结婚的日子都不记得了
2000年后北京唯一的一桩维汉婚姻快满5年了。两个爱人,也是两个艾滋病毒携带者兼“资深”吸毒者,生活在北京南五环外的大兴工业区。
2006年年底结婚后,艾克和他的新疆老乡——这个群体最多的时候有一千多人——像他们过着游牧生活的祖先一样,在拆迁以及房租的驱使下一次次寻找新的聚居地。从甘家口到北京西站南广场,2008年底,他们搬到了大兴工业区。这里是京城繁华的边缘,是北京生活成本最低的地区之一。
结婚才5年,年轻的妻子柳风便忘记了自己和丈夫艾克一生中最重要的那个日子。这是因为长期吸食海洛因所导致的健忘。
因为遗忘,他们经常在租住的那套一百余平米的房子里,就过往的一些生活细节争论。大到两个人认识的时间地点、第一次带对方回家是什么时候,小到家里的那个红色杯子是妻子送给丈夫的,还是丈夫送给妻子的。但有一个细节,夫妻俩这么多年都没有忘记:对方无论什么时候吸毒,自己都必须守在旁边。
“这是最危险的时候,”柳风说,“一般是先把针管往下推三分之二,但有时毒瘾来得急,手不听使唤,一下子就全推进去,便会非常危险。”
柳风清楚地记得8年前的5月14日,她的前男友兼毒友、台湾人吴杰华,因为吸食海洛因过量死亡。于是,同艾克结婚后,每一次丈夫将海洛因注入胳膊时,柳风都坚持要守在身边。
这便是他们的爱情细节。圈子里的人,都明白旁边有没有人意味着什么。
55岁的阿米娜1991年便从乌鲁木齐到北京谋生。她声称“在北京的维吾尔人,百分之九十我都认识”。她说,从2003年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多个人因为海洛因吸食过量死亡。
搬来大兴工业区之前,艾克夫妇的毒品供应,依赖于增光路那边的“云南街”(并无此街道名,因为此处为北京毒品重要交易点,所以被唤作“云南街”)买粉。北京奥运会之前,警方剔除了这一贩毒渠道。
认识艾克夫妇的人,大多羡慕他们感情好。这在吸毒者群体中属于异类。多数吸毒女嫁人,只是为了寻找一个经济依靠或者稳定的毒品渠道,一旦丈夫被抓,渠道废弃了,女性往往会迅速换人——毒瘾在后面逼着呢。
但艾克几次被抓了以后,柳风都到处找人“捞人”。她说上一次为了“捞”艾克花了一万多块钱。尽管是北京姑娘,但吸毒以后,她在京的社会关系几乎全断了,没有朋友愿意帮忙。最后柳风辗转找到一个给艾滋病患者提供帮助的志愿者,通过后者的人脉,才打通关系,从派出所把艾克带回了家。
柳风体型壮硕,祖上是满族正蓝旗的,谈吐间流露着旗里姑娘的豪气。如果不是胳膊上密密麻麻的针孔,没人会相信她已经有20年的毒史。“四号(海洛因)如果纯度高,对体型影响不是太大,溜冰(冰毒)一星期就能让人变成骷髅。”柳风解释。
黄金年代
1972年出生的柳风,18岁开始吸毒。她的朋友说,柳父是高级干部,柳风1990年从北京外事职高毕业以后,便开始经商。三年后,身家百万。1992年前后,柳风认识了台湾人吴杰华,吴是她资金和毒品的来源。
也就是从1991年前后开始,新疆人蜂拥至内地。新疆真正的改革开放是从1991年开始,随着边境贸易量增加,维吾尔人的金钱意识开始提高,他们渴望体验都市生活。
1995年,23岁的艾克从乌鲁木齐来到北京,在甘家口住下。当时甘家口有近1000维吾尔人。这是阿米娜记忆中的黄金年代。“当时街道两边都是新疆餐馆,北京人都把这里叫新疆村。”当时双方相处融洽,在宰牲节、开斋节等节日里,当地派出所还特地封闭道路,让新疆民众尽情歌舞。孩子们也可以在就近的学校上学读书,成年人可以去牛街那边的清真寺做礼拜。
“当时来北京的,大多是南疆喀什、阿克苏的人,那里比较穷,都想着来北京赚钱。”在北京呆了20年,阿米娜的普通话已经非常纯正。“那时,从新疆来的人,大多有正当工作。”
艾克是带着一个发财的美梦来到北京的。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便有新疆人进京闯荡,这些人衣锦返乡后,具有难以拒绝的示范效应。京疆两地的经济、文化发展落差,让大批新疆人进京寻梦。这和同一时期北京人到纽约寻梦,有同样的内在动因。
但艾克在北京的发展,比柳风要困难得多。语言不通,并且他只读过小学,找不到工作。即使是今天,这也是大多数新疆青年来北京谋生面临的最大障碍。
1995年是在京新疆人境遇的一个分水岭。1995年之前,阿米娜几乎没有见到过有人吸毒,但这一年开始,她经常在路边的垃圾桶看到注射完毒品的针管。
后来维持艾克毒资的主业——贼头——也是在那个时期出现。艾克手下带过几个小孩,小孩去偷钱包,然后提成给艾克。
阿米娜目睹了故乡的孩子慢慢在街头多起来的过程。1997年,她认识了来自伊宁市的图尔斯娜依,一个拥有两个孩子的母亲。来北京半年没有找到工作,却染上了毒瘾。于是,逼着七八岁的儿女,去街上偷毒资。
毒品、小偷几乎是不可遏制地在新疆村蔓延。因为熟悉维汉两种语言,阿米娜隔三差五地被派出所请去当翻译。“很多孩子都是被骗到北京的,骗子跟父母说,带孩子去北京做生意,一年赚一万。结果来了以后,都当了小偷。”
派出所曾解救过多批孩子送回新疆。但凡是已经在北京染上毒瘾的,很快,便又出现在了新疆村。
2002年,北京市开始整治甘家口一带的治安状况。一些新疆人回到了故乡,另一些则搬到了北京西站南广场一带。
2003年,柳风和艾克邂逅。柳风已经不记得她和艾克第一次见面的具体日子。“应该是吴杰华死后不久。”每当柳风开始回顾往事,她都似乎是在同自己的记忆力玩“砸金蛋”游戏,连她自己都不能肯定,哪一些是真相,哪一些是自己的想象,“吴杰华死后,我的天就塌了,买粉的渠道就断了”。
按照柳风的说法,她当时在亚运村经营的一家民族风情酒楼需要维族歌手,艾克来应聘。“我一见面就知道他也是‘跟四哥’(海洛因)的。”柳风的一个好朋友却提供了另一个版本。当时艾克的手下偷了柳风的钱包。柳风托人找到了艾克。两个人一见如故。
但两种说法对于二人后来的发展过程是一致的:过了几天,柳风找艾克买白粉,于是成了好朋友。
那时,两个人的“事业”都处于“上升期”。彼此的朋友没人看好这段感情。“艾克的朋友说我是为了白粉找艾克,我的朋友说艾克是为了我的钱找我。”
从戒毒所出来便结婚
但柳风第一次找艾克买白粉,就被后者骗了。
当时柳风开着一辆白色丰田。艾克说,你下车,我来开,带你去取货。柳风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但艾克把车开到了他朋友开的一个小旅馆。
艾克把柳风带进房间,说在这里等着,我去取白粉。但出门就把门从外面给锁上了。
“他当时以为我吸毒时间不长,忍一下就戒掉了。”柳风回忆。在小旅馆里住了一个星期,毒瘾自然没有戒掉,但出来后,柳风就带着艾克回家了。“我觉得他是真心对我好。”
在随后的两年里,艾克“逃”过很多次。他说他是艾滋病毒携带者,不能和柳风在一起。2005年夏,再一次从乌鲁木齐找回艾克后,柳风拿艾克刚用过的针头刺了一下胳膊。“我跟艾克说,如果我也染上了艾滋病,我们就能在一起了。”
这期间,柳风的生意一落千丈,一则是吴杰华死后,柳的资金链断了;二则是2006年夏,柳风因吸毒被警方抓获,送进了强制戒毒所强制戒毒半年。
柳风进戒毒所后的半年里,艾克主动投案。“我以为进去就能见到她。”艾克笑着回忆他们最终订婚的缘由,“但没想到,里面男女是分开的,我们半年都没有见一面。”
两人从戒毒所出来,已经是2006年底。两个人到乌鲁木齐领了结婚证。研究维族社区的学者及阿米娜均向记者证实,在2000年之后,这是唯一一对在京的维汉通婚的案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曾有过7对,其中6对离婚;1990年代的时候,曾有过3对,其中两对离婚。”伊力哈木说。
此后,他们在北京西站南广场一带的维族聚居区住过一段时间。艾克重操就业,供养着两个人的毒资。但境况已经大不如前。以前有钱的时候,两人都是吸食,即把海洛因放在锡纸上,烘烤,通过呼吸道进入体内,这样相对安全,但是浪费;现在没钱了,两个人开始注射。
新生者和悄然故去者
2008年,36岁的柳风突然想当母亲。“我和艾克商量,如果生下来不健康,孩子活三年,我就养他三年,反正要当一次妈妈。”
2009年,儿子出生了。去地坛医院检查了三次,检查结果都显示,孩子不是艾滋病毒携带者。
为了做到母婴隔断,儿子出生后不久,就送到了乌鲁木齐的婆婆家由小姑子养。柳风决定戒毒。她定期去医院领取海洛因的替代品美沙酮。
儿子健健康康地出生后,艾克曾尝试着收手。他遣散了手下的几个小孩,和柳风一块去找工作,但因为两个人都有案底,且是艾滋病毒携带者,除了艾克做过一段短暂的修车工外,一无所获。
这几乎是目前北京整个吸毒者、艾滋病携带者人群普遍的窘境。
2008年底他们刚迁来的时候,近百名维族人甚至连房子都租不到。他们在网吧、澡堂里度过了多个夜晚。
“其实,房东的想法也可以理解。”拜尔,某NGO的志愿者,他所在的组织每星期免费向艾克他们发放清洁的针头并宣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房东一看这些人吸毒的吸毒偷东西的偷东西,谁敢租房子给他们?”
在拜尔的帮助下,最终租房的问题,勉强解决了。
但毒品和艾滋病,已经开始裁剪这个本就不断缩小的人群。就在2008年底,那个逼着自己儿女去偷窃的图尔斯娜依,因为艾滋病,孤零零地在一街附近的一家小旅馆去世。当地的新疆人集资请阿訇给她办了葬礼。两个孩子已经成年,听说在南方打工。
2010年冬,二十岁的哑巴因为吸毒过量去世了。哑巴是阿克苏人。1995年到北京后,就一直以偷养毒。大家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只知道他是孤儿。
“现在在大兴的这一批维族人,其中60%是吸毒成瘾者,这60%当中约有30%患有艾滋病或者是艾滋病毒携带者。”拜尔说,他所服务的NGO已经关注这个人群近4年。“剩下的多是乙肝或者丙肝患者。”
阿米娜已经盘算着退休回乌鲁木齐了。她不时提起鼎盛时期的甘家口。在她的叙述里,1990年代初
的甘家口新疆村就像史前的马孔多小镇,但毒品就像失眠症,几乎一夜之间就来了。
“我很爱北京。”她说,这些年,她的饭店从甘家口到鼓楼东再到大兴工业区。“越来越偏远了,生意越来越难做了。”
北京市政府已在努力解决在京新疆人的生存发展问题。2010年8月16日,北京新发地市场新疆名特优农产品展销大厅开业。共有两百多个商铺,建筑面积达六千多平方米,专门批发销售新疆特色农产品。“已经有几十户新疆人搬到新发地去了。”阿米娜说。
也许是因为毒品,在大多数时候,柳风看上去都要比普通人更乐观。但她还是难免会在某些时候盘点自己的余生:“我不知道我和艾克什么时候会死,也许10年也许20年。”她想起艾克第一次带她去乌鲁木齐见婆婆。婆婆颤颤巍巍地亲着她的脸颊。婆婆知道她携带有艾滋病毒。
老太太摸着柳风的脸:“希望你和艾克在北京生活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