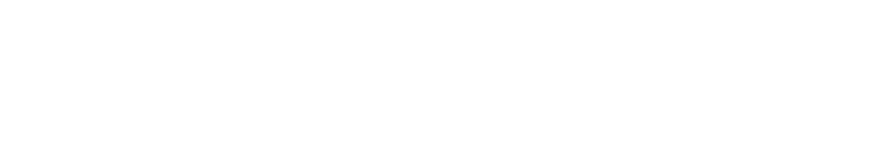杨宝钢大师 走访黑市心惊肉跳
|
|
|||||||||||||||||
简介:
杨宝钢大师 走访黑市心惊肉跳
——犀牛角上的中国魅影
作者: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黄泓翔
发自:南非、莫桑比克 最后更新:2013-10-10 14:48:00
一名在南非做调查的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留学生,通过卧底、暗访,展现了走私网的层层复杂生态,以及其中牵涉中国人的环节。这里是克鲁格国家公园——南非最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全非洲野生犀牛最后的避难所。然而,这里已非犀牛的天堂。据统计,2012年在南非被猎杀的犀牛共有668头,而2013年至今,又有618头犀牛被盗猎者杀死取角。“十二年后的2024年,野生犀牛将因盗猎而从克鲁格国家公园消失。”纪录片《The Hanoi Connection》这样讲述。在这部纪录片中,虽然扣动来复枪扳机的多是非洲黑人,但是亚洲市场尤其是越南、中国,扮演的却是“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的真实存在。
据南非一名反盗猎特警介绍,克鲁格国家公园犀牛角走私利益链一般由五层构成:最底层的盗猎者往往是贫困的黑人;第二层是地方性的小规模收购和转运者,被称为“跑者”,总是能嗅到犀牛角的货源并进行中间倒卖;第三层是全国性的收购者,从事更专业、有组织的集团犯罪;第四层是在非洲的收购者兼出口者,以越南人居多,也有部分是中国人;第五层是身在越南、中国组织销售的头目,为亚洲人。
在南非,犀牛角、象牙、狮子骨、野生鲍鱼的走私往往由同样一张交错着毒品和枪支的网络在运作,而亚洲人扮演了关键的买家角色。为了深度调查这张走私网及“亚洲环节”,我扮演中国买家,成为了南非反盗猎部门特警戴维斯(化名)的卧底同伴。
特警的卧底行动
南非最大都市约翰内斯堡(以下简称约堡)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之一。枪杀、抢劫、黑帮、走私……它们无时不刻喧嚣在大街小巷,连夜幕都不需要。这就是戴维斯的工作环境。据他描述,反盗猎警察牺牲、被暗杀并不是好莱坞电影里才有的情节,在南非,特警的妻子总要心怀恐惧——她们从不知道丈夫突然离开是执行什么任务,也不知道丈夫能否平安归来。
2013年8月某天中午,在约堡中国城附近一家快餐店里,戴维斯、我、线人和嫌犯约好了在此面谈交易细节。戴维斯面前放了一听可乐,如果不看底部,绝对看不出是录音和录像设备。斜对面的桌子旁坐着夸克,那是我们的线人。夸克牵线搭桥,将戴维斯介绍给了一伙走私鲍鱼的嫌犯。戴维斯告诉我,90%的鲍鱼走私犯都和犀牛角有关联。因此,抓捕鲍鱼走私犯往往能一箭双雕。
三名黑人走进来,眼神飘忽,坐在了我们对面。“这位黄杰森先生是我的雇主,他在这边从事收购已经有一年了。”戴维斯打破僵局,向走私犯介绍我。在大多数非洲黑人的眼里,中国人乃至亚洲人是“财神爷”,没有他们,非洲人不会想到犀牛角、鲍鱼可以卖出天价。
据WWF(世界自然基金会)和TRAFFIC(国际野生物贸易组织)最新发布的报告《犀牛角消费者是谁》显示,犀牛角主要流向越南的富人,中国人追随其后,香港也成为举足轻重的亚洲中转站。TRAFFIC的报告显示,2009至2012年期间,亚洲近80%被截获的犀牛角走私案例都在中国境内。开始谈细节。对方有数吨冰冻鲍鱼,开价1500兰特(约150美元)一公斤。
砍价。“1200可以吗?你去跟你叔叔电话确认一下。”一番交涉后,戴维斯对我使了个眼色。我随即在一旁打了个电话,回来跟戴维斯耳语。成交。约好第二天早上9点交易。“你明天在唐人街牌坊里面第一条横路的离街口三十米处等我,我会上他们的车,带他们到那里,然后我们的警车会截击并逮捕他们。”戴维斯对我说。不过,第二天在戴维斯指定的地点,直到10点都没有发生预期的闪电战。近11点,我终于接到戴维斯电话,被告知计划临时出现了变故,但罪犯均已被捕。“看你吓成这样,这绝对是我工作里面最不危险的情况之一了。”戴维斯笑道。
唐人街的买家们
此次卧底,我经历的正是犀牛角走私链上,从第三层转向第四层的一幕。
据警方透露,约堡中国城地区是犀牛角、象牙、鲍鱼走私的中心枢纽,隐匿着很多第四层的犯罪嫌疑人,他们从当地第三层走私者手里收购犀牛角等,再通过打点,用飞机或轮船输送到越南、中国等亚洲地区,从中牟取暴利。“绝大部分的交易都发生在豪登地区,尤其是约翰内斯堡的中国城附近。”戴维斯说。
乔老大(Big Joe)是戴维斯印象最深的第三层全国性罪犯头子。他正是在约堡所在的豪登省地区进行犀牛角贸易。早期,他从事绑架、抢劫、毒品、军火等勾当。再之后,他发现犀牛角这个极其赚钱的行当:早在数年前,南非的犀牛角大概就可以卖到两万美元一公斤,价格超过黄金和毒品。
2012年3月,警方对乔老大进行了“钓鱼执法”(Reverse Trap):南非法律规定,犯罪现场必须同时存在犀牛角和交易款,定罪才能成立。为此,警方常常使用卧底进行购买或贩卖,以将罪犯抓获于现场。乔老大落网后,与之固定联系的亚洲买家并不知情。根据警方信息,2012年5月,一名中国男性买家从该渠道试图购买犀牛角被抓,当时他已有六根从其他地方收购来的犀牛角。次月,另一名中国女子落网。据悉,他们都是有南非籍的华人。
反盗猎特警在南非的运作依靠着广泛的线人。罪犯一旦根据线人的信息被捕,线人会获得一千到两千美元左右的奖励。不过中国人和越南人群体里则至今没有真正能信任的线人,这令警方非常头痛。
为了解中国移民在犀牛角走私网络里的关联,我住进了约堡西罗町地区的唐人街。这是一条用十分钟就走完全程的街,鱼龙混杂。在中国企业外派员工眼里,这里有一群“老侨”,以福建、浙江、广东人为主。在南非汇率形势较好的那些年,很多移民呼朋唤友,一起在这里从事各种生意——有些是阳光生意,有些则在灰色边缘。
东北人丁哥(化名)六七年前来到约堡,现在以开出租车谋生。“象牙很容易,我经常带人去买。犀牛角现在不可能买到,那个比走私毒品还厉害。如果说象牙是大麻,那么犀牛角就是海洛因。就算我有货,我也只会给固定的下家。”他说。一提到犀牛角,这里的不少华人都表示不知情,有的还会劝我不要到处问,以免被抓。“最近中国人也有因为这个被抓的。”开饭店的李阿姨说。在这个中国城里,浮动着不少被举报但还没被证实的信息,比如“一名姓张的中国人在这里长期从事象牙交易,供给他在国内的亲戚”,“每次只要有国内高访团过来,犀牛角象牙价格就飞涨”等等。
根据警方线索,我来到了唐人街附近一家办公楼,这家位于四楼的进出口公司如今已人去楼空。华人老板夫妇在2012年6月份左右被现场缴获。“琳达龚(该女子名字)哭得跟孩子一样,整个脸都扭曲了。”当时在场的警方知情人说。
会说中文“犀牛角”的黑人商贩
克鲁格国家公园位于南非和莫桑比克长达400公里长的边界上,而莫桑比克正是犀牛盗猎者的主要源头。而虽然被CITES(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公约)等敦促,莫桑比克的打击力度远远不及盗猎者猖獗。戴维斯告诉我,对于贫穷的莫桑比克人而言,一支犀牛角就是他们20年的生活来源。
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有个著名的象牙市场。象牙商贩往往也走私犀牛角,但犀牛角往往通过固定渠道,更隐秘地输送。他们多属于犀牛角走私第二层犯罪者,连接着猎手。
见我到来,小贩们用流利的中文喊着“象牙”。“有犀牛角吗?”我问。“有,15000美元一公斤,不过在家里,不在这里。”商贩伊诺柯告诉我,可以去他家看货,在机场只需要给工作人员一些钱就可以顺利把犀牛角带走。当发现有人想买犀牛角,其他几个商贩也过来招呼,并且次日就可以约定看货交易。他们透露,犀牛角多来自莫桑比克和南非接壤的边境地区。
老朱(化名)是一家中企员工,他在马普托已经两年了,黑木和象牙是他的主要采购对象。“象牙的价格比我刚来时贵多了,成色也没那么好了。”他叹息当时没有多买。老朱介绍,他的同事去年把一根手臂粗的原牙制品带了回去,在马普托机场时被查到了,但仅仅付了300美元就了事。在北京机场,他的象牙并没有被查到。如果说中国企业的海外员工更多是充当散客,那么中国在莫桑比克的较底层移民就更多地参与到更专业化的走私之中,包括金额比象牙多百倍的犀牛角交易。
盗猎者“大脚”
“大脚”把拖鞋留在了围栏外边,从莫桑比克边境赤脚走进克鲁格国家公园。这是处在犀牛角利益链最底层的盗猎者:出生偏僻乡村,穿梭于丛林间,靠着盗猎犀牛角的高危收入,试图一夜之间从赤贫变成暴富。“大脚”是盗猎圈内非常有名的猎手,他特别大的足迹总是被追踪者留意到。2012年4月,他终于被捕,并向警方说出了他的故事。
数年前,他来到莫桑比克一座小城,遇到了盗猎网第二层中间人——对方在招募能够跟巡逻队员、狗以及直升机对抗的盗猎者。“大脚”和其他两名猎手形成小队。他们一般选择夜间行进,就着星光,寻找着草丛里犀牛的粪便和脚印。每个月的月圆之夜,是他们活动的最好时机。他们必须非常小心——不只是提防巡逻队,还要提防同行。“如果我看到其他盗猎者,可能杀了他们并且拿走他们手里的货。”“大脚”告诉警方。
即便是“大脚”这样优秀的猎手,找到犀牛并成功猎杀还是很困难的。他先后进入公园十次,只成功猎杀了一头犀牛。而在第十一次,他的生涯终结了:一个作为竞争对手的盗猎团伙出卖了他们的信息,他被警察埋伏并抓获。在非洲的当地报纸里,总有像上面这样零星的盗猎者被抓的消息。2013年到7月31日为止,共147名犀牛盗猎者被南非警方逮捕,这并不包括被击毙的盗猎者。
没有办法打赢的战争
如今,在莫桑比克挨着克鲁格国家公园边境的乡村,为了带给那些贫穷盗猎者新的生存方式,一系列实验性的农业项目开始启动。里维是一个甘蔗项目的工作人员,他讲述了自己在某个偏远乡村的经历:“一个村民把我带到了三个并排的坟墓边上,告诉我,那些都是他的亲人,因为盗猎犀牛而死在了国家公园里。他告诉我,他也是一个犀牛盗猎者,但是他不想重蹈覆辙。”
然而,盗猎依然凶猛。
“今天的盗猎已经不像我年轻时了,那时候我们开着车,追赶着拿着弓弩和长矛的盗猎者。”年届六旬的汉斯曾经是一名巡逻员,他今天仍然志愿从事很多相关反盗猎的活动,面对着往往是配备夜视等先进设备的盗猎者,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各种野生动物保护机构尝试做出自己的尝试:锯断犀牛的角,甚至在犀牛角里“下毒”——然而,走私者视此为笑话,那所谓的“犀牛角”涂毒,只不过是涂上会掉落的让人感到不适的药物而已。
对于像戴维斯这样的特警,他感到遏制这张庞大走私网的关键不仅仅在非洲的盗猎者。“只要有巨大的市场,就没有办法打赢这场战争。一批的盗猎者倒下,又有另一批盗猎者站起来,填补了链条的空缺。”戴维斯叹息。
——犀牛角上的中国魅影
作者: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黄泓翔
发自:南非、莫桑比克 最后更新:2013-10-10 14:48:00
一名在南非做调查的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留学生,通过卧底、暗访,展现了走私网的层层复杂生态,以及其中牵涉中国人的环节。这里是克鲁格国家公园——南非最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全非洲野生犀牛最后的避难所。然而,这里已非犀牛的天堂。据统计,2012年在南非被猎杀的犀牛共有668头,而2013年至今,又有618头犀牛被盗猎者杀死取角。“十二年后的2024年,野生犀牛将因盗猎而从克鲁格国家公园消失。”纪录片《The Hanoi Connection》这样讲述。在这部纪录片中,虽然扣动来复枪扳机的多是非洲黑人,但是亚洲市场尤其是越南、中国,扮演的却是“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的真实存在。
据南非一名反盗猎特警介绍,克鲁格国家公园犀牛角走私利益链一般由五层构成:最底层的盗猎者往往是贫困的黑人;第二层是地方性的小规模收购和转运者,被称为“跑者”,总是能嗅到犀牛角的货源并进行中间倒卖;第三层是全国性的收购者,从事更专业、有组织的集团犯罪;第四层是在非洲的收购者兼出口者,以越南人居多,也有部分是中国人;第五层是身在越南、中国组织销售的头目,为亚洲人。
在南非,犀牛角、象牙、狮子骨、野生鲍鱼的走私往往由同样一张交错着毒品和枪支的网络在运作,而亚洲人扮演了关键的买家角色。为了深度调查这张走私网及“亚洲环节”,我扮演中国买家,成为了南非反盗猎部门特警戴维斯(化名)的卧底同伴。
特警的卧底行动
南非最大都市约翰内斯堡(以下简称约堡)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之一。枪杀、抢劫、黑帮、走私……它们无时不刻喧嚣在大街小巷,连夜幕都不需要。这就是戴维斯的工作环境。据他描述,反盗猎警察牺牲、被暗杀并不是好莱坞电影里才有的情节,在南非,特警的妻子总要心怀恐惧——她们从不知道丈夫突然离开是执行什么任务,也不知道丈夫能否平安归来。
2013年8月某天中午,在约堡中国城附近一家快餐店里,戴维斯、我、线人和嫌犯约好了在此面谈交易细节。戴维斯面前放了一听可乐,如果不看底部,绝对看不出是录音和录像设备。斜对面的桌子旁坐着夸克,那是我们的线人。夸克牵线搭桥,将戴维斯介绍给了一伙走私鲍鱼的嫌犯。戴维斯告诉我,90%的鲍鱼走私犯都和犀牛角有关联。因此,抓捕鲍鱼走私犯往往能一箭双雕。
三名黑人走进来,眼神飘忽,坐在了我们对面。“这位黄杰森先生是我的雇主,他在这边从事收购已经有一年了。”戴维斯打破僵局,向走私犯介绍我。在大多数非洲黑人的眼里,中国人乃至亚洲人是“财神爷”,没有他们,非洲人不会想到犀牛角、鲍鱼可以卖出天价。
据WWF(世界自然基金会)和TRAFFIC(国际野生物贸易组织)最新发布的报告《犀牛角消费者是谁》显示,犀牛角主要流向越南的富人,中国人追随其后,香港也成为举足轻重的亚洲中转站。TRAFFIC的报告显示,2009至2012年期间,亚洲近80%被截获的犀牛角走私案例都在中国境内。开始谈细节。对方有数吨冰冻鲍鱼,开价1500兰特(约150美元)一公斤。
砍价。“1200可以吗?你去跟你叔叔电话确认一下。”一番交涉后,戴维斯对我使了个眼色。我随即在一旁打了个电话,回来跟戴维斯耳语。成交。约好第二天早上9点交易。“你明天在唐人街牌坊里面第一条横路的离街口三十米处等我,我会上他们的车,带他们到那里,然后我们的警车会截击并逮捕他们。”戴维斯对我说。不过,第二天在戴维斯指定的地点,直到10点都没有发生预期的闪电战。近11点,我终于接到戴维斯电话,被告知计划临时出现了变故,但罪犯均已被捕。“看你吓成这样,这绝对是我工作里面最不危险的情况之一了。”戴维斯笑道。
唐人街的买家们
此次卧底,我经历的正是犀牛角走私链上,从第三层转向第四层的一幕。
据警方透露,约堡中国城地区是犀牛角、象牙、鲍鱼走私的中心枢纽,隐匿着很多第四层的犯罪嫌疑人,他们从当地第三层走私者手里收购犀牛角等,再通过打点,用飞机或轮船输送到越南、中国等亚洲地区,从中牟取暴利。“绝大部分的交易都发生在豪登地区,尤其是约翰内斯堡的中国城附近。”戴维斯说。
乔老大(Big Joe)是戴维斯印象最深的第三层全国性罪犯头子。他正是在约堡所在的豪登省地区进行犀牛角贸易。早期,他从事绑架、抢劫、毒品、军火等勾当。再之后,他发现犀牛角这个极其赚钱的行当:早在数年前,南非的犀牛角大概就可以卖到两万美元一公斤,价格超过黄金和毒品。
2012年3月,警方对乔老大进行了“钓鱼执法”(Reverse Trap):南非法律规定,犯罪现场必须同时存在犀牛角和交易款,定罪才能成立。为此,警方常常使用卧底进行购买或贩卖,以将罪犯抓获于现场。乔老大落网后,与之固定联系的亚洲买家并不知情。根据警方信息,2012年5月,一名中国男性买家从该渠道试图购买犀牛角被抓,当时他已有六根从其他地方收购来的犀牛角。次月,另一名中国女子落网。据悉,他们都是有南非籍的华人。
反盗猎特警在南非的运作依靠着广泛的线人。罪犯一旦根据线人的信息被捕,线人会获得一千到两千美元左右的奖励。不过中国人和越南人群体里则至今没有真正能信任的线人,这令警方非常头痛。
为了解中国移民在犀牛角走私网络里的关联,我住进了约堡西罗町地区的唐人街。这是一条用十分钟就走完全程的街,鱼龙混杂。在中国企业外派员工眼里,这里有一群“老侨”,以福建、浙江、广东人为主。在南非汇率形势较好的那些年,很多移民呼朋唤友,一起在这里从事各种生意——有些是阳光生意,有些则在灰色边缘。
东北人丁哥(化名)六七年前来到约堡,现在以开出租车谋生。“象牙很容易,我经常带人去买。犀牛角现在不可能买到,那个比走私毒品还厉害。如果说象牙是大麻,那么犀牛角就是海洛因。就算我有货,我也只会给固定的下家。”他说。一提到犀牛角,这里的不少华人都表示不知情,有的还会劝我不要到处问,以免被抓。“最近中国人也有因为这个被抓的。”开饭店的李阿姨说。在这个中国城里,浮动着不少被举报但还没被证实的信息,比如“一名姓张的中国人在这里长期从事象牙交易,供给他在国内的亲戚”,“每次只要有国内高访团过来,犀牛角象牙价格就飞涨”等等。
根据警方线索,我来到了唐人街附近一家办公楼,这家位于四楼的进出口公司如今已人去楼空。华人老板夫妇在2012年6月份左右被现场缴获。“琳达龚(该女子名字)哭得跟孩子一样,整个脸都扭曲了。”当时在场的警方知情人说。
会说中文“犀牛角”的黑人商贩
克鲁格国家公园位于南非和莫桑比克长达400公里长的边界上,而莫桑比克正是犀牛盗猎者的主要源头。而虽然被CITES(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公约)等敦促,莫桑比克的打击力度远远不及盗猎者猖獗。戴维斯告诉我,对于贫穷的莫桑比克人而言,一支犀牛角就是他们20年的生活来源。
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有个著名的象牙市场。象牙商贩往往也走私犀牛角,但犀牛角往往通过固定渠道,更隐秘地输送。他们多属于犀牛角走私第二层犯罪者,连接着猎手。
见我到来,小贩们用流利的中文喊着“象牙”。“有犀牛角吗?”我问。“有,15000美元一公斤,不过在家里,不在这里。”商贩伊诺柯告诉我,可以去他家看货,在机场只需要给工作人员一些钱就可以顺利把犀牛角带走。当发现有人想买犀牛角,其他几个商贩也过来招呼,并且次日就可以约定看货交易。他们透露,犀牛角多来自莫桑比克和南非接壤的边境地区。
老朱(化名)是一家中企员工,他在马普托已经两年了,黑木和象牙是他的主要采购对象。“象牙的价格比我刚来时贵多了,成色也没那么好了。”他叹息当时没有多买。老朱介绍,他的同事去年把一根手臂粗的原牙制品带了回去,在马普托机场时被查到了,但仅仅付了300美元就了事。在北京机场,他的象牙并没有被查到。如果说中国企业的海外员工更多是充当散客,那么中国在莫桑比克的较底层移民就更多地参与到更专业化的走私之中,包括金额比象牙多百倍的犀牛角交易。
盗猎者“大脚”
“大脚”把拖鞋留在了围栏外边,从莫桑比克边境赤脚走进克鲁格国家公园。这是处在犀牛角利益链最底层的盗猎者:出生偏僻乡村,穿梭于丛林间,靠着盗猎犀牛角的高危收入,试图一夜之间从赤贫变成暴富。“大脚”是盗猎圈内非常有名的猎手,他特别大的足迹总是被追踪者留意到。2012年4月,他终于被捕,并向警方说出了他的故事。
数年前,他来到莫桑比克一座小城,遇到了盗猎网第二层中间人——对方在招募能够跟巡逻队员、狗以及直升机对抗的盗猎者。“大脚”和其他两名猎手形成小队。他们一般选择夜间行进,就着星光,寻找着草丛里犀牛的粪便和脚印。每个月的月圆之夜,是他们活动的最好时机。他们必须非常小心——不只是提防巡逻队,还要提防同行。“如果我看到其他盗猎者,可能杀了他们并且拿走他们手里的货。”“大脚”告诉警方。
即便是“大脚”这样优秀的猎手,找到犀牛并成功猎杀还是很困难的。他先后进入公园十次,只成功猎杀了一头犀牛。而在第十一次,他的生涯终结了:一个作为竞争对手的盗猎团伙出卖了他们的信息,他被警察埋伏并抓获。在非洲的当地报纸里,总有像上面这样零星的盗猎者被抓的消息。2013年到7月31日为止,共147名犀牛盗猎者被南非警方逮捕,这并不包括被击毙的盗猎者。
没有办法打赢的战争
如今,在莫桑比克挨着克鲁格国家公园边境的乡村,为了带给那些贫穷盗猎者新的生存方式,一系列实验性的农业项目开始启动。里维是一个甘蔗项目的工作人员,他讲述了自己在某个偏远乡村的经历:“一个村民把我带到了三个并排的坟墓边上,告诉我,那些都是他的亲人,因为盗猎犀牛而死在了国家公园里。他告诉我,他也是一个犀牛盗猎者,但是他不想重蹈覆辙。”
然而,盗猎依然凶猛。
“今天的盗猎已经不像我年轻时了,那时候我们开着车,追赶着拿着弓弩和长矛的盗猎者。”年届六旬的汉斯曾经是一名巡逻员,他今天仍然志愿从事很多相关反盗猎的活动,面对着往往是配备夜视等先进设备的盗猎者,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各种野生动物保护机构尝试做出自己的尝试:锯断犀牛的角,甚至在犀牛角里“下毒”——然而,走私者视此为笑话,那所谓的“犀牛角”涂毒,只不过是涂上会掉落的让人感到不适的药物而已。
对于像戴维斯这样的特警,他感到遏制这张庞大走私网的关键不仅仅在非洲的盗猎者。“只要有巨大的市场,就没有办法打赢这场战争。一批的盗猎者倒下,又有另一批盗猎者站起来,填补了链条的空缺。”戴维斯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