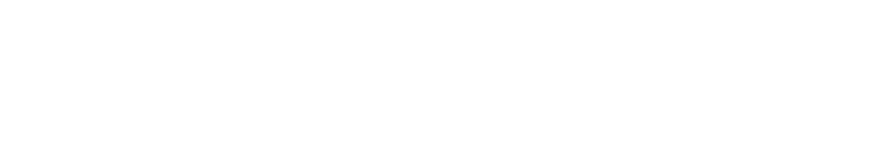| 发布时间: | 2009-07-17 16:33:04 | 点击次数: | 0 |
简述:
简介:
车丕照:和平发展与国际合作义务
--------------------------------------------------------------------------------
我国的和平发展离不开特定的国际环境。尽管与冷战结束之前或与二战结束之前相比,国际形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国际社会的基本结构未变,即:国际社会依然是由地位平等的主权国家所构成,不存在超越国家之上的世界
政府。
国际社会的这种“无政府”状态,以及世界范围内资源的有限性,使得国家间的冲突成为可能。但另一方面,由于各国具有共同的利益,而单边追求本国利益又会受到其他国家的遏止,所以,国际合作又成为每个国家的现实选择。[1]目前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两大流派: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
主义,分别对国际冲突和国际合作做出了解释。[2]那么,如何从国际法学角度来解释国家之间的合作呢?国际合作是否已成为国家的一项“法律义务”或已经成为国际法的一项原则呢?[3]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一、国际合作法律义务的产生
现实告诉我们,国家的确承担着大量的法律意义上的合作义务。例如,向他国引渡罪犯、向他国提供对外经济贸易管理方面的法律信息、放弃某种税收管辖权、履行国际组织就特定事项做出的决议等等。那么,国家的这些合作义务是如何产生的呢?
一项法律义务的产生无非基于两种情况:法律规定和符合法律规定的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国家的合作义务也只能基于国际法的规定或国家之间的符合国际法的约定而产生。
国际法是否一般地规定了国家具有同他国合作的义务呢?对此很难给出肯定的判断。如前所述,由于国家都是平等的主权者,因此,并不存在着超越国家的政府和立法机关;除非存在国际强行法规则,国际法规则只能基于国家之间明示或默示的约定产生,每个国家只接受自己所愿意接受的规范的约束。我们目前还无法证明存在着这样一条国际强行法规则:每个国家都必须与其他国家合作。由此,国家如果承担着合作义务的话,那么,这种合作义务或者产生于它所明确接受的条约规范,或者产生于它所明示或默示接受了的习惯法规则。所以,国家的合作义务,尽管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但从性质上看,应属于约定义务,而非法定义务。
在实践中,我们可以确切地加以表述的国家的合作义务基本上都属于国家通过条约所接受的义务。由于《联合国宪章》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具有十分广泛的成员国(方),这些条约所规定的合作义务又影响到许多领域,这才使一些学者不加区分地认为,国际合作已成为一般的国际法上的义务,甚至已成为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二战结束以来,国际条约的数量急剧增加、条约所覆盖的领域不断扩大、条约的约束机制也不断完善,这使得国家的合作义务也日益增多。从1920年1月10日到1945年10月1日国际联盟实施条约登记和公布制度的25年中,在国际联盟登记的条约有4834项;而根据联合国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的资料,截止到1998年4月,经联合国登记并公布的条约已超过1900卷,计40000余项。国际条约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已扩展到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例如,在政治方面有《联合国宪章》;在经济方面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WTO规则;在外交方面有《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和《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在人权保护方面有《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环境保护方面有《防止海上油污国际公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海洋方面有《海洋法公约》,在航空方面有《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在外空方面有《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等等。国际条约所覆盖的领域的扩大,使得各缔约国几乎在国际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承担起合作的义务。与此同时,国际条约的约束力也不断增强。许多国际条约都设立了特定的机构以保障条约的履行。一些国际条约还设立了争端解决机制,由争端当事国或特定的争端解决机构依据预先设立的程序规则来解决条约履行过程中所产生的争议,以促使缔约国履行自己的合作义务。而且,由于条约的争端解决机制通常都具有救济功能,所以当条约所意图维系的合作关系遭到破坏时,可尽量得以修复。
国际条约成为国际合作的基本载体是由条约的性质所决定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在其序言中即明确指出:“条约为国际法渊源之一,且为各国间不分宪法及社会制度发展和平合作之工具,其重要性日益增加”,“自由同意与善意之原则以及条约必须遵守规则乃举世所承认”。前一句话在于说明条约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发展和平合作的工具;后一句话则说明了条约成为合作工具的原因,即:条约是善意的自由同意的产物,而且,条约必须遵守是普遍承认的国际法规则。因为主权国家地位平等,所以条约只能是缔约国自由同意的产物;而“条约必须遵守”则是条约实践得以持续的基础性的规则保障。如果国家之间的约定可以随意毁弃,那么条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正因为如此,许多国际法学者都将条约必须遵守作为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或基本规范。汉斯.凯尔森即曾指出,由习惯所创设的国际法规范(被凯尔森称为“一般”国际法规范)在效力上高于条约所创设的国际法规范;而在这些一般的国际法规范中,条约必须遵守这一规范尤为重要,因为它使得国际社会的主体得以凭借条约来约束彼此的行为。[4]由于“条约必须遵守”的原则是如此重要,而且也从来没有哪个国家拒绝承认这一原则,所以,“条约必须遵守”应该是一项国际强行法规则。
国际条约为缔约国所设立的合作义务,不仅是指条约中已经列明的具体义务,而且还包括条约所规定的进一步合作的义务。许多条约在明确了缔约国在特定事项的合作上已取得的进展的同时,还为以后的合作建构出基本的框架。在这种情况下,各缔约国的合作义务就包括了为未来的合作而进行合作的义务。世界贸易组织、欧盟和其他一些区域性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当然,未来的合作究竟能否实现,仍由各缔约国自主决定。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同意就竞争规则进行谈判,并不意味着(事实上也没有使得)统一竞争规则的如期确立。
国际合作义务,从广义上看,还包括一国不单方面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义务。有学者将这类义务的内容归纳为:不干涉他国内政、不鼓动他国内乱和不威胁国际和平。[5]这类合作义务并不需要基于条约的约定。国际习惯法已为国家创设了这类义务。
二、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
我们有时所说的“国际合作义务”可能只是一种国际道德义务,而非法律义务。在没有习惯法依据和条约约定情况下的合作义务,只能是道德义务。
道德义务产生于道德规范。道德与法虽然同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但法律是国家意志规范化的表现,须经国家制订或认可,并以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其实施;而道德虽然也以规范的形式表现,但这种规范却无需国家制订或认可,而且这种规范也只以舆论谴责作为其实施的保证。从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范围上看,“法律只对建立和维持正常社会秩序具有较为重要意义的社会关系加以调控并发生作用。而道德则对人的整个生活和人们的全部社会关系发生作用。”[6]
同国内社会一样,国际社会中的各种社会关系也需要法律规范(国际法)和道德规范(国际道德)的调整。在谈到国际法与国际道德的区别时,菲德罗斯写道:“这两个规范领域是支配世界的道德律的两个分支,然而它们是有区别的,其区别在于道德包括那些把人作为道德的人格者而拘束他们的规范,而法律则把人作为社会的生物而规定他们的行为。” [7]其实,国际法与国际道德的更为明显的区别在于依据国际法和国际道德所承担的义务的不同。国际法主体依据国际法规范所承担的义务是法律义务。同国内法上的义务一样,违背国际法律义务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义务违背者不肯主动承担这种法律责任的话,那么,法律责任的实现就会表现为一种制裁。而违背国际道德义务则通常只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当然,同国内的情形相同,国际法与国际道德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既然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只是组成国家的人民的权利和义务,那么,使国际法与作为调整人的行为的主要国内法理体系所依据的一般法律原则和道德相脱离,在科学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中也是不适宜的。如果法律反映了现行道德规则,法律作为法律体系的力量就增强了,这对于国际法和国内法是同样适用的。”[8]
国际道德规范也要求国家之间进行合作。国际道德规范的一个古老的例子是:在其他民族发生饥谨的情况下,有予以救助的义务。[9]其他的一些国际合作义务实质上也属于道德义务。例如,从1964年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开始,国际社会即呼吁发达国家排除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障碍,给予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商品以普遍的、非互惠的和非歧视的关税优惠待遇。尽管这一设想,已被关贸总协定第37条第8 款和一些发达国家的国内立法所肯定,但由于总协定的用语十分模糊,而国内立法又不能像国际条约那样在给惠国和受惠国之间建立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如果说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负有某种合作义务的话,那么,这种义务也只能是道德义务。
由于道德标准通常高于法律标准,因此,如果某种国际道德规范已转化为国际法律规范,则表明国际法的进步。法律意义上的合作义务自然要比道德意义上的合作义务更加确定和更易于履行。由于环境问题具有跨国性,因此在环境保护方面各国应相互合作,这一直是人们的共识。但在有关的国际条约达成之前,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义务只是道德义务。随着各国共同保护和治理环境的需求日见迫切,国际社会终于在上个问题上达成了一系列的公约。而且,由于考虑到发达国家应对国际环境的恶化负主要责任,而发展中国家治理环境的能力又十分有限,这些公约一开始即体现出公平原则。例如,1990年修正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和1992年制订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均规定发达国家要做出特别安排,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额外的资金和转让有关的技术;1992年制订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则明确规定:“各缔约方应在公平的基础上,并根据它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为人类当代和后代的利益保护气候系统。因此,发达国家缔约方应当率先对付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1997年制订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更是在温室气体排放方面为发达国家规定了特别的义务。
三、合作义务与国家主权
广泛的国际合作义务约束是否会损害国家的主权呢?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是需要澄清:主权其实是国家的身份,而非国家的权力。权力与身份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权力通常是指某一主体从事某项可以产生法律效力的行为的能力;而身份则是指某一个体与共同体的其他成员的法律关系。我们在谈论国家主权的时候,我们所关注的并不是国家的某项行为是否会产生法律效力,而是在强调国家与其他国内社会成员或国际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因此,主权这一概念所阐释的其实是国家的身份。“各个国家按照它们的性质在权力、领土等方面肯定不是平等的。但是,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它们在原则上是平等的,尽管它们可以有任何差异。这是它们在国际范围内的主权的结果。”[10]
国际条约的大量产生及其覆盖领域的扩大使得国家不能再像先前一样独立地进行决策,因为它必须考虑已经通过条约所承担的国际义务。但不能就此认为国际条约在限制或剥夺国家主权。首先,对外订立条约是国家主权的一项具体内容。正因为主权使得各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地位平等,国家才拥有对外订立条约的资格。前常设国际法院于1923年即曾声明:“法院拒绝承认,国家在缔结任何承允采取或不采取某种特定行动的条约时是放弃了它的主权……。参加国际协定的权利,是国家主权的一种属性。”[11]其次,条约对国家的约束是国家之间的彼此约束,而不是其他实体对国家所施加的约束。通过缔结条约,国家虽然承受某种新的约束,但同时也获得它先前不曾获得的利益。再次,条约对国家的约束并非是绝对的,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来选择是实际地履行某一条约义务,还是不履行义务而接受他国的报复或对其他国家提供补偿。最后,国家既然可以缔结和加入条约,也就可以在其认为适当的时候退出条约。当国家认为它参加条约所获得的利益小于它基于条约所付出的代价的话,它自可以依照条约所设定的程序退出该条约。
政府间国际组织所创设的合作义务是条约创设合作义务的一种特殊表现。这种合作义务对有关国家的约束更为广泛和直接。以欧盟为例,欧盟是当今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和最具影响力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其成员国所承担的合作义务也最为广泛和具体,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即已建成欧洲统一市场,实现了商品、人员、劳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高度的一体化使欧盟法律具有超越各成员国国内立法的效力。当欧盟的立法与成员国的国内立法相冲突时,欧盟法优先;某些欧盟立法更是具有直接效力性,各国的私人可以直接依据欧盟立法而主张其权利。如此高度一体化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否会削弱国家主权呢?回答也应该是否定的。首先,尽管政府间国际组织通常均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但这种国际法主体资格是成员国政府通过条约方式予以设定的,因此,国际组织尽管在主体资格方面可以同成员国的资格相分离,但它毕竟是成员国的合意的产物,成员国不会因为创设了国际组织的人格而使其自身的人格受到损伤。其次,成员国让渡给国际组织的只能是主权者的某些权力或权利,而不是主权本身。[12]由于国家主权其实指的是国家的身份、国家的人格;因此,只要国家正常存在,主权就不容许有任何减损。但主权者的权力或权利,或者说主权性权力或权利是可以转让的。许多国际条约对主权(sovereignty)和主权权利(sovereign right)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别,正说明主权这一概念虽然在汉语中隐含着“权力”或“权利”的概念,但它有别于法律意义上的“权力”或“权利”。再次,即使是欧盟这种高度发达的国际组织,也没有产生销蚀成员国主权的后果。虽然欧盟的成员国已经将货币发行权这种最能体现国家主权的权力都交给了欧盟组织,但也只能将此理解为成员国选择了别样的行使货币发行权的方式。不是每个欧盟成员都必须选择欧元,而且,即使加入欧元货币体系,成员国仍有退出的权利。从根本上说,只要国家保有退出国际组织的权利,就不能说国家主权已受到限制。
四、小结
我国的和平发展离不开广泛的国际合作。具体的合作义务源自条约的规定。只有基于条约,我国才会承担确定的合作义务;只有基于条约,我国才会享有要求其他国家予以合作的权利。某些国际合作义务可能仅属国际道德义务。道德义务不会产生法律责任。但国际合作义务可以从道德义务转变为法律义务。合作义务使国家承受约束,但不会损害国家主权。主权作为国家的身份将伴随国家始终。
此文曾载于《法学家》2004年第6期
【注释】
[1]可参见Scott Barret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ons, Duke Environmental Law & Policy Forum, Vol.10:131, 1999, pp.131.
[2]可参见秦亚青:《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反思新新自由制度主义》,《外交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第40页-41页。
[3]许多学者认为国际合作已成为国家的法律义务,或者已成为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可参见邵沙平、余敏友主编:《国际法问题专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版11月版,第75页;曾华群:《国际经济法导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214页;屈广清、陈小云:《现代国际海洋环境保护法之基本原则》,载于张乃根主编:《当代国际法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416页。
[4]Hans Kelsen, The Essence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Relevance of International Law, edited by Karl Deutsch and Stanley Hoffman, Schenkman Publishing Company, 1968, pp.118-119.
[5]张乃根:《国际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53页。
[6]郑成良主编:《现代法理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7页。
[7][奥]阿.菲德罗斯:《国际法》,李浩培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0页。
[8][英]詹宁斯、瓦茨:《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一分册,王铁崖等译,31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9][奥]阿.菲德罗斯:《国际法》,李浩培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1页。
[10][英]詹宁斯、瓦茨:《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一分册,王铁崖等译,275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11]转引自[英]M.阿库斯特:《现代国际法概论》,汪暄等译,1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2]有学者指出:国家可以向国际组织让渡某些主权功能(sovereign functions),但这绝不意味着主权的任何部分的永久出让。见:Ingrid Detter,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 1998, pp.484.
车丕照 (清华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
我国的和平发展离不开特定的国际环境。尽管与冷战结束之前或与二战结束之前相比,国际形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国际社会的基本结构未变,即:国际社会依然是由地位平等的主权国家所构成,不存在超越国家之上的世界
政府。
国际社会的这种“无政府”状态,以及世界范围内资源的有限性,使得国家间的冲突成为可能。但另一方面,由于各国具有共同的利益,而单边追求本国利益又会受到其他国家的遏止,所以,国际合作又成为每个国家的现实选择。[1]目前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两大流派: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
主义,分别对国际冲突和国际合作做出了解释。[2]那么,如何从国际法学角度来解释国家之间的合作呢?国际合作是否已成为国家的一项“法律义务”或已经成为国际法的一项原则呢?[3]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一、国际合作法律义务的产生
现实告诉我们,国家的确承担着大量的法律意义上的合作义务。例如,向他国引渡罪犯、向他国提供对外经济贸易管理方面的法律信息、放弃某种税收管辖权、履行国际组织就特定事项做出的决议等等。那么,国家的这些合作义务是如何产生的呢?
一项法律义务的产生无非基于两种情况:法律规定和符合法律规定的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国家的合作义务也只能基于国际法的规定或国家之间的符合国际法的约定而产生。
国际法是否一般地规定了国家具有同他国合作的义务呢?对此很难给出肯定的判断。如前所述,由于国家都是平等的主权者,因此,并不存在着超越国家的政府和立法机关;除非存在国际强行法规则,国际法规则只能基于国家之间明示或默示的约定产生,每个国家只接受自己所愿意接受的规范的约束。我们目前还无法证明存在着这样一条国际强行法规则:每个国家都必须与其他国家合作。由此,国家如果承担着合作义务的话,那么,这种合作义务或者产生于它所明确接受的条约规范,或者产生于它所明示或默示接受了的习惯法规则。所以,国家的合作义务,尽管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但从性质上看,应属于约定义务,而非法定义务。
在实践中,我们可以确切地加以表述的国家的合作义务基本上都属于国家通过条约所接受的义务。由于《联合国宪章》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具有十分广泛的成员国(方),这些条约所规定的合作义务又影响到许多领域,这才使一些学者不加区分地认为,国际合作已成为一般的国际法上的义务,甚至已成为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二战结束以来,国际条约的数量急剧增加、条约所覆盖的领域不断扩大、条约的约束机制也不断完善,这使得国家的合作义务也日益增多。从1920年1月10日到1945年10月1日国际联盟实施条约登记和公布制度的25年中,在国际联盟登记的条约有4834项;而根据联合国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的资料,截止到1998年4月,经联合国登记并公布的条约已超过1900卷,计40000余项。国际条约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已扩展到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例如,在政治方面有《联合国宪章》;在经济方面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WTO规则;在外交方面有《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和《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在人权保护方面有《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环境保护方面有《防止海上油污国际公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海洋方面有《海洋法公约》,在航空方面有《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在外空方面有《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等等。国际条约所覆盖的领域的扩大,使得各缔约国几乎在国际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承担起合作的义务。与此同时,国际条约的约束力也不断增强。许多国际条约都设立了特定的机构以保障条约的履行。一些国际条约还设立了争端解决机制,由争端当事国或特定的争端解决机构依据预先设立的程序规则来解决条约履行过程中所产生的争议,以促使缔约国履行自己的合作义务。而且,由于条约的争端解决机制通常都具有救济功能,所以当条约所意图维系的合作关系遭到破坏时,可尽量得以修复。
国际条约成为国际合作的基本载体是由条约的性质所决定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在其序言中即明确指出:“条约为国际法渊源之一,且为各国间不分宪法及社会制度发展和平合作之工具,其重要性日益增加”,“自由同意与善意之原则以及条约必须遵守规则乃举世所承认”。前一句话在于说明条约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发展和平合作的工具;后一句话则说明了条约成为合作工具的原因,即:条约是善意的自由同意的产物,而且,条约必须遵守是普遍承认的国际法规则。因为主权国家地位平等,所以条约只能是缔约国自由同意的产物;而“条约必须遵守”则是条约实践得以持续的基础性的规则保障。如果国家之间的约定可以随意毁弃,那么条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正因为如此,许多国际法学者都将条约必须遵守作为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或基本规范。汉斯.凯尔森即曾指出,由习惯所创设的国际法规范(被凯尔森称为“一般”国际法规范)在效力上高于条约所创设的国际法规范;而在这些一般的国际法规范中,条约必须遵守这一规范尤为重要,因为它使得国际社会的主体得以凭借条约来约束彼此的行为。[4]由于“条约必须遵守”的原则是如此重要,而且也从来没有哪个国家拒绝承认这一原则,所以,“条约必须遵守”应该是一项国际强行法规则。
国际条约为缔约国所设立的合作义务,不仅是指条约中已经列明的具体义务,而且还包括条约所规定的进一步合作的义务。许多条约在明确了缔约国在特定事项的合作上已取得的进展的同时,还为以后的合作建构出基本的框架。在这种情况下,各缔约国的合作义务就包括了为未来的合作而进行合作的义务。世界贸易组织、欧盟和其他一些区域性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当然,未来的合作究竟能否实现,仍由各缔约国自主决定。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同意就竞争规则进行谈判,并不意味着(事实上也没有使得)统一竞争规则的如期确立。
国际合作义务,从广义上看,还包括一国不单方面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义务。有学者将这类义务的内容归纳为:不干涉他国内政、不鼓动他国内乱和不威胁国际和平。[5]这类合作义务并不需要基于条约的约定。国际习惯法已为国家创设了这类义务。
二、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
我们有时所说的“国际合作义务”可能只是一种国际道德义务,而非法律义务。在没有习惯法依据和条约约定情况下的合作义务,只能是道德义务。
道德义务产生于道德规范。道德与法虽然同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但法律是国家意志规范化的表现,须经国家制订或认可,并以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其实施;而道德虽然也以规范的形式表现,但这种规范却无需国家制订或认可,而且这种规范也只以舆论谴责作为其实施的保证。从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范围上看,“法律只对建立和维持正常社会秩序具有较为重要意义的社会关系加以调控并发生作用。而道德则对人的整个生活和人们的全部社会关系发生作用。”[6]
同国内社会一样,国际社会中的各种社会关系也需要法律规范(国际法)和道德规范(国际道德)的调整。在谈到国际法与国际道德的区别时,菲德罗斯写道:“这两个规范领域是支配世界的道德律的两个分支,然而它们是有区别的,其区别在于道德包括那些把人作为道德的人格者而拘束他们的规范,而法律则把人作为社会的生物而规定他们的行为。” [7]其实,国际法与国际道德的更为明显的区别在于依据国际法和国际道德所承担的义务的不同。国际法主体依据国际法规范所承担的义务是法律义务。同国内法上的义务一样,违背国际法律义务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义务违背者不肯主动承担这种法律责任的话,那么,法律责任的实现就会表现为一种制裁。而违背国际道德义务则通常只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当然,同国内的情形相同,国际法与国际道德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既然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只是组成国家的人民的权利和义务,那么,使国际法与作为调整人的行为的主要国内法理体系所依据的一般法律原则和道德相脱离,在科学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中也是不适宜的。如果法律反映了现行道德规则,法律作为法律体系的力量就增强了,这对于国际法和国内法是同样适用的。”[8]
国际道德规范也要求国家之间进行合作。国际道德规范的一个古老的例子是:在其他民族发生饥谨的情况下,有予以救助的义务。[9]其他的一些国际合作义务实质上也属于道德义务。例如,从1964年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开始,国际社会即呼吁发达国家排除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障碍,给予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商品以普遍的、非互惠的和非歧视的关税优惠待遇。尽管这一设想,已被关贸总协定第37条第8 款和一些发达国家的国内立法所肯定,但由于总协定的用语十分模糊,而国内立法又不能像国际条约那样在给惠国和受惠国之间建立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如果说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负有某种合作义务的话,那么,这种义务也只能是道德义务。
由于道德标准通常高于法律标准,因此,如果某种国际道德规范已转化为国际法律规范,则表明国际法的进步。法律意义上的合作义务自然要比道德意义上的合作义务更加确定和更易于履行。由于环境问题具有跨国性,因此在环境保护方面各国应相互合作,这一直是人们的共识。但在有关的国际条约达成之前,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义务只是道德义务。随着各国共同保护和治理环境的需求日见迫切,国际社会终于在上个问题上达成了一系列的公约。而且,由于考虑到发达国家应对国际环境的恶化负主要责任,而发展中国家治理环境的能力又十分有限,这些公约一开始即体现出公平原则。例如,1990年修正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和1992年制订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均规定发达国家要做出特别安排,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额外的资金和转让有关的技术;1992年制订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则明确规定:“各缔约方应在公平的基础上,并根据它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为人类当代和后代的利益保护气候系统。因此,发达国家缔约方应当率先对付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1997年制订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更是在温室气体排放方面为发达国家规定了特别的义务。
三、合作义务与国家主权
广泛的国际合作义务约束是否会损害国家的主权呢?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是需要澄清:主权其实是国家的身份,而非国家的权力。权力与身份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权力通常是指某一主体从事某项可以产生法律效力的行为的能力;而身份则是指某一个体与共同体的其他成员的法律关系。我们在谈论国家主权的时候,我们所关注的并不是国家的某项行为是否会产生法律效力,而是在强调国家与其他国内社会成员或国际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因此,主权这一概念所阐释的其实是国家的身份。“各个国家按照它们的性质在权力、领土等方面肯定不是平等的。但是,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它们在原则上是平等的,尽管它们可以有任何差异。这是它们在国际范围内的主权的结果。”[10]
国际条约的大量产生及其覆盖领域的扩大使得国家不能再像先前一样独立地进行决策,因为它必须考虑已经通过条约所承担的国际义务。但不能就此认为国际条约在限制或剥夺国家主权。首先,对外订立条约是国家主权的一项具体内容。正因为主权使得各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地位平等,国家才拥有对外订立条约的资格。前常设国际法院于1923年即曾声明:“法院拒绝承认,国家在缔结任何承允采取或不采取某种特定行动的条约时是放弃了它的主权……。参加国际协定的权利,是国家主权的一种属性。”[11]其次,条约对国家的约束是国家之间的彼此约束,而不是其他实体对国家所施加的约束。通过缔结条约,国家虽然承受某种新的约束,但同时也获得它先前不曾获得的利益。再次,条约对国家的约束并非是绝对的,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来选择是实际地履行某一条约义务,还是不履行义务而接受他国的报复或对其他国家提供补偿。最后,国家既然可以缔结和加入条约,也就可以在其认为适当的时候退出条约。当国家认为它参加条约所获得的利益小于它基于条约所付出的代价的话,它自可以依照条约所设定的程序退出该条约。
政府间国际组织所创设的合作义务是条约创设合作义务的一种特殊表现。这种合作义务对有关国家的约束更为广泛和直接。以欧盟为例,欧盟是当今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和最具影响力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其成员国所承担的合作义务也最为广泛和具体,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即已建成欧洲统一市场,实现了商品、人员、劳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高度的一体化使欧盟法律具有超越各成员国国内立法的效力。当欧盟的立法与成员国的国内立法相冲突时,欧盟法优先;某些欧盟立法更是具有直接效力性,各国的私人可以直接依据欧盟立法而主张其权利。如此高度一体化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否会削弱国家主权呢?回答也应该是否定的。首先,尽管政府间国际组织通常均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但这种国际法主体资格是成员国政府通过条约方式予以设定的,因此,国际组织尽管在主体资格方面可以同成员国的资格相分离,但它毕竟是成员国的合意的产物,成员国不会因为创设了国际组织的人格而使其自身的人格受到损伤。其次,成员国让渡给国际组织的只能是主权者的某些权力或权利,而不是主权本身。[12]由于国家主权其实指的是国家的身份、国家的人格;因此,只要国家正常存在,主权就不容许有任何减损。但主权者的权力或权利,或者说主权性权力或权利是可以转让的。许多国际条约对主权(sovereignty)和主权权利(sovereign right)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别,正说明主权这一概念虽然在汉语中隐含着“权力”或“权利”的概念,但它有别于法律意义上的“权力”或“权利”。再次,即使是欧盟这种高度发达的国际组织,也没有产生销蚀成员国主权的后果。虽然欧盟的成员国已经将货币发行权这种最能体现国家主权的权力都交给了欧盟组织,但也只能将此理解为成员国选择了别样的行使货币发行权的方式。不是每个欧盟成员都必须选择欧元,而且,即使加入欧元货币体系,成员国仍有退出的权利。从根本上说,只要国家保有退出国际组织的权利,就不能说国家主权已受到限制。
四、小结
我国的和平发展离不开广泛的国际合作。具体的合作义务源自条约的规定。只有基于条约,我国才会承担确定的合作义务;只有基于条约,我国才会享有要求其他国家予以合作的权利。某些国际合作义务可能仅属国际道德义务。道德义务不会产生法律责任。但国际合作义务可以从道德义务转变为法律义务。合作义务使国家承受约束,但不会损害国家主权。主权作为国家的身份将伴随国家始终。
此文曾载于《法学家》2004年第6期
【注释】
[1]可参见Scott Barret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ons, Duke Environmental Law & Policy Forum, Vol.10:131, 1999, pp.131.
[2]可参见秦亚青:《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反思新新自由制度主义》,《外交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第40页-41页。
[3]许多学者认为国际合作已成为国家的法律义务,或者已成为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可参见邵沙平、余敏友主编:《国际法问题专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版11月版,第75页;曾华群:《国际经济法导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214页;屈广清、陈小云:《现代国际海洋环境保护法之基本原则》,载于张乃根主编:《当代国际法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416页。
[4]Hans Kelsen, The Essence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Relevance of International Law, edited by Karl Deutsch and Stanley Hoffman, Schenkman Publishing Company, 1968, pp.118-119.
[5]张乃根:《国际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53页。
[6]郑成良主编:《现代法理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7页。
[7][奥]阿.菲德罗斯:《国际法》,李浩培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0页。
[8][英]詹宁斯、瓦茨:《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一分册,王铁崖等译,31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9][奥]阿.菲德罗斯:《国际法》,李浩培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1页。
[10][英]詹宁斯、瓦茨:《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一分册,王铁崖等译,275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11]转引自[英]M.阿库斯特:《现代国际法概论》,汪暄等译,1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2]有学者指出:国家可以向国际组织让渡某些主权功能(sovereign functions),但这绝不意味着主权的任何部分的永久出让。见:Ingrid Detter,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 1998, pp.484.
车丕照 (清华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